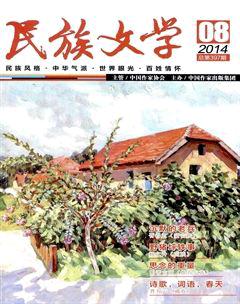葉梅創作論
李美皆
葉梅的寫作,基本上可以分為三個方面:民族書寫、地域書寫、女性書寫。
民族書寫
葉梅是一個具有強烈民族自覺的作家,那種自然而然地化在她骨子里的民族眼光和民族意識,首先緣于她的土家族出身,以及她文化血液中的土家族精神。
葉梅的寫作,既是對土家族歷史風俗的巡禮,又是向土家族文化精神的致敬,即使一個不了解土家族的人,在讀完葉梅的作品后,心里也會立起一座土家族的文化雕像。
小說是民族的感性歷史,鄂西土家族從前是土司制,雍正十三年“改土歸流”,實行流官制,葉梅的小說《山上有個洞》中,寫到了“改土歸流”的疼痛轉折。葉梅是以虛寫實,雖然故事是虛構的,但這段歷史卻是真實的,田土司也實有其人,雖然此田土司未必彼田土司。葉梅筆下的土司(包括《最后的土司》中的土司覃堯),從來不是一個腐朽的代名詞或惡的刻板印象,而是到“武漢、宜昌等地上過學堂,尊重文化,喜愛山水,包容豁達”的勵精圖治、值得崇敬的陽剛男人,這是葉梅對于土司的一以貫之的歷史認知。田土司絕非托爾斯泰理想中將土地財產分給窮人的人道主義者,但也不是一個桀紂式的暴君昏君,罪不當絕,但朝廷決定收回各族自治的權力,改世襲土司制為朝廷任命制,實現中央集權,就必定要拿田土司是問。田土司作為最后的土司的歷史命運是無法逃脫的,無論他本人如何作為,都改變不了這一命運。一個陽剛的土司,代表著一個陽剛的民族;一個土司的勵精圖治,說明著一個民族生活的蒸蒸日上,在對田土司的理想刻畫中,暗寓著葉梅深厚的民族情感。
葉梅不僅熟稔自己的民族歷史,對于土家族的規矩也是頗下功夫的。她寫龍船河祖上的規矩,造屋很講究:“土官衙署可倚柱雕梁,磚瓦鱗次。百姓叉木架屋,編竹為墻。舍巴頭目則可立豎梁柱,周以板壁,然不準蓋瓦。違者即治僭越之罪。”
葉梅對于土家風俗的呈現更為感性和直觀。土家族實行流官制之后,有了多種文化的匯合。“即便如此,土家族還是保留著許多屬于自己的文化,他們敬畏天地,以跳喪的方式表達對生死的莊重泰然……”“我曾經多次在鄉間看到土家人的跳喪而為之深深感動。這不僅是一種習俗,更多的是表達了一個民族對世界和生命的看法。”《撒憂的龍船河》中,葉梅把跳喪的場面寫得酣暢淋漓,感覺那絕非死亡之舞,而是剽悍的生命之舞。“久居山野的土家人古來便信奉‘天人合一,他們與大自然的關系十分親近,對于生命的來去因此而達觀從容,把死亡看作是生命的另一種形式,不過是踏進了生的另一道門檻。因此親友離去之后,活著的人們不是以悲傷告別,而是載歌載舞歡送亡人的遠行。歌者酣暢淋漓地吟唱亡人生前的事跡,還有古往今來的傳說,通宵達旦,多者可達三天三夜。”這種生死觀無疑昭示著一個民族來自彼岸的強大元氣。
《最后的土司》中,葉梅寫土家族的舍巴日儀式,寫伍娘的舞蹈,如精靈,如火焰,寫如雷滾過的鼓聲,令人血脈賁張。《花樹花樹》等寫到哭嫁是土家女兒的必修功課,哭嫁歌要唱上一個月,夜晚姑娘們同著火塘輪流唱。《歌棒》則寫到了大量薈萃土家精華的民歌民謠。這得益于葉梅接地氣的生活經歷:“在與其他民族文化相融之時,土家人仍然保留了自己獨有的民歌民謠民間文化。我在文工團期間,曾上山下鄉走鄉串戶,做過多年的搜集,受到過很多滋養。”
除了土司、巫師、祭祀儀式等民族符號,葉梅的民族書寫更重要的是寫出了土家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葉梅從不掩飾作為土家人的自豪及其對于土家民族性的傾心。“他們任俠尚義,知恩必報,一語相投,傾身與交,偶觸所忌,反言若不相識;彼此有仇釁,經世不能解,待明察者一言剖解,往往貼首而服。”
《撒憂的龍船河》寫出了土家漢子覃老大的血性。有婦之夫覃老大在一次艱險的行船中與客家女子蓮玉發生激情之戀,造成蓮玉的不幸,之后蓮玉的一個神色,就讓覃老大義無反顧前往,失掉了一條胳膊。這算是為革命立了一功,覃老大被縣里請去做貧協委員。當覃老大日思夜想的蓮玉為了補償,為了了結,將身子交給覃老大時,覃老大感覺到蓮玉已經沒有情分了,只是施舍,便斷然拒絕,揚長而去。
你覃老大是人,不是發情的野豬。這一點真好,要三叩九拜感謝祖先,你是人。你可以無所顧忌地呼喊著,高高地雄踞在豌豆角船頭,將船兒撥弄得如一把利刃,犁開河的胸膛,將癡呆的峽谷和云彩遠遠地拋在身后,讓兩岸的猴兒望塵莫及地追趕不停。那時你一腔熱血一腔激情至高無上,你全身輕松自若出神入化一點也不勉強也不忸怩。你是應該回到那里去,心搏斗了這么些時光,終于明白過來,趁著月光趕緊走啊。
“文革”中,覃老大進了縣革委會,蓮玉又為落難的丈夫來求覃老大,并表示“你要什么我全依你”。
覃老大臉上像潑了盆豬血,心里惱怒而又感嘆不已。他與女子終究是兩座山上的人,歌子里的詞這樣唱的,見面能搭話,相見要一年。他與這女子的心總是遠遠地隔著。她始終沒有明白他覃老大是怎樣一條漢子。而這女子對于他來說也永遠是一個摸不透的謎。
覃老大深愛這個女人,愛得恨不能吞了她,但是,他要的是愛,不是施舍、補償、交易,否則,就是對他的侮辱,再怎么想要他也不能接受。他會幫這個女人,但他絕不乘人之危。在覃老大這個形象身上,一個民族的精魂被刻畫到入骨。
在彰顯土家民族文化人格的同時,葉梅也觸及了民族間的隔膜問題。《撒憂的龍船河》中,已經寫到了土家人覃老大與客家人蓮玉之間無法消泯的隔膜,就算他們的身體曾經親密交融,內心卻“終究是兩座山上的人”。這不僅是人與人之間的隔膜,而且是民族與民族之間的隔膜,對于客家女子蓮玉來說,一個男人既已與一個姑娘有親密關系,就要為她負責;而“在土家人來說,旁人的媳婦只準看不準弄,但未出門的妹子家是可以相好相交的。到人家里做客,千萬不能同人家婆娘坐一條板凳,但同人家的妹妹卻可以任意調笑。”因此,這罪與罰的關系在兩個人乃至兩個民族看來,是錯位并難以統一的。
在《最后的土司》中,民族間的文化隔膜導致的問題更加明顯。手藝人李安躲壯丁來到龍船河,恰逢龍船河的舍巴日祭祀儀式,李安腿壞了,無法覓食,因為太餓偷拿了舍巴日的供品,得罪了龍船河的祖先和眾神,土司覃堯下令砍去他的一條腿——正是壞掉的那條腿,并讓美麗的啞女伍娘照顧他。伍娘是一個在木盆里順水漂來的孤女,是舍巴日儀式中舞動得最美麗最酣暢的女子。在伍娘的細心照料下,李安很快康復,并用自己的手藝做了一條假腿。李安和伍娘相愛了。伍娘認為,他們的婚事必須征得土司覃堯的同意;李安卻認為,相愛是兩個人的事。在伍娘的周旋下,他們的婚事還是得到了土司覃堯的同意。龍船河的一切都由土司覃堯做主,由梯瑪覃老二稟報神靈祖先。伍娘和李安的居屋,也按照土家規矩由覃堯帶人進行了重建。婚前,伍娘按土家規矩住到覃堯家去,有九個姑娘日夜圍唱哭嫁歌,李安根本見不到她,好不容易見到一次,李安激情難抑,竟遭伍娘拒絕。終于到新婚之夜,李安卻遲遲不見伍娘。原來,龍船河還有一個規矩,新嫁娘的初夜是要獻給神的,神就是土司覃堯。這就是伍娘幾天前拒絕李安的原因。李安咆哮著要殺掉覃堯。
伍娘從小“就感覺到有無數的精靈在天地間活躍,她驚奇太陽的落下月亮的升起,花兒的開放和莊稼按時的成熟。她在無師自通的舍巴舞中感到自己就要與那種無所不在卻又無影無形的力量融合。老人們許多次隱喻的啟示使她知道有.一種方式可以抵達,那與她的舞蹈不約而同地有著相通之處。”她完全是把覃堯當作神來看待,并奉獻自己初夜的。她跳舍巴舞時有多投入,這一夜就有多投入,那都是對神的激情。
覃堯到外面的世界受過教育,回來后許多世代相傳的規矩已經廢止了,包括初夜權。覃堯自感慚愧,他知道土民奉獻的是神而自己只是一個凡人,不想去污染了族間的女兒,其后初夜權只是象征而已。然而這一次,他對伍娘,卻不只是象征而已。因為,自從伍娘定親之后,他發現自己是如此愛戀這個神靈的女孩,簡直無法想象她將為李安這個外鄉人所擁有。這一夜,經過一番心理斗爭后,覃堯決定心安理得地擁有伍娘,并做好了一旦李安不能容忍,自己就娶她的心理準備。
在人與“神”歡合之時,暴怒的李安點燃了新房,自己也消失不見了。覃堯正中下懷,以為這下他可以娶伍娘了。然而,伍娘卻像不認識他了似的。伍娘愛的是李安,她不愛作為凡人的覃堯。那一夜,她只是把自己奉獻給覃堯所代表的神,而不是覃堯本人,是覃堯混淆了自己身上人與神的界限。伍娘不明白,李安為什么一夜之間變了。梯瑪告訴她,因為她把身子給了別人。她指天發誓,那一夜她是給了神,而不是什么人。梯瑪說:“你說你給了神,可李安只是人,他不懂得神,也一點兒都不想懂得。”伍娘絕望地尋找著李安。
李安回來向覃堯復仇時,被官兵捉住了。覃堯不惜代價救下了李安,要他與伍娘好好生活。可是,李安并不感激覃堯,依然恨之入骨。李安對伍娘也百般虐待,他越愛她,就越要虐待她。李安終于對伍娘回心轉意,并設計報復了覃堯之后,卻發現孩子是覃堯的。李安又開始虐待伍娘,并惡毒地讓伍娘把孩子生下來,作為挾制和報復覃堯的殺手锏。李安以得到覃堯的寶物和讓覃堯失去舌頭為條件,把孩子給了覃堯,自己要帶伍娘遠走高飛。但伍娘決不答應。
又一年舍巴日到來時,傳說瘋了或躲起來了的伍娘像一道火焰,突然沖進了舍巴堂的中央,舍巴舞立刻有了精魂。伍娘滴血而舞,鼓聲停住時,她倒下了。此時,李安正帶著孩子離開龍船河。他原是想與伍娘一起走,走到龍船河人不知道的平壩子地去,但伍娘不從。覃堯帶人截住李安,要回了孩子,用槍聲送走了李安。舍巴日的儀式繼續,只是少了一個伍娘,多了一個孩子。而那外鄉人,原本就是與舍巴日無關的。
文化的隔膜導致的仇恨與報復,將原本善良的人性都扭曲了。站在各自的角度看,都可以理解和原諒;但若彼此去看,則既無法理解,也無法原諒。這就是文化差異的根深蒂固。每一種文化都有特定的語境,要想與一種文化對話,必先進入其語境。在一種語境下順理成章的,在另一種語境下可能是悖謬荒唐。覃堯在土家人看來是神,在李安眼里卻不是,那么,所有那些關于“神”的解釋,對于李安是講不通的,他對于此地的神和權都是極端蔑視的:“心想伍娘未必有什么大錯,可恨的是那覃堯,倚仗權勢霸人妻子,偏是龍船河的人和伍娘都將他當作神一般對待,真是可笑至極。”
即便彼此相愛的人,也可能因為文化的藩籬而互成陌路,可見,文化的制約力量是何等強大。伍娘是活在人神共在的世界里,沐浴著神的恩澤,過著通神靈的生活,神之于她,須臾不可離。心中有神,如有信仰,進入某種文化的條件,可以是某種信仰,有此信仰,此種文化就成立,無此信仰,則不能成立,李安心中是無神無信仰的,所以,土司文化對他是不成立的。文化的隔膜可能導致一個人的美酒是另一個人的毒藥,在種族隔膜已經成為全球性問題的今天,不同文化之間的積極溝通與彼此尊重,尤其顯得重要。《最后的土司》是對族裔文化差異的一個復雜隱喻,對于文化差異問題的思考達到了一個相當的深度。
葉梅文學視野中的民族元素,除了她的土家族出身,還緣于她的《民族文學》主編的使命意識,這雖然是后天形成,卻已化為她不可剝除的情懷。她的成長和閱歷使她貼近自己的民族,主編《民族文學》又使她走近了其他民族。散文集《穿過拉夢的河流》,涉及三十多個民族的作家作品,簡直就是一部民族文學的感性百科。拉夢,在藏語里是多元、多樣的意思,這本書就是一條五彩斑斕的多民族的河流,沿著這條河流,可以領略到各民族文學的美麗動人。比如,她提到蒙古族詩人阿爾泰的《醒來吧,我的詩》:醒來吧,我的詩/蘇醒的牛奶正愉快地滋人驚醒的牛奶/蘇醒的羊群正悠然漫向惺忪的牧場……一個民族對于生活的熱情洋溢撲面而來。葉梅還寫到蒙古族對于詩歌的熱愛。蒙古族真正是一個有詩性的民族,每一個普通人,都可以在盛大的群眾詩會上朗誦自己的詩歌,一位老人竟因一個小伙子不知道詩歌節而結結實實給他一巴掌,“連詩歌節都不知道?你還是咱蒙古人嗎?”這一切,由一個熱愛民族文學的人寫來,尤其散發出內心的溫度。
地域書寫
葉梅的地域書寫幾乎等同于鄉土書寫。葉梅生于三峽長于三峽,地地道道是三峽的女兒,后來雖已到京城,仍然有著濃重的原鄉情結,三峽的語言、風物、山水草木和人物,都滿滿地充實在她的文字中。“我從小生活在三峽那片土地上,即使走得再遠,也離不開對那片土地的回顧與想象。”葉梅筆下的地域,經常是三峽的龍船河、龍船寨,她的人物和故事,往往出沒于這里。也只有當她的人物與故事出沒于這里時,她寫起來才得心應手。葉梅的龍船河上,還經常行走著一種叫豌豆角的小船,她的人物和故事若是從這小小的豌豆角上激蕩而來,就更是驚心動魄了。
葉梅寫三峽的皂角樹,字里行間透著熱愛。三舅嘎公的土屋前長著一棵青青的皂角樹,像一把大傘,傘下擺著凳和茶。“我們奔跑著從刺目的烈日下撲進那一片蔭涼,頭上捆著白帕子的三舅嘎公提著旱煙袋,會伸手抹一抹我們額前的汗,笑瞇瞇地說:‘喝茶喝茶,灶頭上有燒好的苞谷坨。我和我的表兄妹們,一屁股對著江水坐下,皂角樹下吹過一陣江風,我們咕嘟咕嘟喝下大碗的梨兒茶,啃出滿嘴苞谷香。”
葉梅筆下的三峽人物,對于三峽往往有著難以離棄的愛,比如《撒憂的龍船河》中的覃老大,無論外面的世界有怎樣的誘惑,他始終走不出這條龍船河。
有熱愛就有痛楚,葉梅的《青云衣》寫三峽搬遷,無可避免地浸透著別離三峽的痛楚。三峽移民是一個現實題材,但這卻是一篇略帶歷史傳奇色彩的小說。向懷田和父母居住在三峽,有一天,山體滑坡,家園被毀。向懷田已入贅到嫂子家的哥哥向懷書,此時正在給武昌來的水利勘探隊當向導,乘船時遇見劫匪,向懷書為了保護勘探隊的陶先生等人以及他們的資料儀器,命喪激流。緊接著,向懷書妻子為他生下了兒子向波。向懷田到嫂子家安葬了哥哥,又回到三峽。他要靠個人的力量,在這里重建向家屋場。建屋場的過程中,劫匪的妹妹妲兒出于內疚,女扮男裝來到向懷田身邊,二人相愛,結為夫妻。屋場雖然最終沒有建好,但即便住在巖洞里,也不影響他們的幸福。解放了,他們分得一些富人的浮財,正準備再次造屋,妲兒卻因土匪妹妹的身份而被揪出。盡管妲兒本人并未做過什么惡事,仍然承受不了土匪妹妹的心理壓力,抑郁而死,留下女兒和向懷田。幾十年過去了,向懷田和女兒女婿已經在三峽安居樂業,他們的屋場卻因二三峽工程而即將被淹沒。向懷田不舍,因為這里埋葬著他的父母和心愛的妲兒。但最終,為了千秋大計,向懷田決定將向家亡人請進當年居住過的山洞,然后用水泥封住洞口。他把自己的棺材,連同當年妲兒為自己做的一套青云衣,也一起封進了洞中,并留下遺囑,等他死了,也要睡進洞中棺材里。他要與親人永遠親密相伴,與三峽永遠化在一起。
《青云衣》成功地刻畫出幾個性格各異生動鮮活的三峽人物,寫義薄云天的三峽漢子向懷書和向懷田,筆力峻健,以冷筆寫熱血,令人震撼;寫山野精靈妲兒,筆調靈活多姿,潑灑有致,如魚得水;而寫東方情韻的嫂子,筆力沉穩,體現出默然對弈的小說內功。
《山上有個洞》寫相傳土家族最后的土司——田土司留下一個藏寶洞,此地的土家后裔因此對這個洞都懷有一種崇拜。這個洞很神秘,田土司的后裔、田快活的爺爺田紅軍,跟連長一同跳崖,結果一腳跳進了藏寶洞,這洞口進,那洞口出,革命一場,無人承認。田快活自小在洞中玩耍,那洞就是他的宮殿。目前,田快活是一個普通的農民,最大愿望就是能娶桃子為妻,可是桃子到城里打工去了,對田快活很是看不上。田快活也去城里打工,卻不適應城市,哪怕那只是個縣城,于是他去而復轉。田快活妄想找到洞中藏寶改變命運,也掉進這個洞,一同掉進去的還有村長,田快活的命運因此改變。田快活這一掉,好像也掉進了自己的命運,與爺爺一樣。這篇小說對于山洞和命運的關系,有一些復雜含混的暗示意義。但有一點是很明確的,農民田快活無法適應城市。
《玫瑰莊園的七個夜晚》中,從三峽進城打工的農民馬松,對于城市也是不適應和不以為然的。他看城里人雖然要啥有啥,卻活得冰冷蒼白,沒有過日子的熱乎氣兒,沒有生命元氣,女的像蠟人,男的像燒餅,反而讓他這一無所有的家伙感到可憐和不屑。“這些房子看上去好生寂寞。如果他是主人,不趕緊熱鍋熱灶地讓它們歡騰起來?再如果,他是一個站起來比房子還要高的巨人,他就會彎下腰去逐一撫摸它們,至少用他熱熱的手,暖一暖那些冰冷的房頂。”馬松衡量城市,用的是他家鄉的標準,“這家的頂樓不像他三峽老屋的閣樓上晾放著苞谷、煙葉和辣椒,卻亂七八糟地擱著一些箱柜和舊書報。”這里有一個文化參照的問題,以深懷熱愛的鄉村為參照物來衡量城市,結論是可想而知的。反之亦然。衡量一種文化,首先要選取適用的參照(包括情感在內),否則,無法做出可靠的判斷。小說中,葉梅在城市與鄉村之間的抑與揚的傾向是不難看出的。這篇小說,是葉梅從三峽移植到京城后的產物,這是否同時說明著她本人在移植過程中的不適?這水土不服是否只是暫時的?
如果說,《撒憂的龍船河》和《最后的土司》觸及的是民族文化之間的隔膜,《歌棒》觸及的則是城鄉心靈之間的隔膜。
近幾年,原生態唱法作為一個音樂亮點非常引人矚目,幾乎掀起了一種文化潮流,《歌棒》中,三峽龍船河的農民歌手沙魯就是在這種潮流中被挖掘出來的。然而,在一場重要演出中,他卻突然失蹤了,因為一根歌棒。歌棒就是三峽歌者記歌詞的一根棒,不是用文字來記,而是用只有本人能看懂的一些紋路,他們“用一輩子精心刻畫,任何時候只要一摸,就會想起那些美妙的詞來”。這根歌棒對別人沒用,對它的主人,卻是魂兒一般重要,離開這根歌棒,他們唱歌時就找不到感覺,就會忘詞。
為了尋找沙魯,女主持人芳羅來到了沙魯的家鄉,先見到了發現沙魯的歌師傅,并了解到,歌師傅當年到龍船河采集山歌時,差點墜崖,被瓜子妹所救,二人結為夫婦。可是,瓜子妹原本是沙魯父親的戀人。芳羅來到沙魯的家,見到了沙魯的父親,發現他神神叨叨,嘴里時常蹦出一些歌詞警句。原來,沙魯父親曾經是一個民歌好手,但現在已經“武功”盡失了。
芳羅意外地與沙魯相愛了,這剝除了文化外衣的原生態的愛注定是短暫的,一旦穿上文化的外衣,二人就注定隔膜。“他們本來就是兩個山頭上的樹,永遠無法將根連在一起。”有一段對話耐人尋味:
芳羅說:“你在北京把歌棒丟了,為什么不留在那里找?”沙魯沉默著,搖頭,“那不是我的地方,我一天也呆不下去了。”
“我們弄不過城里人。”他說,“我爹當初就是讓縣城的人給騙去了歌棒,還騙走了情人,才變成那樣的。”
沙魯父親對城里人本能地不信任,是遭遇教會了他防范,然后,他又把這種防范和不信任傳給了兒子。歌棒和所愛的女人,是龍船河歌王的靈魂,沒有了靈魂,他們就不能再唱歌。而偷走他們靈魂的,是城里人。在這里,城市和城市人,是與鄉下和鄉下人對立出現的。前者對后者,構成了對后者的侵害和掠奪;后者對前者,沒有任何好感,只有抵觸和自衛。
沙魯的特殊經歷還需要注意,他是三峽移民,搬遷后不適應,又回到了龍船河,這也是一個把根扎在龍船河的人。葉梅筆下的這一類人物有一個共性,就是他們越熱愛三峽,對外面的世界就越不適應。這里面是否蘊含著一種文化方向上的迷茫?是否存在著一個令人憂慮的文化融合問題?文化的同化風潮已經席卷世界,那些擁有自己獨特文化的地域,將何去何從?某些具有景觀價值的地域,作為文化留存當然不難,更值得關心的,是那些景觀之外的平凡的生存選擇。小說的最后,沙魯的歌棒在城里找到了,芳羅想:沙魯有了這歌棒,會不會再一次走進都市呢?這個結尾隱含著一個良好的祈愿,如果鄉下人被城市弄丟的靈魂能夠找回來,兩者的心靈是不是就能夠消除壁壘彼此溝通了呢?
葉梅筆下那些亮烈的三峽兒女,聚焦了三峽人物身上的三峽性格三峽精神。葉梅之所以能夠托起這些人物,是因為作為三峽女兒,她身上首先就具有這種三峽性格三峽精神。葉梅是一個接三峽地氣的作家,這得益于她的經歷。少女時代,她與一位女同學到偏遠鄉村插隊,兩個城市少女,居然自己在居處養了一頭豬。“沒有豬圈,就讓小豬睡在我們的床下。到夜里,只聽豬兒在床底下打鼾,奇怪的是,不僅不覺得臟和臭,反倒聽來踏實。似乎養了豬,缺這少那的屋子就像個人家了。”后來,葉梅離開了插隊的地方,年底女伴把小豬殺了,送到葉梅家一塊肉,母親說,肉“好嫩好嫩”——這暗示著,那只豬其實還很幼小。葉梅沒吃,“眼前不時晃動著頭子在場壩上歡跑的樣子”。在葉梅的感情中,這只叫頭子的小豬已經成了她的家人。“幸福大隊的鄉親與我們相處有了很深的感情,我前幾年還去看過他們,跟當時在一塊兒打花鑼鼓的兄弟們坐在一個屋場又打了一陣。”這種緊接地氣的樸素情感,在女作家中是少見的。葉梅已經把幸福大隊納入自己的根系,她回到幸福大隊,如同歸省。
插隊生活,在許多作家那里都是苦難敘事,在葉梅這里卻別開生面。“很多同齡人把插隊當作受苦受難,但對我和力勤來說,從極為壓抑的環境里來到鄉下,卻是獲得了一種自由。……農忙時,中午從坡上急匆匆回來,力勤點燃灶里的柴火,我在鍋臺上操持,將南瓜和洋芋切成塊兒,先放點油炒一炒,然后舀一瓢水,蓋上鍋蓋,不一刻香氣四溢,我和力勤一人能吃三碗。下飯的菜則是幸福二隊的鄉親送的酸蘿卜腌菜榨辣椒。再沒有吃過比那更香甜的飯菜。一年下來,我和力勤紅光滿面,五大三粗,能從十幾里外背回七八十斤重的柴火,能挑起百十斤的糞桶。十六歲的年齡,再累睡一覺又會精神飽滿。”一個十六歲的城市少女,卻完全不將鄉下勞動視如畏途,實在難能可貴。這種接地氣的歷世態度,同樣撐起了葉梅文學創作的天空。
葉梅寫仡佬族女作家肖勤從鄉長到副縣長,文學創作的成功離不開常年鄉鎮工作的經歷,她自己其實同樣如此,從副縣長到州局長,擁有豐富的基層領導經歷。葉梅即便去參加一個文學活動,路遇老農,仍然會關心地問起產量,這些細節,可以見出她副縣長的底子。即便在云南蒸塘河一帶觀景的時候,葉梅都會注意到田房:“這房子土墻茅草頂,倚山而建,也算是一個小吊腳樓。樓下是牛舍,樓上放農具和種子等,當地人稱之為田房。瀾滄江畔地勢險要,即便是自家的田地,每天往返也是很費勁的事,因此農閑時將種子、肥料搬到田房來,種地最忙時還可以此為歇宿之地。”這與知識分子型作家的關注點大相徑庭。
葉梅從不拘于形而上的寫作,她的適應性很強,最初寫舞臺劇本,后來寫小說,小說寫得正旺,工作需要,又轉而“嘗試新聞寫作,大量時間在走鄉串戶,配合中心,采寫典型,從不適應到比較適應,寫了一批通訊特寫和報告文學。有的朋友曾替我惋惜,說要是在小說創作上一鼓作氣多好,可我卻從來不為自己經歷過的而后悔。我以為,無論是什么樣的體驗,都是我生命之路的一個過程,正是從那樣一些經歷中,橫看成嶺側成峰,更多地體味到文學的多種滋味。”葉梅的寫作之所以不那么自我,完全沒有知識分子寫作的象牙塔局限,與她對待文學創作的樸素態度密切相關。創作上的包容與豁達,與作家人格的包容與豁達是一脈相承的。
女性書寫
葉梅塑造得較好的男性往往是過去的,她塑造得較好的現代人,則是女人,尤其是三峽女人。
《花樹花樹》開篇就是女人生產,寫得靈異震撼。七仙女附體在巫師覃老二身上,為即將出生的嬰兒看她們的命樹一花樹。難產的女人死去,女兒們在太的撫養下長大。太是個決絕的有骨氣的女人,對于負心的男人,斬截如刀,絕不軟弱,令男人懾服卻步。但不幸瑛女重復了被男人辜負的命運,自亡火海。似乎家中女人的不幸,都是對昭女的試煉,當昭女看到鄉長朱國才皮袍下面揣著的“小”時。當昭女知道這個男人不會選擇愛情時,她立刻鄙棄了他。同時,她也放棄了那個改變命運的公辦老師的名額。當女人最珍貴的愛情都可以被男人放棄時,女人還有什么不可以放棄?她不要別人賜予她一個改變命運的機會,她要自己去創造自己的命運。她說,“我只是想試一試,我依靠我自己的力量,到底能往前走多遠。”這句話,如簡·愛關于靈魂和尊嚴的宣言一樣擲地有聲,且更加有力。回鄉知青朱國才本來不愿做大隊支書的上門女婿,但是,家里因此遭到報復:分糧時明顯被少了秤,評工分時無端矮了一個等級,等等,最后他妥協了。昭女面對局促的命運,卻決不妥協和茍且,也許只有這樣,她的命運才不會再局促。對比之下,女人比男人活得響亮。昭女瑛女的命樹——桃樹李樹在她們出生時就種到了母親的墳上,瑛女死去之后,昭女決計砍掉這兩棵樹,“猶如砍去冥冥之中一只任意主宰的手”。這意味著,她要自己掌握自己的命運。太只能終生守在這個地方,嚴加看管著自己的命運,昭女則要離開這里,對命運出擊。昭女出走時想的是:我會回來的,一方水土養一方人。而且,她要穿過人群,抓住畏葸的大表姐的手。這預示著回歸,同時也顯示出,在女性命運的相互關照中,女性情誼的偉大力量。無疑,葉梅看重女性個體的力量,也看重女性情誼的力量。
《五月飛蛾》中,石板坡的二妹不甘被動接受別人安排的命運,頑強地活在城市里,守望著隨時可能到來的希望,她尋找幸福的決心,簡直可以令命運低頭。
《鄉姑李玉霞的婚事》中,李玉霞主動出擊,把自己出人意料地嫁了出去,她的出嫁不是賭氣,而是主宰生活的自信。粗糲的生活奈何不得她,即使在菜市場賣魚,她的形象也是明眸皓齒的,嗓音也是鮮活嘹亮的:“看那臉上,居然化了淡妝,明眸皓齒地扎一根橡皮圍裙,將一雙紅通通的小手伸到亂毛跟前,果然裂了一道小口,亂毛在一旁樂呵呵地打下手,聽著玉霞的呵斥,兩口子滋潤得就跟那魚和水似的。”她駕馭著男人,駕馭著自家的日子,活色生香地住在自己的命運里。
葉梅筆下的女性總是“有渴望沖破羈絆和束縛而走向新生活的一面”。她說:“我希望女人不要甘于做一個弱者,要在這個光怪陸離的世界里站立著,勇敢地愛和被愛,勇敢地追求自己的理想。……或許潛意識里我們都有張顯女性主義的沖動。”但她的女性主義絕非理念上的,而是行動上的,是不打女性主義旗幟的實實在在的女性主義。
土家族有一首《龍船調》:妹娃要過河,哪個來推我?對于這首傳統的歌謠,葉梅進行了新的闡釋,她說,“在河的對岸,星空閃爍的彼岸,有著女人的希望,雖然河水深淺不一,有著不可知的風起云涌,但過河——是一件多么誘惑女人的事情。……這些要過河的女人,閃動在我的小說里,她們是《最后的土司》中的伍娘,《花樹花樹》中的昭女、瑛女,《撒憂的龍船河》中的蓮玉、巴茶,《青云衣》中的妲兒,《五月飛蛾》中的二妹、桃子、桔子、安安,還有鄉姑李玉霞……她們從遠處走到今天,對命運改變的期許,對渡過河流的心馳神往,女人骨子里的堅韌與無奈,浪漫與現實,溫情與倔強,使她們在不同歲月里卻有著相似的夢想,又因為性格的差異而走向不同的路徑,那載著她們的一只只船兒各自漂流。我凝望著她們,猶如看著我自己的電影。”她更廣闊地認為,是女人過河的欲望鼓舞著男人,推動著世界。
葉梅之所以能夠成功地塑造出這些“過河的女人”,是因為她本人就在一直為理想而過河,無論是作家葉梅、主編葉梅還是女人葉梅,“在做著這樣那樣的事情時,似乎總在趟過一條又一條河流,就如同……‘妹娃要過河。路程很遙遠,但路的前方總閃爍著明亮的光芒,那或許就是理想。”
葉梅評論好友的小說時提到一句話:“現在的文明是讓女性吃虧的文明。”也許正是意識到這一點,她才要反撥這種“讓女性吃虧的文明”,她才要塑造一些不虧的女性。不虧是因為不屈,葉梅以她的內在力量,讓這些不虧不屈得以成立,絕不牽強。她與她筆下的女性,是交相輝映的。“我會不斷寫這些女人的故事,她們會承載著我的以及更多女性的理想。”同時,從這些富有力道的女性身上,能夠看到葉梅的精神之光與人格力量,只有發光的靈魂,才能用自己的光芒照亮筆下的女性。這些女性身上都有葉梅的靈魂,有葉梅自我人格的外射。而我欣賞葉梅,如同欣賞我想要的另一個自己。
葉梅寫自己少女時代來到貧苦的幸福大隊插隊:
“我喜歡這個地方,并沒有因為勞動苦而心生厭倦,相比在城里父母挨斗那種恐懼,勞動的辛苦并不算什么。”由此可見,這是一個要把腸子捋直了、氣兒喘順了的人,寧可受苦,不可受屈。所以,看她筆下的女性,也是氣兒特別順,不憋屈自己,活得要痛快,輸也要輸得亮堂。葉梅敞亮地說,“私下一直認為,女人還是女人來演比較好。因為靠女子的才能,完全能做好表現自己這件事,何苦勞煩男人來費心揣摩呢?男人恐怕更多要揣摩的是如何做好一個男人。”她樸素自然的審美心理,與她身板挺直,活得敞亮的人生姿態是一脈相承的。
葉梅的內在傳承自她的母親,母親與她,構成了三峽土家女性的一個精神母系。葉梅所寫的三峽,就是母親的三峽。三峽的性格就是母親的性格,母親的性格就是三峽的性格,母親與三峽,就像一對互文。母親愛三峽,愛說三峽,到生命的最后階段,還建議葉梅要寫一部關于三峽的小說,即便逝在異鄉,也要把骨灰撒到三峽去。“三峽,是母親最為親切的地方。童年的苦難鑄成了母親剛烈的性格,如同三峽的山和水,時而峻峭時而柔情,她常說的一些話成為我們生活中的座右銘。”(《母親留給三峽的歌》)這位意志力極強的母親,熱愛自由,愛憎分明,豁達剛烈,葉梅無疑繼承了母親的性格。葉梅的母親晚年住到北京密云,仍然丟不下三峽的背簍。而在母親去世幾年后,葉梅在云南昭通買了一個背簍,乘飛機帶回北京,這個背簍對于葉梅和母親,無疑是一個象征。
葉梅有俠骨,也有柔腸。葉梅最愛重的舅舅,儒雅而多才多藝的悄悄寫小說的舅舅,還未戀愛過就意外身亡,幾十年后,已經遠遠超過舅舅當年年紀的葉梅回憶最后一次見面,是雪天舅舅送她和妹妹上船:“最后用那雙沉穩而略顯憂郁的眼睛久久地看著我們。他將一種從容和鎮靜傳遞給了我們。……多年來,總覺得身后有一雙沉穩的眼睛。”其中,既有少女葉梅對舅舅的崇拜,也有年長的葉梅對永遠停留在年輕之中的舅舅的愛憐,是一種柔腸九轉的復雜纖細的情感。
如果從文化上進行細分,葉梅也是一個文化的移植者,她觀照本民族和本鄉本土的目光,既有內視角的,也有外視角的——即嘗試站在外來者的立場上、用陌生化的眼光,來發現自己的民族和鄉土。葉梅民族書寫和地域書寫的些許遺憾,在于她無論是內觀還是外觀,都缺少必要的反思和挑戰性的省視。葉梅女性書寫的些微局限,則在于對女性突破命運的現實基石的構筑,有欠厚實和可靠。葉梅的小說寫作還可以更加內在化、更具個人辨識度一些。也許多年來雖與文學貼得很緊,卻畢竟不是直接進行創作操練以及跨領域較多的緣故,葉梅自身的小說靈性和感性略有鈍化,在以后的專一寫作中,或可得到糾治,臻于完善。
責任編輯 安殿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