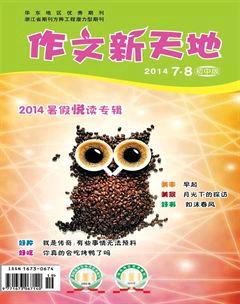旅行的意義
艾小柯
旅行書寫得最好的一本,我會說是英國作家阿蘭·德波頓的《旅行的藝術》。
最關鍵的是他的視角并不局限于所游之地的好,不局限于他的經驗本身,而是更進一步地思考人為什么要旅行的問題。比如他從自己為什么要去加勒比島國巴巴多斯寫起,引出了旅行的預期與現實對比的話題,又從這種對比自然而然地開始討論起旅行的動機。他旁征博引,以令人意外的方式講“大道理”,然而幽默風趣,絕非廉價的心靈雞湯或人生警句的羅列,完全沒有好為人師的自我優越感或傲慢。我很喜歡他談“福樓拜的埃及”。對法國人福樓拜來說,埃及的異國情調與他內心深處對法國的種種不滿有必然的關聯。福樓拜對亞歷山大港繁忙混亂的欣賞,對街市上隨處便溺的人和驢的贊譽,甚至對駱駝的崇敬,都與他對19世紀中葉法國社會裝模作樣古板作風的深惡痛絕分不開。理解旅行的動機,而不單單歸結于異地情調的召喚,是一個自我認知的過程。我們因了解自己而明曉離開的理由,也正因為離開的理由而進一步認識自己。
《旅行的藝術》分五部分:出發—動機—風景—藝術—回歸。每部分有一至兩篇文章,結合德波頓的親身經歷,講述名人軼事或文史故事,挖掘有關旅行的話題。這其中我最感興趣的是關于旅行意義的思考。
講到某件事情的意義,自然離不開預先的期待。對旅行而言,人們之所以甘愿忍受舟車勞頓之苦踏上旅途無外乎為了獲得以下幾點:
·逃離生活的繁瑣與一成不變;
·親歷美好的事物或人物;
·獲取新視角新觀感;
·獲取美(紀念品)
德波頓在《對旅行的期待》一章中講到了法國作家于斯曼(Joris-Karl Huysmans)的小說《流逝》(A Rebours)中的一個人物:德埃桑迪斯公爵著迷于狄更斯筆下的倫敦,心血來潮決定乘火車從巴黎外郊去倫敦旅游。然而他在到達巴黎火車站后,在書店買了本《倫敦旅行指南》,逛了家英國酒吧,在英國小餐館里吃了個便飯,卻突然決定不去了,毅然帶著他的大包小包返回了自己的巴黎郊外別墅,再沒離開。
這位法國公爵之所以改變心意,是因為他認為自己已經從閱讀和酒吧觀察與餐館體驗中得到了他心目中的倫敦,如若真正登車而行,等待自己的也只能是種種失望。公爵先生當然是個夸張的例子,但藝術作品中的遠方與真正遠方存在差別則是千真萬確。我們當然不能為了擔心失望就拋棄旅行,但如何在旅行中收獲更多,這的確不是一種與生俱來的本領,需學習、需實踐,需要“旅行的藝術”。
起點當然是設立實際的期望。簡單點的,不要被種種糖水風景照欺騙,成為旅行社浮夸廣告的犧牲品。更深入的,也許應該問問自己為什么要去旅行,是獵奇,還是散心?是否該指望一場旅行來徹底改變一個人的心境,解決生活中存在的實際問題?
設立了預先期望之后還得注重旅行的技巧。德波頓強調的技巧不是“路線攻略”,也不是“出行指南”,他指的是怎么去真正觀察。在“藝術”的部分,德波頓試圖理解梵高為什么要用一種特別的方式來摹繪法國普羅旺斯省的絲柏樹。他觀察絲柏樹在風中的擺動方式,比較它們與松樹和橡樹的不同。他贊美英國作家、藝術家約翰·拉斯金(John Ruskin),真正按照拉斯金在1857年所著的《繪畫要素》(Elements of Drawing)中所教授的那樣去臨摹自己旅行中所見的景物,態度可謂一絲不茍。在這些親身的體驗與思考中,他總是能找出新鮮的視角,奇妙的解說,就好像他自己總結的,“藝術——只是推波助瀾,誘發出更深刻的感受,使我們不至于因匆忙和隨意而變得麻木”。
也正是因為這樣的細致體驗,德波頓才是一個了不起的觀察者與思考者。在“風景”的部分他寫了兩章:《鄉村與城市》和《壯闊》。前者借英國詩人威廉·華茲華斯的作品來討論大自然對人情緒甚至靈魂的凈化;后者則從他的埃及西奈之旅談起,思考為什么大自然中“壯闊”這一品質會具有非凡魅力。德波頓的“游記”總是將自己的經歷細節與藝術史及哲學思想相結合,書寫所謂“日常生活的哲學”。他常讓我覺得自己看世界的速度太快了,讓我想像他一樣慢下來,慢下來,仔細觀察,踏實描寫。比如我第一次去加勒比海,在墨西哥科蘇梅爾島頭一次體會清澈見底的湛藍海水時,只是在碼頭上激動得不能自己。如果我也能像德波頓那樣停下來,問問自己為什么看見美、體會美能讓人感動地流淚,或者細致描繪海水的顏色,那些泛著不同反光的藍的層次,船與桅桿在海面上的倒影,水下橙黃而具波紋形態的沙粒,與水波相依相戀的天光云影,那么我也將不僅僅在旅途中找到景致,還有可能通過景致找到我自己。
對我而言,《旅行的藝術》中最關鍵的一章是《對美的擁有》。德波頓并沒有從道德層面去譴責在名勝古跡上刻下“某某到此一游”的行為,而是話鋒一轉,介紹起拉斯金的生平來。拉斯金相信學習繪畫的終極目的并非成為藝術家,而是觀察,養成對生活細致、準確的觀察習慣,因觀察而發現圍繞我們的豐富細節,發現美。“只有一種辦法可以正確地擁有美,”拉斯金認為,“那就是通過理解美,通過意識到那些促成美的因素(心理的和視覺上的)而擁有美。最后,追求這種有意識的理解的最有效方法是通過藝術、通過描寫或摹繪去嘗試描述美麗之處,不管他是否具有任何的藝術才華。”
拉斯金在講繪畫,德波頓談的是旅游,但他們所言的這一切卻和日常生活的細節息息相關。難怪我第一次享受到旅途的樂趣是因為在江南游之前借了《孤獨星球中國游指南》一書,做足了功課,有意識地計劃了旅途中的期待;難怪我從開始記錄卡特里娜颶風的逃難經歷起就停不下筆,新地點,新人物,電影、書籍,一盆花、一道菜、一首歌,我原來都是在試圖描繪美、理解美啊,試圖理解那些促成美的因素,從而擁有這些了不起的美的品質。
我想德波頓唯一沒有提到的一項旅行的藝術是“意外”。《旅行的藝術》最后一章獻給“室內旅行家”法國人塞維爾·德·梅伊斯特。梅伊斯特寫了《我的臥室之旅》和《臥室夜游》兩本書,意在“將我們從被動狀態中喚醒”(shake us from our passivity),將“旅行心境”(the mind set we travel with)運用到日常生活中。這種“旅行心境”德波頓覺得主要是“接受力”(receptivity)。之后他模仿梅伊斯特作“街區之旅”,也是講述如何在日常生活中運用“旅行心境”,實現旅行的意義。
然而我依然覺得有些感受與成長要求人必須被放入陌生的環境,接受不一樣的視角,才能終于“打破盒子”,尋找到連自己都毫無頭緒的寶藏。
美國導演韋斯·安德森(Wes Anderson)在2007年的電影《穿越大吉嶺》(Darjeeling Limited)中講了懷特曼三兄弟去印度坐“大吉嶺號”列車尋母的故事。大哥弗蘭西斯對行程安排可謂精心備至,甚至專門雇傭了一個私人助理,每天清早將需要參觀的景點廟宇打印成文,塑封壓模從門縫里悄悄塞進三兄弟的頭等包廂。然而周到的安排并沒能使三兄弟的隔閡減少,他們不得不忍受彼此的臭毛病——大哥的獨斷、老二的陰郁,還有老三的神經質。他們甚至各懷鬼胎打主意臨陣脫逃,直到被意外踢下火車,助理辭職,所有計劃安排亂作一團。可正因為這場意外,三兄弟搭救了兩個落水的孩子,參加了一個印度風俗的葬禮,旅途中久尋不遇的心靈滌蕩竟不期而至,直到每個人終于甩掉包袱找回自己。而我十年前的江南行,記憶最深刻的也是在杭州“被騙”,才意外領略到了煙雨龍井,嘗到了最純美的綠茶。
我始終相信,人在旅途里最令人刻骨銘心的,總是一次次的意外、偶然、驚訝,甚至挫敗、錯誤、失去。旅行的意義從不在旅途本身。千山萬水,都只為了轉身回程的那一個背影,只為了讓我們從他鄉終于奔赴故鄉。
然而,這大概就是另外一本書了。
(選自《流浪者的鄉愁》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3月出版)
[鏈接:]
《旅行的藝術》
作者:[英]阿蘭·德波頓
出版社:上海譯文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2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