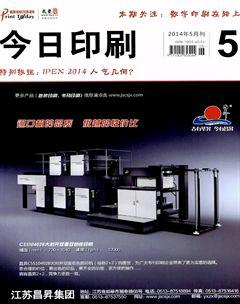改行還是轉型?
呂理哲
報紙經營的困難我們可以想象,因為我們都在相同的出版印刷行業。報紙和印刷廠都需要改變,轉型已經是產業共識,不再是先知先覺的智慧。
問題是如何改變才值得一試呢?恐怕沒有典范可循。以往有報社企圖強化網絡內容來轉型,卻解決不了收費閱讀的問題,也有企圖開創一個完全沒有紙張的平板電腦專用電子報的報業集團,最后還是鎩羽而歸。
那先生曾介紹過各式各樣的報紙改革或是創新,即使有成功的案例,卻不是其他報社可以模仿的。
印刷廠的轉型似乎也有類似的現象,臺灣的合版印刷企業開始于2000年以前,到今天具有持續發展潛力的幾個范例已經成為超大規模、超高效率的印刷服務引擎。但一般的印刷企業實在無法那樣轉型,一方面是這種規模不是短時期可以創造的,而是要日積月累慢慢形成,另一方面是2000年以前的時空背景和今天已經有了天壤之別。
轉型如果一味模仿而沒有創新,那么一定有問題,因為別人當時的“創新”到了今天早已經成為“老生常談”,這些成功企業今天的規模和效益或許可以用金錢打造,即使全部照抄,可是一天幾千甚至上萬張的訂單量如何模仿?
所謂創新,一定是發掘產業供應鏈(不管是出版還是印刷)某一段的“無效益”,利用科學的方法去彌補,如果彌補得有道理就能創造價值,對自己的企業有價值,就對同行一樣有價值。今天的移動通訊技術太強了,你的價值很快就會傳遍整個產業。轉型的思路如果不是這樣的邏輯,再強大的技術或資金的投入皆是枉然。
為了自己賣書,亞馬遜在世界各地安裝了無數電腦和寬帶,獲得了全球各地亞馬遜賣書的效益。世界各地的企業都想上網賣東西,同樣需要電腦和寬帶,找上亞馬遜,利用其已經成熟的網路平臺來運行自己的軟件,于是亞馬遜成為云平臺的“始作俑者”供應商。
合版印刷因為解決了名片印刷市場的“無效益”,許多印刷廠再自己印名片就沒有效益了。虎彩文化的按需印書平臺解決了少量印刷書的“無效益”,大部分出版社自然都把剛出版書的第一次印刷交給他們,以免印太多本賣不掉而變成庫存。
為什么不考慮為終端客戶解決問題?
移動通訊時代的產業創新也不例外,都是幫助同行解決某種“無效益”。以前各行各業不論技術或服務都達到某種程度的成熟,最終客戶的需求早在前面十幾年的數字化或服務自動化的競爭中被滿足了。加上通訊效益越來越高,一定有滿足客戶需求的好方法或好做法,產業內相互模仿,最后一定變成業內服務的標準,甚至成為基本條件。這也是客戶要求多些服務而不愿意多花錢的原因,因為你不提供這種服務,只能去隔壁找一家愿意提供這種服務的印刷廠。
如果以創新的效益去服務同行,這個問題(要求不花錢的服務)就沒有了。合版印刷為同行印刷名片“有效益”,其他印刷廠即使不愿意把活讓別人去做,效益也會讓他們失去選擇的余地。
富士康幫蘋果生產iPhone和iPad,也幫小米生產手機,還幫許多電子產品品牌制造產品,產量數以億計,即使毛利只有1%,加起來也有上千億的獲利可以期待。假設你也很會制造電子產品,但是你的產能規模太小,那么沒有15%的毛利便無法生存,那就永遠搶不走富士康的活。小米運營團隊常常感謝富士康幫忙生產,讓他們卓越的行銷技術發揮功效,不至于沒有低制造成本的產品可賣。這樣你就知道為什么你沒法和富士康競爭了。
富士康服務IT產業同行,“合版印刷”服務印刷同行,超高效益服務同行讓生意做不完,規模得以一再擴充。
不論是印刷廠還是報社,都應該思考有什么“無效益”需要解決,越早被自己解決,再提供這種效益給同行,就能復制成功的秘訣。
國外報社以前認為轉型就是經營網絡內容,結果許多大報社賠了夫人又折兵。如今有不同的科技新貴帶來了不同思維,進入傳統報業的經營團隊,只要仔細觀察他們是否真的找到傳統新聞傳播的“無效益”,否則等錢燒光了,也不過是一場游戲一場夢。
離開了效益的因素,所有的轉型都會出問題。例如,商業印刷想要轉型包裝印刷,看起來難度較小,如果沒有找到包裝印刷的“無效益”缺口,也不過是從油鍋跳出來再掉進火坑。
去考慮提供已經存在的服務,還不如費心去考慮包裝合版印刷的生意模式。合版一定可以把包裝的最少印量壓低,彈性地把交貨期縮短,未曾不是“無效益”的缺口。
商業印刷想轉型包裝印刷,何不先去看看“嶄新盒子”這類為包裝合版印刷設計的軟件,從“效益”這一點發想,轉型才有道理。
轉型不是改行,只有效益才是突破點,才符合邏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