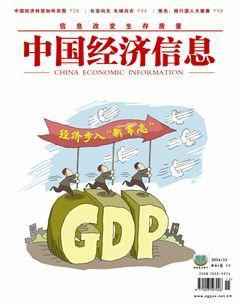中國經濟轉型如何突圍?
陳芬
中國改革穩步前行,但增長放緩的陣痛困擾中國經濟,轉型升級在這種情況下也就變得頗為復雜。
中國的改革開放如果從1978年算起,已經走過36年了。36年前,中國一年的國內生產總值只有3645億元。在1978年,全國城市人口年均收入只有430元,而那時候農民一年的收入更少,只有133元。這三十年來,中國經濟取得了偉大的輝煌成就,一方面我們要看到這個成就;另外一方面,我們還要看到,三十多年來累積了更多深層次的矛盾和問題。
當前,中國經濟發展中很多問題的出路,總會歸結為“經濟要轉型”,但最大的問題是:經濟轉型,知易行難。怎么找準轉型方向?如何真正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到決定性作用,激活實體經濟、激發創新活力?
2014年是深化改革的開局之年,經濟轉型面臨的矛盾、困難和壓力彼此交織。從簡政放權,真正發揮“市場”的作用;到擺脫土地財政,實現投資渠道的多元化;再到廣受熱議的產能過剩、過度投資和地方債等問題,經濟轉型面臨重重壓力,轉型的深刻性、復雜性、艱巨性前所未有。
在7月8日由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經濟之聲主辦的《大國大時代》系列時事報告會上,對于經濟轉型中的矛盾和破解之道,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魏建國、國務院參事室特約研究員姚景源、安邦集團副總裁賀軍、日本大學商學院終身教授李克等嘉賓就紛紛給出了不同角度的見解。
溯根源
產能問題何在
顯然大家知道,我們要想解決經濟中深層次的矛盾問題,根本途徑就是轉方式、調結構,那么,怎么來看這個問題呢?國務院參事室特約研究員姚景源給出了自己的回答。
姚景源 我們的增長方式和結構究竟出現了什么問題?中國的第一、二、三產業出現了什么問題?
從農業上說,盡管我們的糧食十年來皆豐收,去年糧食總產量達到12038.7億斤,但是進口糧食還是超過七千萬噸。總書記講,我們十三億人口的飯碗要端在自己手里,這不單單是我們的國家安全問題,而且從實際上講,全世界也養活不了我們十三億人。
從工業上說,中國的工業確實很“大”,但大而不強。現在我國已經有281種重要工業產品的產量排名世界第一,去年中國設備產量占世界總產量的60%,造船占到世界產量的40%,汽車占到世界產量的25%。但是,我們整個工業還是處在國際經濟的下游。我們的工業領域還缺少核心技術,缺少創造。
從第三產業上說,我國第三產業在整個國民經濟比重中占46%,如果和美國的80%比,我們接近低一小半;全世界平均水平是60%,我們現在比全世界平均水平還低了14個百分點。第三個產業比重如此之低,直接影響民生。第三產業能夠保障我國就業的結構調整。
求破解
攻克轉型難關
轉方式、調結構的問題,我們已經講了十幾年,但為什么到現在依然把它當成一個主題呢?這是因為十幾年來轉方式、調結構的成果還是不如人意。轉型的難點在哪里?應該怎么做?
姚景源 中國經濟增長在過去的長時間里都依賴出口、依賴投資,對世界經濟的依賴度過高,所以從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到2008年的世界經濟危機,發達國家一有病我們這里就受影響,中國經濟一直處于世界經濟波動的深刻影響當中。
我國有限的資源使得我們難以支撐粗獷的生產模式。我國石油要靠進口,鐵礦石一多半要靠進口,單位能耗是世界經濟平均水平的2.2倍,比日本更高。另外在環境上,比如大家都知道的霧霾,現在中國環境已經是整個華北、東北、華東、華南都存在嚴重的霧霾,這種資源環境不可持續,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必須要轉方式、調結構。
我覺得,第一,一定要發揮市場的決定性作用,把轉方式、調結構交給市場,讓市場能夠真正成為我們轉方式、調結構的根本力量、絕對力量,我們的經濟轉型才會有一個根本的、強大的動力。
第二,要打破地方保護主義。一些地方為了招商引資,就采取了一些不公平的措施,比如說你到我這兒來投資,我不管你是什么狀況,你要投資,我給你免稅、撥款等等,一系列的章法都迫害了市場機制。各地按照自己的方式調結構,這是偏袒。
第三點,我覺得中國經濟轉型的主角是企業,我們應該把轉方式、調結構這種艱巨重擔交給企業。要減少政府對轉型的不斷干預,要讓企業成為轉型的主角,政府要做好應該做的事,發揮它的積極作用。政府應當做什么?就是要創造一個良好的社會環境、法律環境、經濟環境,輿論以及文化環境,這樣我們才能夠取得良好的成績。
怎么看
辯證看待“GDP”
在歷史中,大家都覺得日本是近鄰,是一個我們很熟悉的國家,但實際上,中國現在對于日本的了解可能遠遠差于對美國和歐洲的理解。中日管理學院院長、理事長,日本大學商學院終身教授李克以日本為參照性案例,從此入手,解讀了為什么要轉型升級的系列問題。
李 克 上世紀九十年代日本經濟出現泡沫,進入長達二十幾年的衰退期。但只要去過日本的朋友,沒有感覺到日本的衰退狀態。我們一直說,日本是東亞模式最初的創造者之一,我們經常把日本的模式作為中國發展的一個參考,比如說大家都提到的美日的出口導向。
但背后我們看到有一個很要命的問題。前一段時間,我和林毅夫老師,張維迎老師在交流,提到一個問題就是:說經濟增長,中國確實在二戰以后創造了一個世界唯一的奇跡,連續三十年的GDP快速增長,平均年增長率達到9.8%。但是,為什么到現在為止,我們出現了國富民窮,越是發達地區、沿海地區,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的比重越小,這樣一個很奇怪的現象。
2012年,我們連續做了幾個課題,就是分析中國大中城市的經濟結構。姚景源老師講的話我非常認同,真正轉型升級要把政府、市場角色確定清楚,要把政府無端伸向市場的手、伸向資源的手砍掉。這個話說起來非常容易,但是需要考慮政府在經濟層面上到底起了什么樣的作用,如果說不去深入考慮,而是很籠統地看市場,還是解決不了問題。endprint
2011年,中國在全球經濟中排名第二,在日本,有很多媒體采訪我,我說對此我當然很高興,證明我們的祖父輩也有貢獻。很多曾是計劃經濟體制下的資產,在改革開放中,逐步地商品化、市場化、價格化。這確實是幾代人共建努力的結果,值得驕傲。但我覺得又不值得興奮。為什么不值得興奮?因為單純從GDP的角度來講,我們有幾千年的發展歷史,在清朝嘉慶年間我們的GDP就占到全球總值的35%左右,遠遠超過今天的美國。但是,GDP這個指標本身有很大的問題,特別是在體現軟實力的方面,還有很多沒有商品化的、沒法計量的因素沒有納入進來,我們不能對GDP走火入魔。
公平競爭
不要讓市場化離開中國
中國改革開放36年,從計劃經濟時代轉向市場經濟時代,在人類歷史上確實是有著非常大的貢獻,但是下一個時代該怎么走?安邦集團合伙人、副總裁,高級研究員,智庫學者賀軍認為,不能讓市場化離開中國。
賀 軍 可能在很多的方面,中國的市場化還不盡如人意。以制造業為代表的經濟形態講,我們認為中國經濟處在世界工廠的1.0時代;在未來,我們要向2.0、向3.0時代發展。在前進的路上有很多國家或地區的樣板是可以學習的,比如說韓國、中國臺灣地區,還有日本、歐洲,經濟創新能力最強的美國,都是我們前進的目標。
未來中國不能遠離市場化。過去十幾年,特別是中國進入WTO之后,中國的經濟進入了黃金的十年,這十年當中,我們的GDP大概增長了300%,在全球經濟中也變得舉足輕重。但是中國經濟的質量,還有中國人民的福利水平,包括幸福感,這些卻沒有同步提高。
這里面最大的差別是什么?是我們沒有戰略,我們沒有構建市場化的制度。中國經濟受政府和政策的牽引,誰是市場的主體?在成熟的市場經濟當中,不應該是企業,而是市場本身。但是在中國,很多主體不是市場,不是企業,而是政府,政府對資源控制的影響力是比較強的。
比如說,對中國經濟歷次的刺激或者是低谷波動期,實際上都和政策有關系,1992年之后,中國經濟經歷了一個快速的發展,鄧小平同志南巡之后,掀起了改革開放的高潮,政治上的意義是很偉大的,從經濟的角度來講,把所有人的熱情都激發出來了。在中國,沒有政府推動的話,我們確實也很難有這么大的發展。但是到了目前這個階段,我們要靜下心來好好地思考,政府在這個過程當中到底參與了多少。比如在金融領域,從產業獲利來看,從最高端的金融資源,到金融的服務機構,再到制造業這個產業鏈,一直往下捋,我們可以看得到,中小企業尤其是制造企業,它們的發展是非常艱難的。
創新之路
要正確看待“創新”
對于最近被熱議的創新經濟,李克教授也表示要從不同的角度看待,要辯證地看待,不能為所謂的“創新經濟”蒙蔽了雙眼。
李 克 “創新經濟”這個概念沒有錯,這個思路作為戰略方向,包括細節上,我覺得都沒有問題,只是操作模式有問題。比如說,大家到全國各地轉一轉,到處都是科技園、創新園、留學生科技園等等,都是政府主導的這種形式。我聽很多朋友講,國內現在很多園區基本上都長草了,而且一個更重要的問題是,從這些所謂的模式和方式上看,人們根本不知道什么叫現代國際產業園。搞創新跟搞科研是兩碼事,研發出的產品可以達到國際一流水平,但是做出這個東西后,市場能不能接受,產業鏈能不能做大,還是有十萬八千里的距離。
研發出的東西能不能形成最終的品牌,能不能走向國際,能不能在國際上走向中高端,這都是一道一道的門檻,豎在你面前。如果在這種高風險的領域當中,動用大量的國家資源,去全國性地推廣所謂的創新經濟,在模式方面也是以政府主導的方式來做,后果會怎樣?我想不用說大家也知道,這就是某種形式的“大躍進”。
在行業的發展過程當中,沒有所謂的“發展工業”、“發達工業”——這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帶有誤導性的概念。很多人問我:您覺得未來十年哪些行業重要?我說我個人看好三大行業,農產品、能源資源、水,這里面沒有一個大家所說的高科技行業。產業發展的關鍵是要不斷地深挖,追加技術含量。同樣是農產品,有人就可以做出各種各樣的衍生品,就是看有沒有加工開發的能力。
專業化
走“精細化道路”
如今,在經濟增長主要靠投資、出口拉動轉向靠消費拉動的過程中,外貿行業應該如何轉型升級?曾經擔任商務部副部長,長期關注外貿領域的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魏建國先生認為,中國經濟應該走“精細化的道路”,并要參與到世界貿易和投資規則的制定中。
魏建國 前段時間,德國總理默克爾在中國訪問。中國、德國,這兩個國家都重視實體經濟,都重視出口。這兩個國家有大量的外匯儲備,同時這兩個國家現在面臨的問題最多,面臨的社會責任最多。
中國經濟轉型的一個關鍵在于企業家思路的改變。當下中國的現狀很像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期的德國,經濟上比較粗獷,發展所依靠的是勞動力的低成本、高污染和高能耗。中國制造要走到世界制造業的高峰,必須要走一套精細化的路,既要依托產品的精細化,也要依托人的精細化。德國曾提出用國民經濟收入的35%來培訓德國人員,所以德國的鉚工、鉗工、焊工、包括電腦操作人員都非常專業,這是來自于企業家的精細管理。
企業真正把服務做好,做到精細,就成功了一半。有人問我那另外一半是什么呢?我個人認為,就是社會公益事業。企業轉型不要以利益為主,而是要以老百姓為主,以生態為主,以我們的和諧幸福為主,以為子孫留下的家園為主。
精彩激辯
精細化服務
在美國,星巴克公司的老總曾跟我說,咖啡不是一個很簡單的東西,星巴克賣的不是咖啡。我問賣的是什么,他說是服務——只要客戶一進門,他就知道這個客戶要在這兒喝短時間的咖啡還是長時間的咖啡,是想看報還是跟客戶聊天。我從心里佩服他,這些是我們要借鑒的。
——魏建國
不斷創新
全世界的手機大多數都是在中國生產,可是在中國生產的蘋果手機的利潤,美國拿到其中的49%,日本拿到30%,韓國拿到11%,剩下我們有多少呢?只有3.63%。所以大家可以理解習近平總書記講的,我們現在最重要的任務就是創新,創新,再創新。
——姚景源
制度建設
我們在經濟高速增長的階段,忽略了很多建設,包括制度建設,包括政府和市場的關系,還有各種各樣的市場制度的建設。當經濟特別好的時候,每一個人、每一任政府、每一個企業,都覺得自己是經營發展的天才,但是當臺風過去后我們會發現,很多都變了。
——賀軍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