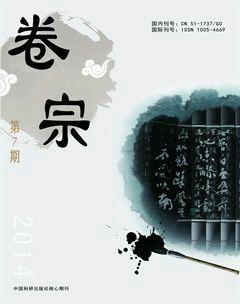論民主與多數人的暴政
摘 要:民主使得社會里部分人的利益得以充分實現,然而另外一部分人的利益又該如何保障?民主在運行時,多數人的意志在投票中成了人民的最高意志。民主伴隨著國家與階級社會的誕生而產生,是人民追求利益的形式與手段,帶著政治的鐐銬披著自由平等的外衣,民主真的有如此美好以至于讓人為之上下求索?本文主要從批判與反思的角度研究民主看似平等的光鮮外表下實質暗藏著多數人的暴政的威脅。
關鍵詞:民主;多數與少數;多數人的暴政
1 什么是民主
在普遍的意識里,民主就是“人民做主”、“主權在民”,人民是公意的代表,任何一種權力都無法凌駕于人民意志之上,一個由絕大多數人統治的國家,則被叫做“民主的國家”。民主一詞要追根溯源到古希臘的雅典時期,這個孕育了民主制度的搖籃,最早開始實行了公民大會和五百人議事會制度,是踐行民主這一概念的最原始最古老也是最基礎的形式,奠定了現當代民主制度運行的基本模式。隨著雅典城邦的建立,這個海洋文明催生而出的國度迫切需要一種管理整個城邦事務的方式。在小國寡民的城邦特色下,城邦事務的管理是由公民參與公民大會投票表決從而最終做出決定,這就是雅典城邦孕育出來的民主。這種民主,一開始就是伴隨著國家的形成而出現的,也隨著階級社會的形成而出現的,因為國家與階級社會涉及到國家權力即主權的行使。民主,就在這種政治背景下誕生了,因此民主一開始就是政治的產物。
“從階級社會形成以來,‘民主一詞的本意是多數人的統治,但這個多數,在一切實行民主制的剝削階級類型的國家,只是一個相對的多數,而不是就一個國家的總人口來說的絕大多數。”雅典的民主有著很大的局限性,它屬于公民的民主,而公民主體的界定僅限于成年男性公民,婦女、兒童和外邦人員被排斥在公民主體之外。因此,由公民大會決定的城邦事務也僅符合部分公民的利益訴求。而且,當時類似上議院的雅典最告法院已經喪失了大部分權利,除了審判殺人罪,其全部作用已被五百人議事會、市民大會和法庭所取代,這些機構所有的成員都是享受俸祿的國家官員,全都通過簡單的抽簽選舉產生。
伴隨著政治而產生的民主是否有其最原始最純粹的內涵?劉瀚在《民主與專政》一書中提到了“原始社會的民主”,原始社會沒有階級、沒有私有制、沒有國家、沒有法律,世代相傳的習俗和慣例便成了其處理公共事務和解決爭端的準則,這是當時“民主”的方法。恩格斯稱之為“自然長成的民主制”,列寧則稱之為“原始的民主制度”。但是這種原始的約定俗成的公共事務的處理方式在蒙昧時期并不能稱之為“民主”,當時國家還沒建立,并沒有所謂的主權,更沒有主權行使的糾紛,故不能將之視為民主的原始狀態。民主帶有濃厚的政治色彩,甚至國家的色彩,它的產生既不純粹,也不美好,只是那些所謂的“大多數人”尋求利益的手段,是披著自由平等外衣帶著政治鐐銬的怪物。
2 破碎的民主
早在希臘城邦運作時,對民主的批評、懷疑就絡繹不絕,在民主投票處死了蘇格拉底之后,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人對民主更加充滿了警懼和戒備。柏拉圖鼓吹“哲學王”的理念,本質就是在抵御民主制度;亞里士多德提醒人們,民主是由很多缺陷的制度,必須對它時時保持警惕。這句話的現代版本就是丘吉爾的名言:“民主是個不好的制度,但是,還沒有發現比它更合適的制度,所以我們不得不用它。”
修昔底德后來在提起伯利克里時期的雅典時寫道的,民主只是虛有其名,雅典實際上是被第一公民統治著。民主名存實亡。“國家應該是公民的仆人,而不是相反。”國家與公民之間如何達成平衡,這是一個復雜的問題。并不是“民主”二字就可以簡單地進行無縫協調的。國家僅此是一個由公民創造出來的統治工具,倘若喧賓奪主,卻還要用一種誰也說不清楚是非的方式(民主)去維系,使其之間不至于崩解。這種不充分的民主逐漸露出了破碎的痕跡。社會里的每一個自然人都該享有的平等權利,正如馬克思所說的:“每一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自由發展的前提。”在這個實質上是分層的社會結構里,何以憑證多數的意志就是對的,少數人的意志就是“異端”?
現代資產階級民主專政的形式,主要是代議制。代議制是工業革命的產物,隨著新興階級的壯大,其政治訴求的強烈,議會成了代表人民醫院的地方。這是一個新興階級的代表,卻不是全社會各個階級的代表。而那些底層階級人民的意愿就此被代表,也就是說,他們的民主權利被代表了。英國資產階級學者狄龍曾經吹噓:“英國議會除了不能把男人變成女人或把女人變成男人之外,任何事情都能辦到。”
因此,盧梭便站出來了,他認為主權在本質上是公意構成的,是至高無上的、不能轉讓、不可分割、也不能代表。他極力反對分權論和代議制的間接民主,他說那樣會把主權者弄成“一個支離破碎拼湊起來的怪物。”“‘代表會使人這個名稱喪失尊嚴。”“如果英國人民自以為是自由的,他們是大錯特錯了,他們只有在選舉國會議員的時候,才是自由的,議員一旦選出來之后,他們就是奴隸,等于零了。”
民主應該建立在平等之上,人與人之間不應該加以互相影響和牽制。但民主的政治制度的初始就已成了一個幌子,它不能等同于平等與自由。卡藍默在《破碎的民主》一書中說到:我們生活的世界正在發生著深刻而巨大的變化,這些變化迅速地擴張蔓延,時時刻刻都在改變著人們的生活方式和社會秩序,而普羅大眾和這個世界的權利階層卻仍然在舊的價值倫理和管理體制中抱殘守缺,世界已經面對著公共倫理和公共治理的雙重危機。
工業革命帶來的不僅是強大的生產力,也帶來社會的分化,民主在這個金字塔的社會結構中逐漸成了社會矛盾的始作俑者。就民主選舉來說,看起來,選民是上帝,然而實質上,選民只是投票的工具,他們在大眾媒體的輿論和政治家的演講鼓吹中會迷失自我判斷的能力;政治家們選舉時為拉攏選票的信誓旦旦,在選舉之后,他們的承諾絕大多數都是被扔在一邊不能兌現在空頭支票。民主的泛濫和限制性,是當今民主制度需要反思的。
3 民主與多數人的暴政
托克維爾在《論美國的民主》一書中寫到:“我最挑剔于美國所建立的民主政府的,并不像大多數的歐洲人所指責的那樣在于它的軟弱無力,而是恰恰相反,在于它擁有不可抗拒的力量。”托克維爾將這種多數人在政府中掌握的絕對權力和多數人行使的無限權力,以及多數人以壓倒性的意見對少數人意見的壓制,形成新的專制的現象稱為“多數人的暴政”。民主在發展過程中,代表民意的所謂“人民代表”和“議會代表”們往往以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進行公共事務的抉擇、法律法規的制定等。多數人的統治成了絕對的、必然的、不可否決的,而這種被扭曲了的民主成了新的一輪社會矛盾沖突催化劑。
民主過分的注重集體的利益,而忽略了個體的利益。在中國,最典型的時代即是文化大革命時期,那是一場多數人對少數人毀滅性壓迫。那個時代里的民主破碎與扭曲成多數人與少數人的對抗,一種不共戴天的對抗。多數原則的民主缺乏彈性,容易形成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價值觀,缺少包容性,是政治化背景下政客尋求利益的手段,卻以“自由”的名義橫行霸道。
多數人不代表著正確,少數人更不能輕易被斷定為“異端”,如果民主成為了多數人意見的集合,那么這必將成為多數人的暴政。民主過程中的“少數服從多數”越來越被質疑,少數人也是享受民主效益的合法人,為何卻以多數人的表決通過使其成為民主破碎裂縫下的受害者?
蘇格拉底就是在多數人的公投下被賜予毒藥而死的,也正是由此引發了之后柏拉圖等人對民主制度的反思與批判。茨威格筆下的《異端的權利》描寫的正是“多數人暴政”下的日內瓦宗教改革時期,加爾文的極權統治。“一個國家將被轉變成一個僵硬的機構。不可計數的心靈,有著無盡情感和思想的人們,將被緊緊地壓縮入一個無所不包、獨一無二的體系中去。”在當時極權統治低下,日內瓦這座晦暗的城里大都是加爾文的追隨者,他們不容忍也絕不允許任何異于加爾文思想的激進分子的存在,多數人統治的城池里,少數人的意志被踐踏甚至烈火焚焚燃燒在十字架下。這種多數對少數的侵害是所謂的“民主”帶來的致命性的結局。在多數人的意志下,少數人被民主欺騙得似乎麻木茫然。這是民主在宗教改革時期的破碎和扭曲。
羅素所言,須知參差多態方是幸福本源。人天生是政治的動物,而民主作為政治的產物,是人們尋求利益的手段,但不是唯一必然的手段,它有其扭曲與不足,其運行中少數人利益的真空必然使人們開始對民主的合理性進行批評與反思。任何事物都不會是永恒的一層不變的,這當然也包括我們所追求的民主,正如丘吉爾所說:“民主不是一個好東西,但目前還沒有找到一個比它更好的東西。”
參考文獻
[1]劉瀚.民主與專政[M].第2頁.北京:法律出版,1987
[2](英)伯特蘭·羅素.西方的智慧[M].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0
[3]馬克思,恩格斯等.馬克思恩格斯選集[M].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4](俄)列寧.列寧選集[M].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5](法)盧梭.社會契約論[M].第37頁.北京:商務印書,1961
[6] 同上
[7](法)皮埃爾·卡藍默.破碎的民主[M].第四頁.北京:三聯書店出版社,2005[8](法)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上卷)[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
[9](奧)斯蒂芬·茨威格.異端的權利.第二章. 北京:西苑出版社
作者簡介
黃怡娜(1993-),女,漢族,福建泉州人,現為四川農業大學文法學院政治學與行政學專業2011級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