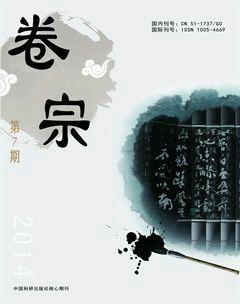父權化的“經濟家長制”:非農化農村家庭中夫妻關系轉變的一個視角
李鍇
摘 要: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廣大的農村地區在工業化和城鎮化等社會宏觀變遷的影響下,正在經歷著一場劇烈的“非農化”變革。在不同程度地擺脫了延續千年的“小農”生產方式后,這場變革對農村家庭的家庭關系、家庭功能及家庭結構也將產生顯著影響。筆者在河南省Y市M鎮C村的田野調查時發現,由于C村非農化后形成了趨于固定的產業結構,使C村男性與女性在經濟收入和家庭地位的獲得上產生了不平等,雖然相關研究表明非農化家庭成員間的關系正向著經濟獲取能力為導向的“經濟家長制”轉變,但在C村,“父權家長制”和以此為基礎的夫妻關系并未發生實質變化,而是朝著父權化的“經濟家長制”的方向轉變。
關鍵詞:非農化;家庭關系;父權家長制;經濟家長制
1 問題的提出
根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2012年末全國人口統計數據,目前我國鄉村人口占全國總人口的比例為47.4%,約為6.42億人。如果按照1998年“現代城鄉家庭研究”中的家庭人口數據來計算(即使取家庭人口上限),我國目前至少也有1.6億戶農村家庭。如此數量的農村家庭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可能產生的影響將難以估量。研究社會宏觀變遷中農民群體和個體的生存狀態一直都是社會學領域的重要課題,而非農化作為改革開放后的出現的新現象,其產生和對農村家庭的影響一直受到廣泛關注。
長期以來,我國農村家庭中的夫妻關系是以男性家長事權統一,掌控家庭各種錢物資源并與其他成員形成主從型關系為特征的“父權家長制”為基礎的。但隨著婦女參與經濟發展和父系父權制家庭制度的逐漸瓦解,婦女在家庭中的地位提高和對其作用的認識逐漸明晰(楊善華、沈崇麟,2000:46)。但筆者在對河南省Y市M鎮C村進行田野調查時,發現以父權家長制為基礎的夫妻關系的改變可能并非是實質性的。筆者試圖對C村家庭夫妻關系進行分析,意圖了解男性家長與妻子的主從關系否發生了本質變化。
2 研究假設和研究方法
2.1 研究假設
隨著非農化進程提速,相關研究者(金一虹,1998;呂青,2004;孫玉娜,2008)開展了農村家庭中女性地位和轉變情況研究,研究指出農村女性的家庭地位由非農化經濟收入的主體來確定,若農村女性本身直接參與非農化就業,那么其收入提高時則會相應提高其家庭地位,若其配偶優先取得具有優勢的非農化職業,則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會產生下降趨勢(孫玉娜,2008)。
因此,本文假設實現了非農化后的C村家庭,夫妻間關系的變化與夫妻獲得經濟報酬的能力正相關,而固化的兩性收入渠道,使得以父權家長制為基礎的夫妻關系并未發生實質性的轉變,而是朝著父權化的“經濟家長制”方向轉變。
2.2 概念界定
經濟家長制:與父權家長制相對應,指在家庭關系中,事權由家庭經濟來源的掌握者所有,并與其它家庭成員形成主從關系特征的家庭關系。
父權化的經濟家長制:指非農化家庭關系向經濟家長制方向轉變過程中,由于男性家長在經濟獲取中占絕對優勢,所以仍然有男性家長為主、其他成員為輔為特征的家庭關系。
2.3 研究方法
本文采取的研究方法是定性研究中的深度訪談法,通過被訪者對其生活史的口述,分析、了解其生活軌跡、行動依據和社會網絡。同時,被訪者主觀建構事實的行為也讓筆者得以從他們建構行為背后的真是意圖推斷事實真相并加以解釋。
3 具體分析
3.1 C村的非農化情況
C村緊鄰江蘇省,是M鎮26個行政村之一,全村共有人口1830人,人均耕地1.1畝。C村中絕大多數家庭已實現非農化,雖然各家還在耕種土地,但除留下口糧外,剩余全部出售。問:你自己的3畝多地現在種什么?答:麥子、玉米、豆子。問:收了糧食是自己吃的還是賣?答:基本都賣了(與Z大姐的對話)。
目前,工業、手工業及外出務工是C村家庭收入的主要來源,村民的非農收入呈現多樣化。問:你種糧食這一塊實際上已經不算你這個主要的收入了?。答:現在這個農村種地都不作為主要收入,都打工掙錢。問:村子不是有小工廠?答:東邊有大的企業(手工品廠),得用得十幾個人。包括在家六七歲、五六十歲的人,只要想干就有活干,一天最少能弄個一二十塊錢(與老C的對話)。
在工業化和農業現代化的帶動下,播種、收割等重要的季節性農活已無需全家趕工。種地靠機械,幾百畝地的時候大概兩天就收完了,收過以后這邊下著雨把地將上了,然后就打除草劑,十天時間就干完了(老C)。
由于農業收入已不作為家庭主要收入來源,對農活的組織和實施也無需絕對依靠男性或人多勢眾,C村傳統的小農生產方式已經發生了相當的改變。
3.2 非農化產業結構與就業
C村非農化后形成了以工業為主,農業和手工業為輔的產業格局。工業主要以四支規模化的打井隊為主,幾支規模較小的打井隊和板材加工、燒磚、伐樹等為輔。這幾類工作經常出門在外,且對工人的體能、技術要求較高,這使女性難以以此為業,除了體力等原因,照顧孩子的職責也很難使女性長期離家。問:那你老公現在也出去打工?答:經常出去打工,只要有活他就出去。問:出去不得一兩個禮拜?答:有時候幾天回來,有時候時間長。問:他這個打井到其他省還是就在附近?答:有時候上小縣,也有其他地兒。(與Z大姐的對話)
C村的婦女的收入來源有兩種,一是出售自家農產品所得(每畝每年大概幾百元),二是參加村辦加工廠,每天可以有20元左右的收入。答:他媳婦干個編織活,村里婦女有五六十歲的、四五十歲的在家沒事兒的都做,一天能掙個20多塊錢。也不耽誤家里干其他事,做飯啦、照顧地啦。(與老陳的對話)
可見,非農化后的C村沒有產生一個公平開放的就業環境,反而將兩性的就業渠道和收入水平固化了。男性收入相當于女性的10倍以上。那幾年收入少,現在一個男勞力他一天能搞到一二百、二三百塊錢(老C)雖然已不再依賴男性組織大規模農業生產,但男性的重要性在家庭中并沒有降低,只是將角色從家庭生產的主導者轉換家庭經濟收入的主導者。
3.3 經濟收入決定家庭地位
C村男性在農業生產中的作用逐漸降低,但家庭地位卻并未發生變化。劉燕舞在分析湖北省J縣J村的離婚現象時,曾提到當地婦女表示一定要嫁給可以賺錢的男人,即使婚后這男人對自己不是很好,她們還奚落那種重感情但不會賺錢的男人,說看著就會煩。2011年,陳峰提出“依附性支配”的概念來表達農村婦女家庭地位提高的被動性,但同時也表示這僅對于對于收入中下等的男性而言處于弱勢地位,而那些處于經濟分層塔尖的男性則依然在家庭中處于優勢地位。有關研究指出,農村外出打工家庭中夫妻經濟收入相當,使得家庭權力的分配也趨于平均,降低了發生家庭暴力的可能,甚至有些女方在經濟地位上占主導的家庭還發生了對男方施暴的情形。這說明經濟地位對農村婦女的家庭地位有顯著影響。
3.4 父權化的“經濟家長制”
由于C村男性的勞動報酬達到女性的10倍以上,這就形成了陳峰所說的在家庭中處于“經濟分層塔尖的男性”,其家庭地位也必然會處于絕對優勢。也就是說,在C村,男性家長的地位和權力沒有發生顯著變化。我們走訪的Z大姐家,就是一個典型案例。
Z大姐在家以看孩子和務農為主,老公經營打井隊,是家庭最主要的收入來源。Z大姐在大女兒出生后,又生了一個兒子,但由于Z大姐的大伯沒有兒子,公婆認為家族需要有“長子長孫”才能抬起頭來,況且Z大姐還年輕,還有機會生兒子,于是做主實施了過繼。但兩年后Z大姐再次生了個女兒,使Z大姐受到了來自婆家和村里輿論的困擾(當地社區情理是一定要生兒子,否則讓人看不起)。對Z大姐而言,過繼肯定不是自愿的,一是親生骨肉誰愿送與旁人,二是將來即使再生也是男女難料。所以,過繼的促成,Z大姐的丈夫肯定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這種過繼現象在城市中幾乎絕跡。由于絕大部分城市家庭中,丈夫與妻子在經濟地位上和家庭權力的行使上相對平等,如果夫妻中的一方強烈反對,行動自然難以實施。但在Z大姐家,由于其丈夫在經濟上處于絕對的主導地位,所以在家庭權力的行使上也“說一不二”,令沒有地位的妻子難以抗拒,這是過繼得以實現的主要前提;此外,該行為得到社區輿論的默認,也使Z大姐難以在家族中和村里找到支持者與過繼行為對抗。
4 結論與不足
4.1 結論與思考
“經濟家長制”是一個中性的概念,表示誰主導經濟誰就有地位。而在C村,恰巧是男性取得了經濟主導地位,這使得傳統的以父權家長制為基礎的夫妻關系在C村并沒有發生實質性的改變。
由于每個村落受所處地域、產業基礎、傳統思想等因素影響,使得家庭中的夫妻地位難以一概而論。但從經濟角度入手是一個相對容易的辦法。一是從各省(市、區)的經濟發展規劃中方便推演村落將會受到的影響;二是村落的產業結構相對簡單,容易推斷家庭中夫妻經濟地位和家庭地位的高低。
4.2 檢討與不足
本文的假設源自對C村田野調查的直觀感受,理論分析和邏輯推論較多,而且結論相對簡單,援引的論據只能說是對假設問題提供了一定的參考依據。更重要的是,夫妻間關系和家庭地位的構成,不能僅從經濟角度去觀察和分析,還有很多其他因素會決定一個家庭的夫妻關系和地位,本文只是一個簡單、粗淺的視角。筆者將在在今后的田野調查中對此問題進行更加深入的研究,貢獻自己微末的力量供其他研究者參考,并與積極參與相關探討。
參考文獻
[1]費孝通.鄉土中國[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2]費孝通.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
[3]陸學藝.當代中國社會結構[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
[4]楊善華.感知與洞察:實踐中的現象學社會學[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
[5]楊善華.田野調查中被訪人敘述的意義詮釋之前提[J].社會科學,2010(1),66-70.
[6]楊善華.30年鄉土中國的家庭變遷[J].決策&信息,2009(3).
[7]劉燕舞.從核心家庭本位邁向個體本位—關于農村夫妻關系與家庭結構變動的研究[J].中共青島市委黨校青島行政學院學報,2009(6).
[8]吳情操.都市村社:一個被圍困的社區[C].北京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