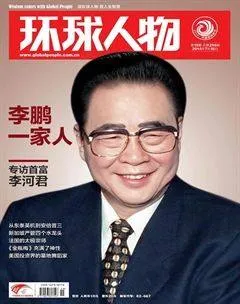李楯:人心壞了,是現在最大的問題

李楯,1947年出生,北京人,法學家和社會學家。先后就職于北京市律師協會和中國社會科學院;1988年任法制與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1989年受聘為北京市市場經濟研究所副所長;1993年受聘為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調查中心教授;1999年以后任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社會政策研究所執行所長,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社會學研究所所長等職。
如果你是從百度上開始認識李楯的,通常會看到他的名字后面跟著這樣一些標題:“既不要迷信官員也不要迷信學者”“艾滋病問題是中國社會問題的溫度計”“現在的清華已經不如1952年前的清華了”……
記者真正認識李楯,是從他的名字開始的。“經常有人寫錯我的名字,這個‘楯’不是‘循’—循規蹈矩,也不是‘遁’—逃跑;乃是堅守、擋住的意思。”接著,他引用了1959年出版的《革命烈士詩抄》中的兩句詩:一手持著信仰的盾牌,一手揮砍著意志的寶劍—這也是他回顧60多年人生歲月,對自己做出的一點點評吧。
對李楯的采訪是在酷暑日子里的一個上午進行的,他即興而言,洋洋灑灑,低沉與激昂、滔滔不絕與沉默不語、略帶感傷的回憶與一針見血的批判在采訪的3個多小時里來回切換著。幾天后,他給環球人物雜志記者發了一封郵件,是他對自己當日談話的總結,列了8條。
老師是中國一流的學者
介紹一個人,少不了出身、求學、經歷這三部分。但想用這三者來描述李楯,卻著實有些難。
李楯出生于一個大家族,父親李瑞年是留學法國、比利時的畫家,母親很早就參加了學運。對這個大家族,李楯不愿太多提及,“小時候的舊宅院在琉璃廠西,掛著五世同堂的匾。里面有線裝書、外文書,有古琴、冰鞋、小提琴、網球拍……我只有一個妹妹,她出生在協和醫院。協和的病案保存得非常好,前幾年,還給她們那年出生的人做了一次體檢……”說著說著,李楯陷入了沉默,良久,只有嗡嗡的空調聲。
李楯是大學教授,極看重大學中各學科嚴格而規范的訓練,他自己卻沒讀過大學,但他的老師不少是中國的一流學者:法學錢端升先生、社會學陳達先生、古漢語陸宗達先生、現代漢語黎錦熙先生等。文革時,甚至更早,這些老師無法正常工作,他才有機會一對一地求教于門下。講到求學經歷時,他自我調侃說:“人家學的是吃飯的買賣,我當時是興趣,沒想到后來靠它吃飯了。”
同樣,李楯到底是干什么的,這個問題也難以回答。他插過8年隊,在街道小廠“以工代干”4年;他是改革開放后第一批律師,參與過司法改革工作,也曾著力研究和推進聽證制度;他做過婦女研究,在湖南和珠三角做過農民工調查,也曾是世界著名社會學家林南的座上賓;他是聯合國一些機構以及政府部委的專家,現在擔任自然之友基金會理事長。他不是一個書齋里的學者,他曾斡旋調停,促成政府、血制品企業聯合解決百余名血友病人因使用血制品而感染艾滋病事件的善后問題。所以,李楯應該被稱為“研究者以及行動者”。
剛烈的唯美主義者
第一次見李楯,是在一次公益組織的會議上。會議有一個環節,8人分作兩組,就一問題展開辯論,別人說得很隨意,唯有他拿著紙筆不時記錄。一直到總結陳詞階段,他才開口,出口成章,頗有氣勢,主持人的聲音完全被淹沒了:“李老師,時間到了。”
但在面對記者采訪時,他卻是溫文爾雅,超然物外,低沉甚至斷續的話語里,夾雜著一絲感傷。
“在做人與做事上,做人是第一位的。但我這人又太想做事了,知其不可而為之。”這種剛烈的態度讓他在面對一些問題時,也會很尖銳。
他公開批評環保部的某位領導,為使項目得以上馬,在環評兩次被否定后,竟決定重做環評。外國基金會出巨資支持的某些項目,被他稱為“連錦上添花都不算,是在玩游戲”。對自己非常喜歡的律師職業,他恨鐵不成鋼,“由于政治的壓力、金錢的誘惑,這是個沒有長成就開始腐爛的職業。”就連他最愛的昆曲申遺成功,他也不免潑冷水:“它的生命力在于:它是中國人認知、思維、記憶和表達的方式,這已經完全毀掉了,現在是去魂借形。”
李楯說自己是個唯美主義者,對很多事很悲觀。但對生活,他很積極。李楯的家里,最多的是書,其次是酒,“曾經很喜歡喝酒,現在很少喝了。”60歲以后,李楯一直在給自己做總結。概括起來大概是三句話:“從少年時的重獻身、重殺戮,到今天的敬畏生命、敬畏自然。”“認可別人和自己不一樣,寬容對待但不認同。”“童心未泯,良知未泯。”
民生第一并不等于公平
環球人物雜志:在您看來,現在我們這個社會最急需解決的是什么問題?
李楯:中國是大國,經濟增長了,如果受益者不是全體國民,而是少數利益人群,那就會造成上層腐敗、底層墮落。想解決好這個事,要做到民生第一。首先,建立覆蓋全體國民的、城鄉一體的、中央財政承擔的、每個人均等享有的、隨處享有的社會保障制度。其次,在分配時,勞動所占的比例多一些,資本相對少一些;居民收入所占比例多一些,財政相對少一些。第三,讓個人可以通過自主選擇生活得更滿意一些。
環球人物雜志:很多人一提到民生,就會想到這要投入多少錢,您覺得,經濟原因是最首要的嗎?
李楯:這不是有沒有錢的問題,任何一個政府的財政盤子都有定數,要看民生在政府問題單子上的排序前后。
環球人物雜志:其實民生和公平有非常密切的關系,您怎么看待公平?
李楯:有了托底的社會保障,自主選擇的權利,這個社會就會好起來,但不能完全解決公平問題。公平或公正,是個價值目標,具體目標可以判斷是已經達到,還是尚未達到;價值目標,只能判斷是日漸接近或者遠離。我們認可一個社會會存在事實上的不公平,但做制度設置時必須基于公平、正義。使不公平可以堂而皇之地進入制度的,不是一個良好的社會。
環球人物雜志:您曾說,和諧是繼民生第一之后的另一大問題。您怎么理解和諧?
李楯:不同的人,不同的人群,利益、主張不同,但只能和平共存,所以才需要和諧—要有原則的妥協。和諧有兩個層面:一是人與人,國內和諧社會,國際和諧世界,但現在總有一些人天天喊打仗。二是人與自然和諧。一提到環保,我們經常說,要改變產業結構增長模式、消費方式,治理污染,修復生態。這非常好,但為什么做不到?這不是簡單的唯GDP論可以解釋的,而是因為體制本身帶來了不安全感。
環球人物雜志:現在,我們經常能聽到這樣一些觀點,比如“叢林法則”,“沒有永遠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等等。您怎么看?
李楯:這幾十年,中國社會有種趨勢:不講價值取向,只講利益,這是極可怕的。人心壞了,這是我們現在最大的問題。我們應該承認,沒有永恒的利益,但要有永遠的規則。
環球人物雜志:什么樣的規則?
李楯:以人為本;法治、善治。在一個法治國家,善良公民的座右銘是:對現行法律,嚴格遵守,積極批評。遵守,才有秩序;批評,才能改進。善治比法治更進一步,需要有政府、企業、非政府、非營利組織、社區,以至是國際社會的合作,比如像環境—生態保護,應對氣候變化這樣一些問題,沒有合作,是不行的。
環球人物雜志:那么,對于老百姓來講,過得好不好的標準是什么?
李楯:能按自己的愿望好好活著。政治家、企業家及其他一切成功人士最大的功業,就應該是能讓更多的人豐衣足食,安居樂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