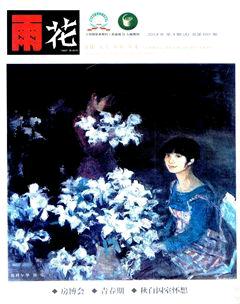蘇州好,水調舊家鄉
●陳 武
蘇州好,水調舊家鄉
●陳 武
故鄉的情懷,在每個人的心中都有很深的暗藏,我不知道,俞平伯頻繁地來往于蘇杭,也是在尋找他的故鄉嗎?
俞平伯對于家鄉蘇州,有著特殊的情懷,這里有他童年、少年成長的故園舊宅,還有他讀過書的中學——雖然只有幾個月,但在他求學生涯中,不能不說是重要的一站。
1920年12月11日,俞平伯從杭州出發,和舅父、夫人一起,開始六天的蘇州、無錫、上海三地游。歷史上,文人們喜歡把蘇杭相提并論,主要是因為相似的江南風光和人文環境。對于俞平伯來說,還有另一層意義,兩地都是故鄉。蘇州自不必說。杭州呢?曾祖父在此擔任多年教習,有故宅俞樓,而曾祖父母的安葬地也在西湖邊上。早在1918年,俞平伯在北京大學求學時,就有四首《憶江南》,把蘇杭一并包羅了:
江南好,長憶在西湖。云際遙青多擁髻,堤頭膩綠每皴螺。葉艇蘸晴波。
江南好,長憶在山塘。遲日烘晴花市鬧,鄰灘打水女砧忙,鈴塔動微陽。
江南好,長憶在吳門。門戶窺人鶯燕懶,日斜深巷賣餳聲,吹徹杏花明。
江南好,長憶在吾鄉。魚浪烏篷春撥網,蟹田紅稻夜鳴榔,人語鬧宵航。
到蘇州的第二天下午,俞平伯一行就到全浙會館,聽了一出昆劇。蘇州和杭州都是昆曲中心,會館、戲園、茶社常有演出,那咿呀聲中,道出多少江南水鄉的清音味兒。這次聽曲,給俞平伯留下了深刻的記憶,直到五十年后,他還寫詞懷念:“蘇州好,水調舊家鄉。只愛清歌諧笛韻,未諳紅粉遞登場,爨弄興偏長。”這首詞,如果把第一句改成“江南好”,可以和上述的四首合為一輯了。雖寫作時間相隔五十多年,情感和詩意上,卻是相互牽連的,甚至相互遞進的。
蘇州好,我是知道的。我多次去過蘇州,開始也只想著寒山寺、拙政園、山塘街什么的。后來便沿老街隨意走走,發現情趣大為不同。如鳳凰街附近有條不起眼的小河邊,是一條麻石鋪的路,隨河蜿蜒。我走在路上,看著腳下的石板,石板上的紋和字,看著流動的河水,看著河邊的白墻和灰黑的小瓦,感覺有一種安靜、恬淡和優雅的氣息,那些老式的窗欞、雕花的門樓,又有一些古老和隱秘。當門窗里透出一縷琴音或清唱時,我的心會跟著琴弦、清音怦然一動,感覺蘇州的味兒有了,情也有了。
俞平伯這次在全浙會館聽曲,莫非是計劃中的一部分?而我相信,第二天重游平江中學舊址,肯定是有所計劃的。俞平伯在投考北大之前,曾在這所新式學校里,突擊上了半年課,時間是1915年春到這年的高考。在這之前,俞平伯的讀書生活,全部是家教或家塾,對于飽學一肚子舊學問的俞平伯來說,平江半年,是他人生的一大轉折。新式的教育,不僅讓他開了眼界,順利考入北大,這半年的平江學習生活,對他也特別關鍵。所以北大畢業后,經歷短暫的留學,回杭州小住半年,游山陰道,八月又去南京游覽莫愁湖和秦淮河,去上海訪陳獨秀,和周作人通信,游杭州皋亭山,還寫了好幾篇關于詩歌的論文,這些成就不可謂不大。但蘇州,畢竟是他出生地,有他的曲園祖宅,有小時候無數次進出的馬醫科巷,內心里還是要回來看看的——并不是要裝點衣錦還鄉的榮耀,而是人人都有的少年情結。那么,平江中學,也就不能不去了。
12月18日,俞平伯專門繞道,去干將坊巷讓王廟舊址,這就是母校平江中學了。只是此時此地,這里已經頹廢得不像樣子了。站立舊址前的俞平伯,憶及幾年前的聚讀時光,感懷是如何的深,心情是如何的不平靜,想必外人無以知曉吧。但,這樣深切的感受,至少一直縈繞于這次旅行,否則,何以一回到杭州,就寫下新詩《如醉夢的躑躅》呢。而詩前一段小序,讀來更讓人唏噓:
一九一五年之春,予在蘇州平江中學校讀書半年,后即北去。校旋亦閉歇,舊時朋侶星散。予亦東西奔走無所成就。一九二○年十二月自杭而蘇,特迂道過干將坊巷讓王廟校址,屋宇荒寂殆將傾圮。惟兒時聚讀光景,忽忽五六年矣,久已淡如煙霧;一旦舊地重來頓堪仿佛。尋跡堂廡間,低回不能遽去;奈守廟童子不解人意,屢相催追以目,遂悵然而去。歸途夕陽在樹,曲陌新晴,賣糖聲,挑擔聲,驢步得得,驢鈴郎當聲,耳目所接皆如舊相識。躑躅街頭,如醉如夢。舊感叢繞,明知其無當;惟不堪排宕,返杭后姑以詩寫之;詩既成,姑序。序之工拙與成詩與否,均不及計矣。
一九二○,十二,二十七,在杭州記。
干將坊巷,是舊時蘇州一條普通的小巷。據《姑蘇志》稱:“因干將墓對峙而名。”又據《吳郡志》載:“吳王使干將鑄劍于此,故曰將門。今謂之匠,音之訛。”據上海、蘇州等地的民間傳說,吳越時,干將是鑄劍名手,與歐冶子齊名。干將鑄劍,“采五山之鐵精,六合之金英,候天伺地,陰陽同光,而金鐵之精還不見銷融”。其妻子莫邪說,“神物之化,須人而成”,鑄劍不成,是否也要得人而后才成。于是莫邪投身爐中,結果鑄成雌雄兩把名劍,陽曰干將,陰曰莫邪。這個傳說,蘇州人記憶最為深刻,某園的試劍石,傳說所用寶劍就是干將的劍。干將坊巷在蘇州存在很久,和如今的干將路不是一回事。據蘇州朋友相告,昔日從人民路到言橋這一截,就是干將坊巷。那時候高高的石牌坊立在巷口。據說,直到1982年才被毀掉。蘇州好東西太多了,毀掉一兩個古牌坊也許并不心疼,毀掉一條小巷也無所謂,毀掉一代人的記憶和情結,卻是任何東西也無法彌補的。
《如醉夢的躑躅》這首詩,收在俞平伯的詩集《冬夜》里。這首詩所傳遞的信息,小序里已經說得非常明白了。但等把全詩讀完,還是心隨俞平伯如醉夢般地躑躅了:
匾是豎著;/廟門是開著;/要枯而不愿意枯的樹,/還是三株四株這樣立著;/塵封了的大殿照舊骯臟著;/什么都是一樣!/早跑了五六年底時光,/什么都是一樣嗎?
俞平伯的無奈一問,沒有得到回答。也不需要回答,答案在他眼里清清楚楚了。最后,詩人只能說:“歷來人事所暗示的,只是添些無聊賴的感慨。暫時撇去,也暫時溫暖起‘兒時’的滋味,依稀酒樣的釅,睡樣的甜。”看來,童年記憶的力量,真能消除人生很多無奈的。
事實果真是這樣嗎?到了來年的1月12日,俞平伯還時時記得半個多月前的游覽所見所聞,又寫了一首《哭聲》:“一別六年的地方,六年后來了的我,頓從可厭中變現可怕的光景來,從可怕里又翻涌出一種搖動的悲哀。這叫我永不忘記!”
時間很快就到了1921年9月14日,心里一直惦念著家鄉的俞平伯,和夫人一起,再次從杭州來到蘇州。俞平伯這回沒有去訪舊,而是和夫人乘船去了寒山寺。不知為什么,對于這次寒山寺的游覽,俞平伯心情也并不愉快,回杭后,于三十日創作一首《凄然》:
哪里有寒山!/哪里有拾得!/哪里去追尋詩人們底魂魄!/只憑著七七八八,廓廓落落/將倒未倒的破屋,/粘住失意的游蹤,/三兩番的低回躑躅。
明艷的鳳仙花,/喜歡開到荒涼的野寺;/那帶路的姑娘,/又想染紅她底指甲,/向花叢去掐了一握。/他倆只隨隨便便的,/似乎就此可以過去了;/但這如何能,在不可聊賴的情懷?
有剝落披離的粉墻。/欹斜宛轉的游廊,/蹭蹬的陂陀路,/有風塵色的游人一雙。/蕭蕭條條的樹梢頭,/迎那西風碎響。/他們可也有悲搖落的心腸?
鏜然起了,/嗡然遠了,/漸殷然散了;/楓橋鎮上底人,/寒山寺里底僧,/九月秋風下癡著的我們,/都跟了沉凝的聲音依依蕩顫。/是寒山寺底鐘么?/是舊時寒山寺底鐘聲么?
每每讀這首詩,就會想起我的寒山寺之游。我到了寒山寺時,心情也不爽,說不出的理由,也許張繼的那首詩太有名了吧,去時,詩中的情調,不由得會涌上心頭。那么俞平伯的游覽,給他的感覺,正如標題所說,也是凄然的了。詩前依舊有一小序,照錄如次,來作證我的推測:“今年九月十四日我同長環到蘇州,買舟去游寒山寺,雖時值秋半,而因江南陰雨兼旬,故秋意已頗深矣。且是日雨意未消,游者闃然;瞻眺之余,頓感寥廓!人在廢殿頹垣間,得聞清鐘,尤動凄愴懷戀之思,低回不能自已。夫寒山一荒寺耳,而搖蕩性靈至于如此,豈非情緣境生,而境隨情感耶?此詩之成,殆吾之結習使然。”已經說得極為明白了。特別是那連用的三個驚嘆號,還有四個問號的安排,把俞平伯當時的心境和寒山寺秋意融合得十分體貼。這次寒山寺之游,他是否專程一見曾祖父重寫的詩碑呢?“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詩在,碑在,人已不在。張繼的詩不朽,書碑的曾祖父也不朽,但是來客的心情卻是悲戚的。不問是否和俞平伯有著同樣的情懷,就是和詩碑毫無瓜葛的我,一到寒山寺,心情也同樣地落進了《楓橋夜泊》所營造的氛圍里。
接下來的1921年11月9日和10日,年輕的俞平伯輕車簡從,又來到隸屬于蘇州的常熟游覽兩天,在美麗的虞山下、尚湖邊,留下他親密常熟山水的印痕和足跡,也留下他對常熟山水的情思和感念。但是,這一次初冬的瀏覽,似乎有些特別,和前幾次的心情大為不一樣,蕩舟尚湖,并非愜意和放松,而是帶著某種心情吧,否則,怎么會在常熟旅館中,想起在杭州看到的那首情歌呢?
歌謠只有四句:“高山有好水,平地有好花;家家有好女,無錢沒想她。”這是一首純樸、明凈、簡潔的歌謠,俞平伯反復咀嚼,夜不能寐,就在旅館里,把歌謠擴寫成一首白話詩。俞平伯在創作自認為重要的作品時,都會寫篇小序。這次也不例外,在序中,他自謙地說:新譯的“詞句雖多至數倍,而溫厚蘊藉之處恐不及原作十分之一。”看來他還是被原作深深地感動著。
第二天,俞平伯作了尚湖之游。俞平伯對尚湖并不陌生,他知道黃公望、沈周、唐寅、康有為等歷代文人均有題詠,也知道虞山西麓拂水巖下的拂水山莊,這是錢牧齋早年的讀書處,也是柳如是生活幾十年的地方。俞平伯一邊蕩舟,一邊欣賞浩渺的湖水和背后的青山,引發了詩興,但他并沒有被湖光山色所蒙蔽(或者他心底里尋找的,并不是湖光山色),而是在船上信筆寫了一首極具現代意義的愛情詩《不解與錯誤》。
紅月季,開著花,空山里,/會覺得孤寂吧,/大約是的!
我來呢,輕輕地握著,/她已先低頭了。
我想慰她底孤寂,/她偏獨自去零落,這將使我不可解了。
詩人借開在空山里的紅月季之名,感嘆“她”的孤寂。即便是“我”來了,輕輕地握著“她”,想慰“她”的孤寂,也沒能挽回“她”的零落。真讓人傷感。這是作者抒發愛情的無常嗎?記得我年輕時讀這首詩時,被深深地感動著,也深深地惋惜著,懷疑俞平伯美滿的婚姻中,會不會也有遺憾。
尚湖我去過三次,都未及劃船。想起九十多年前的湖面上,一葉小舟輕巧漂移,詩文兩絕的俞平伯,只二十出頭歲,多么的意氣風發,他看滿眼湖光山色,難道僅僅是為抒發一點個人的私情?那紅月季是暗指誰呢?
結束尚湖之游,俞平伯于11日又趕往蘇州。在蘇州做何游覽,見了誰,都無從查考了,但他創作的新詩名篇《愿您》,卻是很多人知道的,一來,是這首詩被朱自清選入了《中國新文學大系·詩集》,二來,這首愛情詩里的“您”指向誰,和《不解與錯誤》里的紅月季是否是一個人呢?我們只能猜測了:
愿你不再愛我,/愿你學著自愛罷,/自愛方是愛我了,/自愛更勝于愛我了!/我愿意去躲著你,/碎了我底心,/但卻不愿意你心為我碎啊!/好不寬恕的我,/你能寬恕我嗎?/我可以請求你底寬恕嗎?/你心里如有我,/你心里如有我心里的你;/不應把我怎樣待你的心待我,/應把我愿意你怎樣待我的心待我。
蘇州對于俞平伯來說,是水調舊家鄉,難道也有遺落的愛情?俞氏的老師周作人寫過一篇《初戀》,對那個曾經暗戀過的楊家三姑娘,有過細微的心理刻畫。俞平伯也有過這樣的初戀嗎?這首詩,通過主人公告白的形式,表現自己對戀人的心意,完全袒露了自己的心聲。這樣的愛情,是雙方都把握不了的,不知什么原因,“我”不得不與女友分手。但,兩人的情感,依然藕斷絲連,雖嘴上說,愿你不再愛我,其實是多么希望對方還在愛他啊。而且,這樣的感情一詠三嘆,不斷重復,就是“我”希望“你”愛“我”,而不是不愛“我”。聯想到前一天,他在尚湖舟中寫的《不解與錯誤》,俞平伯對失去的曾經的愛,多么的刻骨銘心。請看詩中這樣的兩節:
她或恨我底自私,/我也怨她底負心。/她已誤,我已錯。/
錯是錯了,/不解只是不解了!
把俞平伯這兩首詩對照著讀,如此的直白、坦率的愛情表白,對俞平伯來說是很少見的。這樣,我們就聯想到,為什么俞平伯匆匆一到常熟,在旅館中想到在杭州看到的童謠了,“家家有好女”只不過是引子,是他念起自己心中的“好女”,所以才從杭州趕往常熟,才有心情把這四句童謠改寫成長長的一首白話詩。
同時在尚湖舟中,他還填寫了那首著名的《霜花腴·尚湖泛舟》:
稻塍徑窄,耐淺寒,低顰屢整羅裳。風懶波沉,櫓稀人淡,深秋共倚斜陽。暮山靜妝,對鏡奩、還暈丹黃。溯來時、翠柏陰多,故家喬木感凄涼。誰醒泛秋輕夢,近荒城一角,夜色茫茫。邀醉清燈,留英殘菊,連宵倦客幽窗。舊游可傷,縱再來、休管滄桑;更西湖、倩影蘭橈,哪堪思故鄉。
從這首詞中,也可知道,俞平伯不是第一次來尚湖了。這次泛舟,給他留下的記憶,更多的是傷感的主調,發出“舊游可傷”、“哪堪思故鄉”的感慨。“低顰屢整羅裳”的人啊,還能“深秋共倚斜陽”嗎?
從1920年12月16日到1921年11月9日,不到一年的時間里,俞平伯三次去蘇州,每次都有新詩創作,粗略統計,共有新詩六首,還有古詩詞若干。這些新詩,都收在他重要的一本詩集《冬夜》里。特別是1921年11月9日的常熟、蘇州之游,他已經于10月辭去浙江一師的教職,準備赴美考察,卻抽時間回蘇常。他對蘇州的情懷,在許多詩章中都有流露,最讓人感懷的,是他在《小詩兩首》的《客》里所說:“我北歸,我又要南歸,歸來底中間,把故鄉掉了!”
故鄉的情懷,在每個人的心中都有很深的暗藏,我不知道,俞平伯頻繁地來往于蘇杭,也是在尋找他的故鄉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