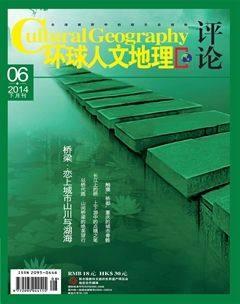未成年人社會調查報告制度探究
作者簡介:范洋洋,(1991.8——) 山東省菏澤市人,專業訴訟法學,2013級遼寧大學碩士研究生
摘 要:新修改的《刑事訴訟法》首次規定了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社會調查報告制度,從而更有利于對未成年人的保護。但是,法條的規定不夠細化,沒有從根本上明確調查報告的性質,也沒有保障該項制度有效運作的措施,從而使得社會調查報告制度形同虛設,在司法實踐中得不到適用。因此必須對該制度的有關方面予以明確,才能保證其作用的發揮,保障未成年人的利益。
關鍵詞:調查報告;保障人權;量刑證據
2012年新《刑事訴訟法》第268條規定了未成年人社會調查報告制度: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根據情況可以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長經歷、犯罪原因、監護教育等情況進行調查。這一制度設計的初衷在于保護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利益,體現我國刑事訴訟制度的人性化,從而實現保障人權的目標。但是,法條的規定過于原則化,并沒有明確規范社會調查報告的性質和功能,也沒有配套的程序設計來保證實施,這就使得社會調查報告在司法實踐中得不到有效運用,無法發揮其預期的效果。
一、社會調查報告的性質定位
對于社會調查報告的性質問題,理論界一直存在很大的爭議,一部分學者認為社會調查報告不是證據,它不符合法定證據種類的任何一種類型,不能作為證據使用。2012年最高院出臺的司法解釋也沒有肯定社會調查報告的證據性質,認為它只是一種法庭教育和量刑上的參考。但是,我們對此持相反的觀點,我們認為,未成年人社會調查報告是證據,能夠在法庭上接受質證、調查,從而更好地發揮其自身的作用,使之在司法實踐中的適用規范化。
首先,法律規定的證據種類是不斷完善和發展的,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取證方式的完善,一系列新型的證據種類諸如電子數據等都會進入法定證據的視野。學術界很早之前就有學者對用法律條文限制證據范圍提出相反的意見,認為這樣的規定會限制證據的彈性和靈活性,使得大量承載案件事實的證據得不到運用,因此,法定證據種類有其固有的局限性,我們不應當固守這一規定;其次,既然法律肯定了社會調查報告可以作為量刑的參考,也就說明了調查報告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作為量刑的依據使用從而影響量刑,刑事訴訟中的證據不僅包括定罪證據,還包括量刑證據,因此,社會調查報告所起到的影響未成年被告人刑罰輕重的作用,可以使之歸屬于量刑證據的范疇。
二、進行社會調查的主體范圍
根據《刑事訴訟法》第268條的規定,對未成年人進行社會調查的主體是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和人民法院。這一規定有其合理之處,公檢法三機關有著自身的權威性,他們有能力完成一般公民力所不能及的調查任務,同時由他們進行社會調查也更為便捷,節省訴訟時間。但是,僅僅規定公、檢、法三個主體是不是過于狹窄了呢?公安機關、檢察機關在一個刑事案件中所承擔的是控訴職能,他們能不能公正客觀地進行社會調查呢?對于那些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有利的報告,他們會不會公平地向法庭提交呢?
我們認為,對于進行社會調查的主體,應該加上辯護律師,這樣一方面能夠保證對未成年人社會調查的全面性,保證社會調查報告的客觀程度,另一方面也能夠切實保護未成年人的訴訟利益,尊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權利。辯護律師出于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保護的需要,一般會積極地進行社會調查,收集有利于其當事人的各種材料,避免未成年人處于極度不利的地位。因此,社會調查主體增加辯護律師,能夠增強社會調查報告制度的可行性,促進保障人權原則落到實處。
三、社會調查報告制度的具體運行
明確了社會調查報告的性質,以及進行社會調查的主體,我們就應當關注該項制度的具體運作。《刑事訴訟法》對未成年人社會調查報告制度的規定過于原則化,在實踐中往往得不到貫徹執行,從而使制度的存在形同虛設,不利于保障未成年人的各項權益。
1、進行社會調查的強制性規定
既然社會調查報告能夠作為量刑的參考依據,成為量刑證據,那么社會調查報告制度就是非常重要的制度,進行社會調查就會關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切身利益。因此,《刑事訴訟法》第268條規定的“……根據情況可以對未成年……進行社會調查”就存在一定程度的欠缺。“可以”進行社會調查,說明對未成年人進行社會調查不是強制性的,在司法實踐中,國家機關出于辦案效率的考慮,通常會省略這一步驟。那么,同樣是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一部分案件通過社會調查收集到了對未成年人有利的信息,因此減輕或免除了刑罰;而另一部分案件則根本沒有進行社會調查,這是十分不公平的,也忽視了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保護和關懷。
因此,法律應當對社會調查做出強制性規定,對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公安機關、檢察機關應當進行社會調查,對于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信息,積極向法庭提供,使未成年人能夠在最大限度上承擔最寬緩的刑罰,貫徹刑事政策寬嚴相濟的原則,發揮刑事程序的教育作用,避免再犯的危險,體現法律的人文關懷。
2、社會調查報告的舉證、質證程序
刑事訴訟法規定,所有的證據必須經過查證屬實,才能夠作為定案的根據。因此,作為量刑證據的社會調查報告,也必須經過舉證質證、查證屬實,才能對未成年被告人的刑罰輕重產生影響。
對于公訴方進行社會調查形成的調查報告,舉證質證程序完全可以按照普通證據的方式進行。關鍵是對于人民法院形成的社會調查報告,應當完成舉證和質證的程序呢?我們知道,法官的消極和中立是現代刑事訴訟的重要標志,法官是事實的裁判者,不承擔主動收集證據調查案件的責任。但是,由于我國的律師制度尚不發達,辯護一方收集證據的能力有限,而得不到有效的證據又不利于保護被告人的權利。因此,允許法官在一定范圍內收集對被告人有利的證據,從而避免法官成為第二公訴人。
對于人民法院進行社會調查形成的調查報告,由于是對未成年被告人有利的證據,因此應當交由辯護方出示,然后由公訴方質證,查證屬實后可以作為量刑的依據,影響未成年被告人刑罰的輕重。
參考文獻
[1]李國莉.未成年人社會調查報告的證據法解析及量刑運用[J].學術交流.2013(10).
[2]馬康.未成年人社會調查制度若干問題研究[J].北京青年政治學院學報.20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