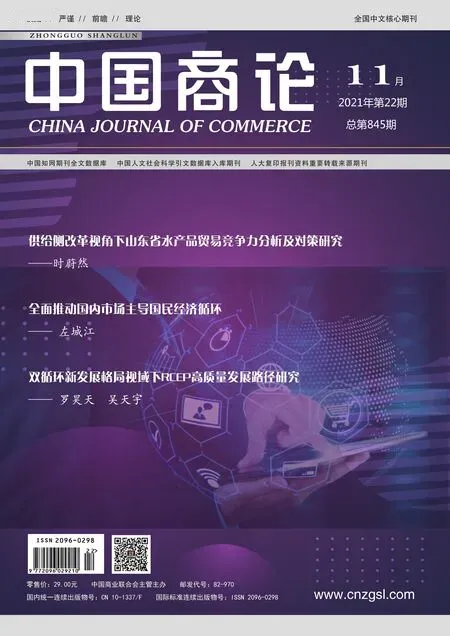武常岐 站在汽車之外看汽車
本刊記者 馬曉蕾 王彥 攝影 胡荻

《中國商貿》:您在“2014中國汽車論壇”中提到“自主品牌汽車市場占有率在過去一段時間里在持續穩定地下降。”請問:這個市場占有率是指全球市場還是特指中國國內市場?您能否可以就這個“持續和穩定地下降”具體地談一談?
武常岐:這個市場占有率是指自主品牌汽車在國內市場的份額。中國本土汽車企業剛剛開始在海外市場上做一些開拓,有一些出口,還談不到有很大的市場份額。
至于導致自主品牌汽車市場占有率“持續穩定下降”的因素有很多,首先是合資品牌汽車在中國市場上積累了大量的利潤,可以加大對中國市場投資的力度,增加產能、加速推出新車型。另一方面是雙方的博弈過程。由于現在主流汽車技術相對比較成熟,大型跨國公司在工藝技術上有很長時間的積累,大家不在同一起跑線上。中國的自主品牌汽車在努力嘗試。比如說紅旗汽車,開始性能和價格不盡如人意,但市場競爭很殘酷。現在各種選擇很多,客戶體驗很重要。第一次市場測試不行,讓大家再買,就很難,因為不是沒有其他替代品。
同時,在過去的一段時間里外資品牌主要占據中高端市場,中國自主品牌由于有價格的吸引力,占據低端領域。但由于一些政策影響而打破了這種平衡。現在由于限購政策,車牌變成稀缺資源,受影響最大的就是中低端的車。購車者在北京好不容易搖兩年搖到一個號,讓我買個奇瑞QQ?不可能!拿到這個號后一定要買一個好點的車。
《中國商貿》:您認為能夠使中國自主品牌汽車提高市場占有率的途徑有哪些?
武常岐:提高自主品牌的市場占有率不可能一蹴而就,有很多事情要做并且可以做。
首先車的品質一定要好,這是基礎。汽車接口的封閉性、車窗、雨刷,這些小的地方,細微的地方,往往是客戶體驗差別的地方。發動機等主要部件也更關鍵,但這些方面不應該有問題。如果這個也有問題,那汽車企業根本沒有辦法在市場上生存。有些東西看上去很小,但是非常重要。這也就是細節決定成敗的道理。
其次就是要重視開拓廣大的中國農村市場。這里我們所說的農村市場,主要是指縣或者鎮。中國自主品牌在這個市場上應該還有機會。
北京汽車集團的李峰總經理認為提升自主品牌競爭力的辦法是一步一個臺階,循序漸進。這也是一種追趕模式。但在國際競爭中,我們還可以考慮是否可以改變游戲規則而取勝,而不是按照既定的游戲規則和現有的大跨國公司玩這個游戲。比如田忌賽馬就是改變競爭方式取勝。不管高端、中端、低端他都比你強,如何可以取勝。如何改變游戲規則,這就是所謂的商業模式。
以現在汽車的精細化程度,你想轉成其他模型挺難的。新技術的出現提供了這樣一種可能性。過去一段時間汽車產業比起其他產業來講有一個非常關鍵的節點,就是新能源車的概念。電動車的出現和技術的改進可以稱之為“顛覆性創新”。
因為現有的大企業對現有的技術投資很多。比如內燃機等很多技術已經非常成熟。一旦轉入電動車就沒用了。這是利益相關方最不愿接受的事。所以,現在汽車大國希望特斯拉永遠不成功。但是這個不取決于某些人的意愿,要看這個技術和商業模式怎么發展了,
由于電動車的技術還不成熟,大家大致都在同一起跑線上,不是人家搞了一百年,你還剛剛起步。我是汽車行業以外的人去看汽車行業。要了解汽車行業就要走出汽車行業看其他行業是怎么發展的。
《中國商貿》:您在演講中提到有關建立統一大市場過程中地方政府對GDP的需要,我們是否可以理解為中國自主品牌汽車在國內市場上仍然處于地方保護主義制約下的割據狀態?在這個方面是否可以請您具體談一談您所掌握的情況?
武常岐:因為汽車是個大產業,它對工業發展、就業帶動都有積極影響,所以,各個地方都希望發展自己的汽車產業。現在,基本上全國每個省都有汽車整車生產企業。全國的整車企業有一百多家。不僅比一些發達國家的汽車公司的數目多出很多,而且在地域上相對分散,美國的汽車企業曾經集中在底特律,而現在也只分布在田納西州等幾個地方。日本也是同樣。
比如比亞迪的電動車瞄準大眾市場,能夠在國內推廣的話,應該說比特斯拉更有前景。但比亞迪的電動車就開出深圳就很困難。深圳市委書記開著比亞迪的E6,說多好多好,但是,其他地方都不積極。
其中一個問題是現在電動車價格還是比較高,在目前階段需要政府給予一定補貼。一部分補貼由中央財政出,另外一部分由地方財政補,有些地方政府就不希望補給外地生產的新能源車。
因為很長一段時間內,地方政府考核、領導干部晉升以GDP增長為標準。地方政府需要投資,需要經濟活動,需要解決就業,比如,在深圳生產的車,運到武漢,在武漢銷售,由武漢政府提供補貼,和武漢本地生產的車來競爭,武漢政府當然很不愿意。
針對這個問題,企業在想辦法,辦法之一就是在不同地方建立合資整車廠。這樣當地有了GDP,企業也有銷售收入。但從經濟效益來講,可能就要犧牲規模經濟帶來的好處。
中央也在想些辦法:原來中央補貼轉給地方,由地方政府去補貼;現在的一個改善就是直接補貼客戶,誰買車補給誰。
更重要的是怎樣去評估地方政府和干部的業績,中央政府應該怎樣去評估地方政府。如果哪一天考核標準改了,各地都以治理環境污染和可持續發展為主要績效考核指標的話,地方政府就得想辦法,可能就歡迎電動車了。
《中國商貿》:合資品牌的汽車是否也受到地方保護主義的影響?
武常岐:合資企業需要合資雙方的能力互補。在合資企業中中方提供市場、政府關系、產業政策,外方提供技術和設計,雙方形成利益共同體。在這樣的制度安排下,中國的汽車工業有了很快的發展,培養出一些產業工程師、產業工人和生產能力。
但是未來發展自主品牌汽車,這樣的安排將帶來很多問題。它在兩方面阻礙了中國自主品牌汽車的發展。
一方面,一汽、二汽、上汽的合資企業是其主要的利潤和收入來源,它們不愿意殺掉這個“下金蛋”的。
你要上海汽車總公司自己搞一幫人把自己的合資打下去?難!因為那樣做是自己傷害自己的利益。合資品牌有點像中國自主品牌汽車發展的毒藥丸一樣,是你沒有自己和自己競爭的勇氣。
另外一方面,汽車產業是全球性的產業。企業要想提升競爭能力的話,規模一定要大,做的不應該是一個局域市場,一定要走出去。但是,合資企業的外方是不希望中國企業走出去的。因為這些跨國公司,比如豐田、大眾、通用等在全世界其他地方也都有自己的企業。在不同地方也可能有本地伙伴,你去干嘛?
中國本土的企業才有更強的動力走出去,像吉利、奇瑞、比亞迪這些企業,沒有這個包袱,沒合資方,才有意愿。它往外走不需要擔心它的合作伙伴在哪里有布局。但是,這些往外走的企業雖然有意愿,目前能力還不夠強。要拼命干幾年。
《中國商貿》:您在演講中引用了卡羅斯·戈恩的一段話,其中提到“至少應該有一家中國企業能夠在這個市場上有20%的市場份額的大廠家。”您認為現有的中國汽車制造商哪家比較有可能成為在中國市場上占據20%市場份額的汽車企業?在您看來,要達到這一市場份額可能還需要多長時間?
武常岐:中國汽車中外合資這種形式把這個局面推遲了。一旦合資,中方就沒“勁”了。你是和跨國公司綁在一起了。合作伙伴不想你變成全球的大企業和它競爭。全球這個格局已經形成了,撼動并不容易。但并非沒有機會,通過自然生長和獨特的商業模式是一種可能性。另一種方法就是通過收購兼并。比如吉利汽車收購沃爾沃汽車,吉利集團的銷售收入就到了財富雜志排名的全球前500的大公司了,當然它還要邁好收購后整合這一步。
《中國商貿》:中國政府在這方面需要做哪些工作?
武常岐:政府也做了很多工作鼓勵自主品牌汽車發展,但也不是沒難處。因為中國13年前加入WTO,作為WTO成員要遵守相應的規則。
假如政府出臺政策說,政府只能采購自主品牌國產車,這就有爭議。有人會出來說這樣做違反WTO規則。跨國公司和某些外國政府就會講:你這什么意思?應該是公平競爭嘛。
中國政府會采取一些合適的政策鼓勵中國汽車產業,特別是自主品牌汽車的發展。但汽車產業政策也要考慮中國汽車企業的競爭能力,汽車產業的長遠發展、全球競爭和全球貿易總平衡。
比如前面我們提到的新能源汽車政策,受益比較大的還是國內的比亞迪汽車或者是長安汽車。
《中國商貿》:中國政府在建立統一大市場方面還有哪些具體的工作要做?
武常岐:因為中國的經濟改革采取了放權的方法,給地方政府更多的決策權,而不是采取中央計劃的方式,造成了地域間的壁壘問題。這個問題不僅僅是汽車產業的問題,而是下一步深化經濟改革的大問題。地方要做的事很多,經濟發展是頭等大事,地方政府就要想盡辦法發展本地經濟。在特定的產業政策下,汽車產業的利潤是比較高的,所以很多地方都想發展汽車產業,就像前些年各地都在發展光伏產業一樣。假如本地企業有競爭力,它就希望開放市場,而有些地方沒有發展汽車的產業基礎和比較優勢,就有可能滋生地方保護主義。
整體來講,現在中國地方保護主義已經改善了很多了。中國加入WTO就解決了一些問題,中國加入WTO很重要的目的之一就是建立國內統一大市場。在中國加入WTO以前,各省自己出臺政策,現在有大的原則,直接的地方保護已經不容易了。但還是有很長的路要走,特別是政策干預力度大的行業
《中國商貿》:我們注意到您在2007年曾有一個觀點:模仿式創新更符合中國企業要走的道路。請問:這一方式是否也適用于中國自主品牌汽車?
武常岐:創新的一種形式是原創,就是藍海,別人都沒做過,你來做這個事。其實,科學發展和技術進步都是在別人的肩膀上一步一步往前進的。英語中有句話就是不需要重新發明輪子,意思就是說咱們不需要再重新發明人家已經有的東西。我熟悉的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奧迪特·申卡教授最近寫了一本書,叫《COPYCAT》,直譯就是山寨。書中舉了大量的例子說明這樣一個道理:“聰明的公司總是通過模仿去得到戰略上的優勢”。
我說的模仿不是簡單地模仿,而是模仿式創新。不是簡單復制,而是在別人的錯誤中吸取教訓,在別人的經驗中持續發展。這就是模仿式創新。韓國三星電子為什么把日本電子企業打敗了。就是抓住了外部技術變化的機會。
中國有其得天獨厚的好處,就是市場規模。中國的經濟可以允許一兩個企業去試錯,賭一把,為其他企業鋪路。但對于任何一家企業還是要小心,如果韓國三星電子賭輸了,整個公司就完了。
《中國商貿》:我們注意到中汽協的董揚副會長不止一次地提出中國自主品牌汽車的同質化競爭,請問,您對這個問題有何評論?董會長對這個問題的解決并不樂觀。您認為這個問題的解決是否可能?這個問題的解決,你是否有所預期?
比如是否有可能存在一個您認為可能的時間表?
武常岐:董揚副會長是希望中國企業要在創新上下功夫,而不要在中低端在價格上同質化競爭。因為中低端汽車技術沒有很多突破,同質化競爭也是一個自然過程,關鍵這個競爭是否能提升自己。華為和中興兩家爭得很猛、爭得很兇,爭來爭去兩家企業發展起來了,其他不少跨國公司的電信制造企業反而死了。沒有競爭,就沒有變革和創新的動力。
汽車市場的過度分散和同質化競爭有政策原因,也有企業本身的原因。假如環境適合,政策適合,其實中國本土汽車企業的發展假以時日還是會有很好的發展的。做時間預測比較困難,因為可變的影響因素太多了。不確定因素太多了。
《中國商貿》:董會長希望少一些競爭,多一些聯合,提高整體競爭力,您如何看待這個問題?
武常岐:目前汽車行業的分割的局面,不是競爭造成的,而是行政干預和政策保護造成的。只有在激烈的競爭中才會出現行業大整合的機會。沒有地方政府的干預的話,整合的過程可能會比較快。十八大提出讓市場成為配置資源的主要力量,就是說市場的力量要發揮作用。產能過剩,市場分散,通過兼并之后就可以控制產能了。讓市場配置資源,可以是大企業把小企業兼并了,如果小企業技術和商業模式對頭,也可以是小企業把大企業兼并了,來個蛇吞象。這些都是市場配置資源的形式。
但是,現在不容易。有些地方政府從自身的利益角度去想,它不愿意被其他省份的企業給吃掉。你要兼并,有些地方千方百計阻礙你兼并,使得應該破產的企業繼續存活。中國做得不好的公司不容易死。現在的問題是競爭不充分。實際上,從經濟角度去想應該讓競爭更加充分,而不是阻止競爭。競爭不充分就是現在強的企業也沒辦法讓弱小的企業投降,難以被收編。
所謂同質化競爭,就是汽車整車廠的規模普遍比較小,而且也沒有整體的競爭能力,缺乏整合,那這個怎么整合,肯定是讓市場更加開放,讓該滅的企業滅掉,然后讓該強大的企業更加強大,在激烈競爭的程度上進行資產重組,這樣反而可以使得中國自主品牌置于死地而后生。
假如進一步放開汽車產業,外資廠商可能會賺很多錢。企業總是逐利的。如果汽車行業這么容易賺錢,企業家一定想盡一切辦法去學習技術、研發技術去做車。就像當年華為一樣,那時候外資企業在中國市場賺錢太容易,一個手機一兩萬。這么容易賺錢,那不把企業家的激情都給激發出來了?假如當時只能合資,一起賺錢,本地企業就沒動機去爭搶了,可能永遠就沒有了華為和中興。現在很多企業都是原來在外資企業干的,一看這么容易賺錢,為什么我們不能干?我們拉出來干。反而成功了。
汽車也是這樣,汽車行業長期保護是做不到的,從長遠看,也不應該,還是要鼓勵健康的競爭。
《中國商貿》:您曾談到“未來10年,汽車產業是朝陽產業。”今年的“中國汽車論壇”上,您談到“希望在2040年,我們可以再寫一本書《中國輪子全世界的道路》。”就中國自主品牌汽車制造業的現狀而言,您認為2040年實現“中國輪子全世界的道路”需要中國自主品牌汽車制造業做出怎樣的努力才能實現?
武常岐:我們2040年還是有機會。
我覺得如果政策對的話應該可以,但是,過程并不這么容易。
現在不應該統一采取捆綁式,自己可以玩,我們原來捆著玩的目的就是跟著外方學習。是不是到了時機,我們可以拉出來自己干了?我現在覺得可以讓一部分企業,至少是“三大”里面有一部分企業自己干,還有廣汽、北汽這些企業有規模有經驗的企業試一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