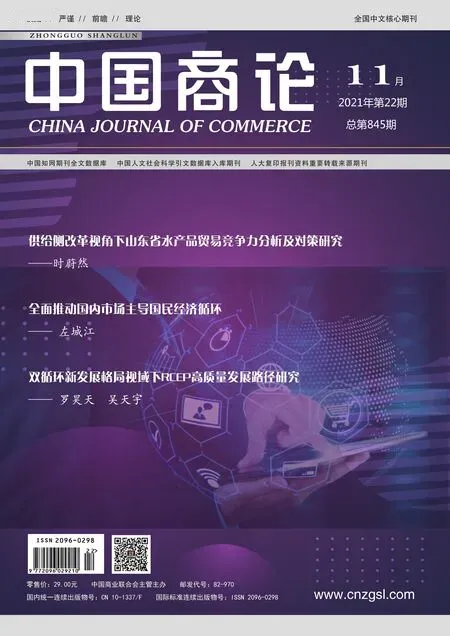莫氏社會發展指數尺度下的東西方競賽:評伊恩·莫里斯兩本文明發展史著述
徐瑾
(作者系FT中文網財經版主編、專欄作家)

所評圖書:
書名:《西方將主宰多久》東方為什么會落后,西方為什么能崛起
作者:(美)伊恩·莫里斯
譯者:錢 峰
出版日期:2014年5月出版
所評圖書:
《文明的度量》社會發展如何決定國家命運
作者:(美)伊恩·莫里斯
譯者:李 陽
出版日期:2014年6月出版
“東方是東方,西方是西方,兩者永無交匯。”英國詩人吉卜林曾經這樣寫過。事實是,早在20世紀這一波全球化之前,東西方早已經相遇,不僅有多次和平交流,更有各類戰爭沖突。有關東西方文明的比較不乏浩如煙海的討論,相關著述也汗牛充棟。西方緣何主宰當今世界?東西文明的分流如何發生?東方的落后是長期決定還是短期決定?文化重要是還是地理重要?從學界到民間,大家對于此類宏大話題無不有著極強的發言欲。鑒于此,跳出既有的研究視角就非常有必要。著名歷史學家、斯坦福大學歷史學和古典文學教授伊恩·莫里斯的《西方將主宰多久:東方為什么會落后,西方為什么能崛起》及其姊妹篇《文明的度量:社會發展如何決定國家命運》,在當下便頗有價值。據他的研究,西方的領先根本不存在長期決定或短期偶然因素,地理比文化等人為因素更為重要。
伊恩·莫里斯拋棄了英雄人物、文化因素以及人口基因等單一而主觀的慣常解釋,認為“過去16000年來東方和西方社會發展驚人的相似性,表明兩個地區的文化特性并沒有很大不同”。他認定人群同源,組成大致相仿,基因無太大差異,故解釋因素只有“地圖”。
莫里斯的觀點初看延續了賈雷德·戴蒙德《槍炮、病菌與鋼鐵》的邏輯,但其實他提供了很多可以度量的指標和生動的歷史細節。莫里斯選擇了長時段的歷史比較,從東西文明分野開始,時間跨度長達5萬年。他借助別的學科工具,創立了“社會發展指數”作為東西方發展的文明度量,以說明財富如何從東方轉移到西方,而最近的發展則預示著東方有可能在2050年全面超越西方。
在他的指標中,東西方一直處于此消彼長的競爭狀態,西方并非長期主宰。“截至公元700年,東方的社會發展程度比西方高了三分之一。”至于1500年之后東方的逐步落后,莫里斯歸結為海洋時代的來臨,“當沙俄和中國忙于關閉舊的草原通道時,西歐國家正在試圖打開一個全新的海洋通道,這一通道的開辟將更劇烈地改變整個世界的歷史。”
所有的爭論都是名詞之爭,何況是東西文明這樣的龐大課題。甚至定義西方與東方就是一個難題。據歷史學家諾曼·戴維斯考察,西方的學術定義超過二十種。為了避免東西方定義的意識形態化,莫里斯將“東方”和“西方”定義為歐亞大陸最東端和最西端的馴養生活核心地區。因此,“西方”最早是底格里斯河和幼發拉底河的源頭地區,隨后囊括了今日的歐洲以及美洲、大洋洲和非洲海岸;而“東方”,最早是黃河和長江之間的地區,后來則陸續包括東南亞、菲律賓、朝鮮半島、日本。選定研究目標之后,莫里斯確立了社會發展指數的能量獲取、社會組織、戰爭能力、信息技術四個特性。

莫里斯在《西方將主宰多久》中的框架并非無懈可擊,他對于東方的界定,對選擇的指標如何構成,有多少可信度,學界一直有不少批評和質疑。作為回應,莫里斯在新著《文明的度量》將社會發展指數延續到之前未被包括在其定義的東西方之內的新世界(如澳大利亞等),并宣稱得出一致結論。莫里斯強調,社會發展指數的主要貢獻是迫使分析家分析得更加清楚明確,“那些持不同意見者或認為指數設計或運用不合理的人,也能清楚地看到指數是怎樣運作的,進而再詳細批駁”。
莫里斯抱負宏大,立場也超越了簡單東西之分,跳出了長期決定論與短期決定論的窠臼,給予東西文明發展以清晰的歷史脈絡,試圖為未來人類文明發展廓清道路。數據始終是歷史研究中的命門,莫里斯的歷史數據也都是基于估算,但他強調其誤差最高不超過20%。對于有心的讀者,不妨在《文明的度量》中去比較印證。
對于國人來說,近代以來的落后成為思想隱傷、文化自卑,近三十年的經濟趕超還遠不能撫平,社會轉型以及國家走向仍舊是知識人群的熱門話題。過度缺乏的反面是過度補償,尤其是“中國落后只是偶然因素”這類話題,安德烈·貢德·弗蘭克《白銀戰爭》和“加州學派”的彭慕蘭《大分流》可謂代表。作為左派,前者將“歐洲中心論”視為霸權,把亞洲尤其是中國置于全球經濟的中心,肯定其在工業革命前的地位,之后的白銀供應縮水才是衰落原因。后者則試圖論證中國的落后僅在18世紀之后,甚至在18世紀70年代長江三角洲的經濟仍高于歐洲平均。至于自由派學者,達倫·阿西莫格魯的新著《國家的興衰》受到了不少關注,試圖從其提供的分析國家興衰的包容性與榨取性政治制度中,來定位中國的當下與未來。
也正因此,國人談及中西分別,文化決定論、制度決定論甚至宗教決定論的觀點層出不窮,動輒批判“中國文化本質”。而莫里斯對于國人最大價值之一,便是其對文化決定論的解讀。國人非此即彼的思維模式,往往無視世界的變化,比如文化因素過去認為是劣勢而后又被認為是優勢(比如儒家文化)。這種老生常談式的自省看似深刻,如果缺乏平行的比較,其實并沒帶來知識的邊際改進。在探究西方究竟“有”什么的追問背后,更多的是東方在后現代時期的匱乏感以及焦慮感。
展望未來,莫里斯不無悲觀,除了西方的沒落,更在于技術進步帶來的負面效應:“也許東方會被西方化,或者西方將被東方化;也許我們會共同生活在地球村里,或者我們會陷入文明的沖突里;也許每一個人都會變得更加富有;也許我們會在第三次世界大戰中灰飛煙滅。”也許如一些科學家所言,整個銀河系中有100萬個潛在的外來文明,外星文明之所以未能聯系人類,正是因為高智能生物的自我滅絕性,“所有這些證據似乎都表明,2045年我們將走向毀滅。這正是廣島和長崎被投下原子彈的100年后”。
未來究竟會怎么樣,人類如何才能避免類似科幻小說《三體》中文明崩潰的可怕場景,或許答案不僅在于莫里斯描繪的社會發展指數的宏大歷史畫卷之中,也在于他未能給予足夠重視的歷史人物以及文化因素之中——每個人是自身歷史的書寫者,也是人類共同命運的締造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