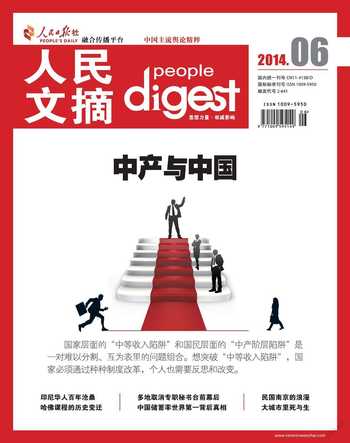中產與中國
邢力

曾經,全國政協委員崔永元關于月入過萬卻感到錢不夠花的“實話實說”引發熱議,而一則“北京上班族月收入7500元沒有安全感”的新聞在網上引起廣泛共鳴。
這位收入不菲卻焦慮不止的先生說:“經過一段時間的不懈奮斗,如今我在事業上已小有成就,但遙望未來,心中又充滿了焦慮和不安感:白天,我依然每天賣力工作,但收入增長卻越來越慢,晉升的愿望總是遙不可及,漸漸地對工作也起了倦意;到了晚上,打開電腦,看到精心挑選的股票和基金總是越買越虧,心中不免嘆息‘你一理財,財就離你’;打開電視,發現93號汽油都已進入‘8’時代,上海車牌更是直沖6萬元,看來買車計劃還得思量下;躺上床,老婆嘮叨著丈母娘又催促趕快生孩子了,但面對從‘蒜你狠’到‘向錢蔥’的詭異物價和今后孩子的擇校費、補課費、出國留學費等林林總總的潛在負債,便只能應付說‘再等等吧’;睡覺前翻了翻報紙,統計局說‘家庭年收入6萬元以上就算中等收入階層’的新聞在眼前突然亮了,但想想自己年收入將近10萬,這日子卻依然過得緊巴巴,不免心中涼了一大截;閉上眼睛,一想到馬上又到房貸還款日了,剛剛舒展的眉頭又緊皺了起來,內心深處傳來汪峰的那首《春天里》:‘如果有一天,我老無所依……’心中突然有了一種想哭的沖動……”
如果你也有崔永元和上面這位“焦慮先生”的這些煩惱的話,那便意味著你已在不知不覺中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緣起
所謂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是指當一個國家的人均收入達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順利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導致經濟增長動力不足,最終出現經濟停滯的一種狀態。很多新興市場國家突破人均GDP1000美元的“貧困陷阱”后,很快會奔向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起飛階段”;但到人均GDP3000美元附近,快速發展中積聚的矛盾集中爆發,自身體制與機制的更新進入臨界,經濟增長回落或長期停滯,陷入所謂“中等收入陷阱”階段。
根據世界銀行2008年公布的最新標準,已成功邁入“中等偏上收入國家”的中國也存在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風險。兩年前,世行前行長佐利克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共同發布的一份權威報告給中國敲響了警鐘。報告顯示,中國具備在2030年成為“高收入國家”的潛力和可能,但假如中國不改變發展模式并反思政府在經濟管理中的作用,中國的增長引擎就有可能在今后幾十年里受到阻礙,結果中國將難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中產階層的標準和困惑
與中國在經歷了快速發展后必然面臨增速放緩、結構轉型等壓力相類似,仔細想一想,其實我們很多人在個人財富積累的道路上,也常常不知不覺地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事實上,許多收入不低、職業體面的“中產階層”便存在這樣的困惑。
隨著我國經濟持續高速發展,近年來關于我國中等收入群體(中產階層)不斷擴大的新聞時有耳聞,然而究竟中國的中等收入階層規模有多大?中等收入的標準到底是多少?月薪7500元算得上中產嗎?
10年前,中國社科院社會學研究所的張宛麗就提供了一套判斷中國“中間階層”的標尺:即個人年均收入以及財富擁有量在人民幣2.5萬元~3.5萬元之間,購買私家車和有相應的社交文化消費。大致占就業人口15%。當時樂觀估計有1億人。
到2005年,國家統計局提出了一個標準:“6萬元~50萬元,這是界定我國城市中等收入群體家庭年收入(以家庭平均人口3人計算)的標準。”按照這個標準推算,到2020年,中等收入群體的規模將由2005年的5%擴大到45%。
2006年,“中國新消費者特別報告”把年收入在2.5萬元~4萬元之間的中國家庭定義為下層中產階級,把年收入在4萬元~10萬元之間的家庭界定為上層中產階級家庭。
2011年中國社科院發布的一份藍皮書則指出,根據恩格爾系數測定,到2009年,中國城市中等收入階層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在1.62萬元~3.73萬元之間;家庭可支配收入在4.86萬元~11.19萬元之間。2009年城市中等收入階層規模已達2.3億人,占城市人口的37%左右。
盡管由于測算標準不同,中產標準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但實際上國家統計局對中等收入階層還是有一個相對明確的概念。從統計學角度說,占社會平均收入水平和中位數收入水平之間的這個階層都應當屬于中等收入階層。而2011年我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21810元,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數為19118元。然而人均2萬元左右、一個三口之家6萬元左右的年收入卻很難與民眾對中等收入階層的理解契合。
由于大量在統計學上已屬中等收入的人群在現實生活中無法對他們的生活感到滿意,因此陷入了像上文中的“焦慮先生”一樣的“中產階層焦慮”中。
國家個人共同努力
事實上,國家層面的“中等收入陷阱”和國民層面的“中產階層陷阱”是一對難以分割、互為表里的問題組合。想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國家必須通過種種制度改革,如縮小社會貧富差距,打破壟斷行業堅冰,遏制房價過快上漲,健全社會保障體系等措施,只有這樣,中產階層才能在社會財富快速增長的過程中分享到足夠的果實,并在解除了住房、教育、醫療、養老等重負之后消除焦慮,敢于消費。反過來說,也只有當中產階層逐漸壯大并有能力也敢于消費時,內需才能真正擴大,進而促使產業結構升級,使國民經濟逐漸擺脫對出口和投資的過度依賴,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最終突破“中等收入陷阱”。換句話說,政府更關心“中等收入陷阱”,老百姓則更關心“中產階層焦慮”,其實是殊途同歸,一把鑰匙可以開啟兩把鎖。
面對“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戰,我們個人也需要反思和改變,不能坐等國家層面的改革,更應該積極發揮自身主觀能動性。一方面要努力尋求職場轉型和突破,或尋找職場外其他收入渠道,實現收入來源多元化;另一方面,也不能放松對投資理財的科學規劃,通過積極投資,合理控制支出等手段,實現財富積累的可持續發展和跨越式發展。當然,作為一種心理現象,想要降低中產焦慮,也需要我們積極調整心態。因為對財富的追求永無止境,只有適當降低自己對物質財富的渴望,減少與他人和社會的物質攀比,轉而更多地關注精神世界的財富,才能真正走出“中等收入陷阱”,收獲幸福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