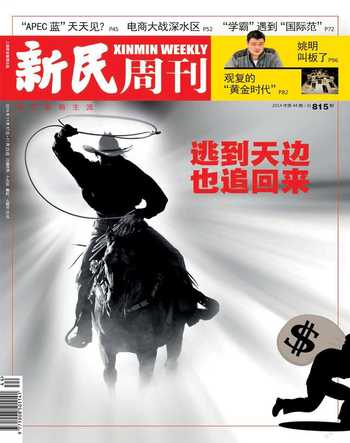胡震國的魅力
胡展奮

我和胡震國認識快四十年了。他曾任上海工藝美術職業學院美術系主任,其水墨風景畫近年來引人注目。
他原來是畫油畫的,作品多次入選全國美展和全軍美展,美術評論家盧金德先生對他的評價是:“胡震國的油畫色調就是法國印象色彩與中國江南湖光深情的融合。”
四十年前,我們一群二十不到的年輕人被分配到皖南工作,第一次見到他,便受感染,他喜歡哲學。佛陀。老莊。家具簡單,但四壁不是塞尚、梵高,就是徐悲鴻、齊白石……夫婦倆都是畫家,夫人叫王守中,這么說,他竟然就是王康樂的女婿?夫妻倆成天討論著繪事,討論著丹青得失。歲月一晃,竟然已是2014年的第十八屆上海藝術博覽會了,布展時忽然看到胡震國的作品,心情之激動,如異鄉見故人。
胡震國先生藝術上深受俄羅斯繪畫風格熏陶,色彩既斑斕又蘊藉,用筆既細膩又豐滿,凸現出鮮明的南派畫風情。但中年以后,他的藝術旨趣明顯轉向水墨風景畫,早年曾浸潤于連環畫的創作,使他的水墨畫筆頭具備了扎實的功底,曾經的皖南山區生活,又使他“胸中自有丘壑”,落筆自然倜儻豪邁,構圖自如,比如此次藝博會展出的胡震國的國畫《巴山夜雨圖》,氣象闊大,秋色磅礴,滿山黃葉,色彩絢爛,類似的題材,傳統手法常用水墨表現,但畫家覺得僅用國畫技法還不夠酣暢,遂點化古詩意境,借用油畫手法,以致畫面產生光影交錯,時空穿越之效果,空山、飛瀑、小橋、茅屋,看似無人,其實有人,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處?但茅屋的窗亮著,隱隱的燭光,給出了某種暗示,令人遐想無限,古人?今人?隱士?名士?離人還是旅人?畫家把極大的想象空間留給了我們,他回憶說,創作此畫時的心情是抑郁的,但詩心之力卻驅使他筆下的色彩異常絢爛,強烈的反差,一如雪中芭蕉,戰地黃花,賦予了作品特殊的藝術張力。
胡震國喜歡寫生,但又“雪藏”寫生,他把每次寫生的印記烙進腦海,任其發酵,然后慢慢回吐,最后憑記憶在更高的移情層面創作,比如其近年來表現手法獨創一路的園林和秀女,氣韻迷離,況味雋永,畫面總帶著淡淡的惆悵和濃濃的鄉愁。這跟其蘇州祖籍、尤其和他童年的傷感記憶不無關系,參展作品《疏雨》中的細雨芭蕉與太湖石,持傘淑女在徜徉凝視,但又為什么背對著我們呢……蘇州的水鄉讓胡震國一直夢牽魂繞,他似乎特別擅長畫那些靜謐的濕漉漉的小橋,橋邊或古樹下的一葉老舊的扁舟;河邊人家拾級而下的河畔躺著一彎冷月……
尤其令人難忘的是那幅《荷風》,蘇式涼亭之下有芭蕉,芭蕉之側有菡萏,一星眸麗人右手持傘,左手捫唇而笑——妙就妙在她用手背捫唇而笑,幾分矜持、幾分嬌憨,幾分慧黠,幾分爛漫,那是鄰家女,還是畫家蘇州童年的溫馨記憶呢?
畫里有畫,他的畫里始終藏著一個人,他的畫背后始終徘徊著一個人。
如同畫家張培礎所言,胡震國那種水墨風景兼具西洋田野畫所散發出的情調,總是如歌唱般的真情燦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