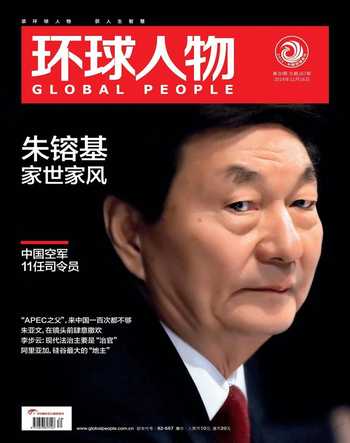誓詞背后的法治精神
和靜鈞
十八屆四中全會1.6萬字的《決定》中,哪條舉措得到的網民“點贊”最多?據中青輿情監測室統計,答案是“憲法日”和“宣誓制”。“建立憲法宣誓制度,凡經人大及其常委會選舉或者決定任命的國家工作人員正式就職時公開向憲法宣誓”,這是不少法學界人士期待已久的舉措,因為“權力來自憲法并忠于憲法,這一現代國家治理原則應當用一個宣誓程序體現出來”。
放在國際舞臺上,憲法宣誓制度并非新鮮事,而是早已有之的慣例。被憲政史研究者公認為最早的宣誓制度,是1086年8月1日的“索爾茲伯里誓約”。在英國索爾茲伯里原野神秘的巨石陣前,法國來的征服者威廉一世召集不列顛諸島的大小領主向他宣誓效忠,違誓者將遭“人定法與神明法的雙重懲罰”。
這個開端決定了西方領導人宣誓儀式的“雙重血統”——始終彌漫著宗教和法律兩種截然不同又同樣莊重的氣氛。1919年,德國《魏瑪憲法》首次提出領導人要“對憲法宣誓”,從此,憲法和《圣經》在領導人的宣誓臺上各領風騷。宣誓制度也就有了兩大流派:“依憲宣誓”和“對憲宣誓”。
美國是“依憲宣誓”的典型。《美國聯邦憲法》規定,總統當選后執行職務前必須宣誓;宣誓時手按《圣經》,面對聯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誓詞中表示“效忠于聯邦憲法”。這套復雜的規定體現了美國的政治傳統——美國是英、荷裔清教徒創立的移民國家,教神敬畏的傳統讓總統宣誓儀式充滿了基督教道義的正統感,手按《圣經》才能體現基督教道義。與此同時,基督教的家庭倫理觀也要在儀式上體現出來。這就不難理解,為什么美國總統宣誓時,衣著靚麗的第一夫人會站在一旁目睹宣誓或者捧起《圣經》,她的使命就是傳達基督教的倫理信息。
當然,作為一個“律師治國”的國家,美國總統宣誓必須體現出法律的元素。總統向國家最高級別的司法官——聯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宣誓,比向憲法宣誓更能形象地體現“敬畏法律與服從法律”。而“效忠于聯邦憲法”的誓詞,主要針對分裂歷史——聯邦制下的美國經歷過慘痛的南北分裂戰爭,在各州至今依然擁有州憲法的情況下,要求總統和大小官員“效忠于聯邦憲法”,也就具有特殊的意義。
相比之下,屬于“對憲宣誓”流派的俄羅斯,總統宣誓儀式就單純得多。他們抬出的不是 《圣經》,而是一部特制鑲金邊的憲法,與代表國家榮譽的功勛大勛章并排放在總統面前,總統右手伸直,按住憲法宣誓,誓詞中處處是維護國家安全的話語。整個儀式充滿了“戰斗民族”的政治性格:強烈而專注,集中展現“憲法主義”與“國家主義”。看到這樣的總統宣誓儀式,就能明白為什么越能維護國家利益的領導人越能收獲俄羅斯民眾的高支持率。
由是觀之,現代領導人宣誓制度的背后,隱藏著各國不同的政治密碼,也釋放著各國不同的政治信號。但其共通的一點,就是一個“法”字。莊重的儀式,由法律保證其不是一場形式;肅穆的誓詞,由法律保障其不是一句說辭。正因如此,宣誓制度成為領導人獲得合法性的關鍵環節之一。如今,在142個有成文憲法的國家中,規定國家公職人員必須宣誓擁護或效忠憲法的有97個。人們已經習慣,宣誓儀式完成后,選舉出來的領導人才正式成為領導人。
當然,在那些長于專制、弱于法治的國家,領導人再怎么宣誓,也只是走個過場。伊拉克總統福阿德·馬蘇姆今年7月24日才宣誓就職,8月10日就被總理指控為“蓄意違反憲法”。而在美國這種律師人數居世界之首、法治傳統深厚的國家,享有至高權威的聯邦最高法院和復雜的違憲審查制度,讓總統不敢輕易越過憲法的雷池。這也就是說,能夠約束領導人的,并非是一場儀式一句誓詞,而是藏在憲法宣誓制度背后的鋼鐵般的法治精神和司法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