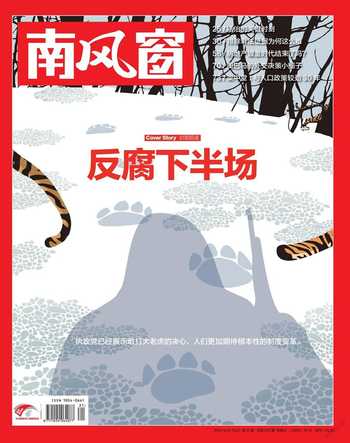“理性人”只是人性一部分
丹尼斯·斯諾爾
世界似乎正站在又一次“大轉型”邊緣。即將到來的改變將從根本上重新定義經濟互動的性質——以及作為經濟互動基礎的形態。
這次轉型的規模堪與8000多年前的那一次相比。8000多年前,人類從游牧狩獵采集社會轉變為定居農業社會,并最終創造出城市。10世紀的歐洲再次發生了類似的轉型,公會(guild,由控制著某地某門手藝的熟練工組成的聯合會)的崛起為工業革命鋪平了道路。
即將到來的轉型的具體特征尚不清楚。也許它將包括生物、納米和數字科技革命以及打破地理和文化壁壘的社交網絡革命。但是,已經清楚的是,和前幾次轉型一樣,這次轉型也將包括一切作為支持基礎的經濟關系和社會關系的根本性改變。
主流經濟學認為:當科技或其他變革讓人們能夠因為互相給予好處而獲得補償時(扣除成本之后),以價格為導向的市場系統將會變化。當變革創造出外部性,就帶來經濟結構重塑——如稅收和補貼的調整、監管變化和產權升級——以抵消市場無法補償的成本和收益。而當變革帶來特別高程度的不平等性時,就需要有再分配計劃。
這一觀點基于一個假設,即如果所有人都因為彼此提供好處而獲得充分的凈收益補償,追求自身私利的個人就會像亞當·斯密所說的那樣,“如同被看不見的手”引導服務于公共利益。這種觀點認為,每個人都是自私的“理性人”。
但是,過去的“大轉型”表明,這一觀點有失偏頗,因為它忽略了市場經濟的社會基礎。在這些經濟中,契約自愿達成而非通過強制。讓這些經濟運轉起來的不是保護商店窗戶不被砸的警察,而是人們的信任、公正,以及對榮譽承諾的歸屬感和對通行規則的遵守。如果缺少這一社會黏合劑,人們就無法利用所有可獲得的經濟機會。
這一聯系顯著地存在于大部分個體的經濟交易所帶來的社會影響中。當人們購買昂貴的汽車、定制服裝和豪宅時,他們總體而言是在尋求社會承認。當夫妻或朋友彼此送禮物或共同度假時,他們在通過親密關系和關心做經濟交易。
簡言之,主流經濟學——以及理性人的概念——只認識到我們的人性的一半。我們毫無疑問是受私利推動的。但我們從根本上也是社會生物。
從即將到來的將顛覆當代社會基礎的轉型的角度看,忽視這一點后果很嚴重。 事實上,從目前看,盡管經濟一體化前所未有,新的合作機會層出不窮,但我們的社會互動依然呈現出原子化(atomized)的特征。
問題在于根深蒂固的身份認知上。這一認知是分裂的。世界被分為許多民族國家,每個國家控制著許多公共政策工具。人們的社會忠誠則進一步被宗教、種族、職業、性別甚至收入檔次所分裂。
在社會壁壘足夠強大的地區,經濟壁壘必然會出現。這些壁壘包括保護主義貿易政策和日益嚴格的移民控制,甚至宗教戰爭和種族清洗。
顯然,經濟成功非常依賴于人們如何看待社會親密關系。一種觀點是我們的身份不可變、不可滲透、外生給定,并且內在地相互排斥。這一經典的“我們和他們”兩分法導致我們同情群體內的人,而與群體外的人產生不可調和的沖突——這也是歷史上無底洞一般的沖突來源。
但另一個觀點是可能的:每個人都具有多重身份,表現出哪種身份取決于人的動機和環境。這一觀點——其具有牢固的神經科學、心理學、人類學和社會學基礎——意味著個體在決定其身份中具有相當的自由意志。
這并不是說民族和宗教身份不具有深刻的重要性。相反,這意味著我們是我們的身份的共同創造者。我們可以不選擇分裂我們的身份,從而讓多邊全球問題難以處理;我們可以選擇擴大我們的同情心和道德責任心的身份。
越來越多的科學證據表明,同情心和其他技能一樣,可以通過教授和練習培養和加強。因此,教育機構可以致力于讓學生的關懷能力與認知能力同步發展。更廣泛地說,各地的社會應該由超越多樣化背景的共同目標所推動。解決跨境問題是一個很好的起點,給不同群體和國家分配具體任務的戰略能推進更大的利益。沖突解決工作坊、調解委員會、跨文化教育項目、畢業生義務社會責任等辦法也有所助益。
人們是完全自利的經濟行為人,這一主流觀點否定我們與生俱來的互惠能力、公正和社會責任心。在深刻的社會親密關系中,我們可以為新形式的經濟打下基礎,讓我們可以抓住多得多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