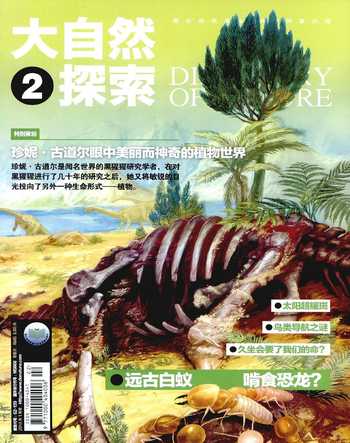鳥類的感官
編譯/方陵生





動物對世界的感知是什么樣的?1974年,哲學家托馬斯·內格爾在他的論文《假如你是一只蝙蝠,你眼中的世界會是什么樣的?》中指出:我們永遠也不可能真正了解它們的世界。他當時選擇蝙蝠來探討這個問題。他說,盡管蝙蝠和我們人類一樣,也是哺乳動物,但它們擁有我們人類所不擁有的利用回聲定位和測定方向的能力,而這是一種我們難以想象的能力。
或許,內格爾過于悲觀了。40年后的今天,人類對于其他動物如何感知世界已經有了廣泛的了解。在物種分類中,鳥類離我們比蝙蝠更遠,雖然我們不能準確地知道,作為一只鳥,它的感覺會是什么樣的,但對于它的感官世界,我們已經有了足夠的了解,特別是對于它的視覺的了解。那么,鳥眼是如何看世界的呢?它們眼中的世界又是什么樣的呢?
①鳥類的視覺
鳥類的視覺能力遠遠超出人類的想象,有的鳥類可以看到它們的身后,有的鳥類可以遠距離視物,有的鳥類可以看到人類看不到的紫外線,還有一些鳥類甚至可以“看”到聲音。
左眼右眼有分工
所有脊椎動物的大腦都分為左右兩半球,大腦神經系統的安排也非常有趣,左半球大腦處理來自右側身體的信息,右半球大腦則處理來自左側身體的信息。此外,大腦的某些認知功能由大腦左半球或大腦右半球負責。例如,大腦左半球的布洛卡區域專門負責語言能力,主管語言信息的處理和話語的產生。身體和大腦的偏側性或偏側優勢,如絕大多數人用右手,曾一度被認為只有人類才擁有,但到上世紀70年代,科學家研究發現,金絲雀專門用左側大腦來控制它們的鳴唱行為。
我們如今已經知道,鳥類大腦的偏側傾向甚至更甚于人類。有趣的是,鳥類的兩只眼睛長在腦袋的兩側,而不像我們并排長在前面,這可能更進一步促使了它們左右眼的明確分工。例如,剛出生一天的小雞往往會用右眼尋覓食物,而用左眼警惕潛在的捕食動物襲擊。
或許有人會認為這是一種奇特的遺傳基因所致。事實卻是,正常情況下,小雞在破殼孵出前,是右眼對著外面的,右眼可以接收到透過蛋殼進入的光線,而朝向內側的左眼則沒有接收外部光線的機會。但是,如果你能將蛋殼中小雞的腦袋轉個方向,讓它的左眼接收到光線,那么它的左右眼偏側性就會反轉過來,與正常情況正好相反。
鳥類能夠聽聲“視”物
南美大怪鴟和金絲燕是兩種完全不同的鳥類,但它們都擁有一種不同凡響的能力,即利用回聲定位和測定方向。雖然它們與蝙蝠不同,能發出一種可以聽得見的短暫而尖利的“喀噠”聲,但它們聽聲“視”物的原理卻和蝙蝠是相同的:都是利用聲波遇到障礙物后反射回來的回聲在黑暗中“視”物。對于蝙蝠而言,它們對低頻聲波的辨別能力不如高頻聲波那么有效,而研究人員發現大怪鴟聽聲“視”物能力極強,可以定位直徑大于20厘米的障礙物,這種能力足以讓它們在黑暗的洞穴中輕松尋找到自己棲居的巢窩。
內格爾認為人類無法想象回聲定位是怎樣的一種感覺,事實上他錯了。研究人員對一個盲人少年進行的山地騎自行車測試實驗發現,盲人少年可根據兩個車輪發出的與大怪鴟類似的2千赫茲低頻的“喀噠”聲安全前行。
鳥類視野與眾不同
我們對鳥類有著某種認同感:我們和鳥類一樣,都是兩足動物,基本上都是一夫一妻制,都極度依賴視覺。我們與鳥類有著很多表面上的相似之處。然而,鳥類眼中的世界與我們人類是大不相同的。
首先,鳥類擁有三種不同的視域,或者說視野,究竟是哪種視域則取決于它們眼睛生長的位置。眼睛長在腦袋兩側的鳥類,如山鳥類、知更鳥等,擁有良好的兩側視野,以及部分面前的視野,但看不到它們身后的景象。眼睛高高地長在腦袋兩側的鳥類,如鴨子和丘鷸,也有良好的兩側視野,實際上它們可以同時看到身體兩側,還可以看到腦袋后面,但它們看不到自己的嘴的尖端。眼睛長在臉的正前方的貓頭鷹,和我們人類一樣擁有雙目視覺(這不僅僅是因為良好的視覺對它們來說非常重要,還因為沒有別的地方可以安放它們的大大的夜視眼睛)。
鳥類和人類視覺還有更多的不同之處。一些鳥類,如歐洲藍冠山雀、相思鸚鵡和斑馬雀等,可以看見人類看不到的紫外線光。還有一些鳥類,特別是天上的捕食猛禽,如鷹隼、獵鷹等,可以看到人類目力遠不能及的遠處。
鳥類眼睛與人類眼睛為什么如此不同?部分原因是因為眼睛的結構不同。人類眼睛后面的視網膜只有一個小凹,用來聚集影像的感光點,而鷹等天上的猛禽,它們每只眼睛里都有兩個這樣的小凹,相當于同時擁有遠距鏡頭和超近鏡頭的攝像機。還有其他一些鳥類,包括海鷗等,擁有一條橫貫視網膜的小凹,所以它們可以一直保持水平方向的視野。
“眼睛導引翅膀”,早在1943年,就有一位眼科專家在一本關于脊椎動物視覺的小冊子中描述鳥類特征時如此寫道。除了新西蘭產的一種叫作幾維鳥的夜行無翼鳥之外,對于大多數鳥類來說,視覺顯然是至關重要的,但鳥類的其他感官同樣也很重要。
②鳥類的觸覺和聽覺
一些鳥類,如水中覓食的鴨子,在夜間捕食的貓頭鷹,以非凡的適應能力來支持它們的這些日常活動。從表面看,研究鳥類的聽覺或觸覺敏感性似乎也不太可能給人類帶來什么益處。但事實并非如此,例如,關于鳥類聽覺研究的一些發現,可給治療人類耳聾和神經退行性疾病帶來很多啟發。而對于鳥類的觸覺的研究,誰又知道會帶來多少實際應用的啟示呢?
敏銳的觸覺感官
在鳥類中,很少有像鴨子那樣是在水中游的。鴨子戲水看起來再平常不過,但實際上,隱藏在鴨喙中的感官能力令人難以想象。
在鴨喙尖端的半圓形區域里,有許多觸覺小體,鴨子能用它們探測水面的波動。靠喙對食物的觸覺,再與嘴中的味覺受體結合起來,鴨子還能區分哪些食物是可食用的,哪些是不能食用的。
除了鴨子,其他許多鳥類的喙尖上也有觸覺受體,如幾維鳥、涉禽類,它們用來尋覓隱藏食物的觸覺受體極為豐富和成熟。例如,在沙灘上覓食的禽鳥,它們可以通過觸覺受體尋找到可吃的雙殼貝類。
鳥類敏銳的觸覺不僅能夠幫助它們尋覓到更多食物,在鳥類的社會活動中也起著重要的作用。許多鳥類都會花很多時間用喙為同伴梳理羽毛,這與靈長類動物相互為對方理毛的社交活動相類似。這種個體間的接觸交往可能是通過皮膚上的感覺受體,或者通過一種叫作毛羽的感官羽毛來進行的。鳥類用喙清理羽毛的行為與靈長類動物的理毛行為有著異曲同工之妙,都會導致釋放帶有善意的化學物質,從而促進個體間的聯系。
非同一般的耳朵
貓頭鷹能夠在黑暗中視物,但一些傳奇故事顯然夸大了它們的這種能力。事實上,雖然貓頭鷹在較暗的光線下仍然擁有極佳的視力,但在完全的黑暗中,它們是什么都看不見的。鮮為人知的是,貓頭鷹最為出眾的不是它們的視覺能力,而是它們杰出的聽覺能力,而聽覺能力在任何時候都不受光線條件的限制。
如果你仔細觀察就會發現,好幾個種類的貓頭鷹的耳朵都呈不對稱的位置,但請不要與它們那叢絨毛樣的“耳朵”給混淆起來。以大灰鷹為例,它們的兩只耳朵的位置一高一低,這種不對稱導致聲音抵達兩只耳朵的時間或音量都稍有不同,正是這種微小的時間差別,或音量差別,讓貓頭鷹可以精確定位聲音的來源。
大灰鷹是貓頭鷹中體形最大的,但它們卻是白天的狩獵者。利用它們出眾的聽覺能力,它們可以發現躲藏在雪地里的嚙齒動物,然后通過精確的定位能力,抓出隱藏在雪下的獵物。
獨特的耳蝸結構
鳥類擁有出眾的鳴唱能力,科學家對于鳥類的叫聲和“歌聲”投入了大量的研究。相比之下,科學家對于鳥類聽覺的研究實在是少之又少,而部分原因在于:鳥類是從爬行類動物演化來的,它們沒有外耳或耳廓。
鳥類能夠聽到我們所能聽到的所有聲音,盡管它們只有一塊聽小骨(這同樣源自于它們的爬行類祖先),而不像我們擁有三塊聽小骨。有意思的是,生活在溫暖氣候條件下的鳥類,它們的聽覺能力在一年里的不同時段會產生一些波動和變化。這是因為,它們大腦里負責聽力的區域在繁殖季節里會更發達一些,而在繁殖季節過去之后,當鳴唱求偶行為不太重要時,這部分大腦的功能就會萎縮。如果能夠充分理解鳥類大腦的這種機制,將有助于人類尋找治療阿爾茲海默氏癥和其他神經退行性疾病的線索。
鳥類聽力與人類聽力的另一個重要不同,在于它們的內耳結構,特別是耳蝸(內含能感知振動的聽毛)。人類的耳蝸形似蝸牛,故得其名。鳥類的耳蝸則形似香蕉。耳蝸中的聽毛細胞可檢測到聲波壓力的變化,并將其轉變為電信號,大腦將這些電信號作為聲音信號接收下來。重要的一點是,受損的聽毛細胞無法更新替換,因此耳聾給許多老年人帶來無以逆轉的痛苦。而對于鳥類來說,卻不存在這樣的問題,它們可以不斷地長出新的聽毛來。如果我們能夠從基因層面來詮釋這一現象,或許就能用以解決普遍存在的老年人的聽力喪失問題。
③鳥類的味覺、嗅覺和“第六感”
鳥類的味覺和嗅覺一直是引起諸多爭議的問題。而如今,鳥類的“第六感”也引起了科學家們極大的興趣。堅硬的喙,再加上不表露任何喜好的臉,鳥兒似乎不會對食物味道和氣味做出反應——這也部分解釋了為什么鳥類學家始終沒有將鳥類對味道和氣味的辨別列為其屬性之一。事實上,我們對鳥類的一些潛在能力所知甚少。
撲朔迷離的鳥類嗅覺
很久以來,鳥類學家一直認為鳥類缺少嗅覺能力。20世紀初的一些證明鳥類沒有嗅覺的研究更是“證實”了這一偏見。在其中的一項研究中,研究者在火雞面前放兩盤食物,一個盤子里的食物上澆有一些味道濃烈的調料,如熏衣草油,另一個盤子里的食物上則不添加有其他氣味的東西。火雞很快將兩盤食物吃完,之后又毫不猶豫地吃下第三盤食物——被氫氰酸污染的食物。當然,這只火雞最后死了。人們于是得出結論認為:鳥類沒有嗅覺。
盡管早期解剖學對此提出了相反的證據,但這種錯誤觀點還是以訛傳訛地流傳了下來。1837年,英國生物學家理查德·歐文在解剖一只土耳其兀鷲后得出結論說,這種鳥有著“發育良好的嗅覺器官”。他還在剛被人們發現不久的幾維鳥的大腦里找到了嗅球存在的證據。之后的一些觀察還發現,野地里的幾維鳥在夜間會在矮樹叢下嗅來嗅去尋找蚯蚓。這些都毫無疑問地表明,這種鳥會利用嗅覺來覓食。但是,由于幾維鳥與其他鳥類有著很大的不同,這些證據很容易被認為只是一種例外。
直到上世紀60年代,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貝蒂西·班的研究終于扭轉了人們對于鳥類嗅覺的偏見。她發現人類鼻腔中用來溫暖吸入空氣以及檢測氣味的鼻窩結構,一些鳥類也同樣擁有,只是更小更精致而已。她據此認為鳥類也有嗅覺。在對鳥類的嗅球進行了深入研究后,她發現,不同種類鳥類的體形大小不一,它們的嗅球大小占大腦的比例也不一樣,反映了它們各自不同的生活環境和生活方式對嗅覺的依賴程度。
如今,人們對鳥類嗅覺的認識已大有改觀,最近一項描述信天翁和海燕嗅覺能力的研究稱,這些鳥類生活在“嗅覺構成的海景中”,靈敏的嗅覺幫助它們尋找食物,繁衍后代,甚至筑窩建巢、尋找配偶也離不開敏感的嗅覺能力。
鳥類也有味覺
狗通常被認為“狼吞虎咽”地迅速咽下食物,它們似乎根本沒有花時間去品嘗食物的口味。但事實上,狗主人都知道,狗并不是對食物不挑剔。對于鳥類來說,其實也是這樣。
很早以前,達爾文和華萊士研究鳥類的同行韋爾的一些研究證據表明,鳥類也有發育完全的味覺。他在給鳥喂食巢蛾毛蟲時觀察到,籠子里的鳥兒搖晃著腦袋,厭惡地將毛蟲吐了出來。之后,華萊士的一些研究表明,鳥類感覺味道難吃的毛蟲通常都帶有鮮艷的“警告色”,擁有這兩個特點的毛蟲發出的信號就是:“我不好吃,請別吃我!”
后來的研究表明,像我們人類一樣,鳥類的舌頭上也有味蕾。不過,令研究人員感到困惑的是,鳥類的味蕾似乎太少,不足以用以區分食物的好吃與難吃。1974年,荷蘭萊頓大學的研究人員在鴨喙上發現了疑似味蕾的東西,通過顯微鏡下的仔細觀察發現,原來野鴨共有五簇味蕾,四簇分布于上顎,一簇分布在下顎,而舌頭上則沒有味蕾。雖然鳥類的味蕾遠少于哺乳動物——人類有數萬個味蕾,野鴨只有400個味蕾,但它們就像我們人類一樣,同樣擁有對甜酸苦咸的品嘗能力,至于它們是否能品出人類情有獨鐘的鮮味來,目前還沒有經過實驗證實。
鳥類神秘的“第六感”
鳥類的另一種鮮為人知的能力——檢測地球磁場的神秘能力,如今正在引起研究人員的極大興趣。
許多鳥類的導航能力堪稱神奇。在威尼斯的教堂塔樓上放飛一只馬恩島上的海鷗類飛鳥,它們可以準確無誤地回到英國西海岸沿海一個島嶼上的它們出生的巢穴中。它們是如何做到這一點的呢?燕子和其他許多鳥類又是如何冬去春來,在地球南半球和北半球年年往返不絕的呢?它們是如何尋找到正確的飛行方向的呢?為什么它們擁有如此神奇的導航能力呢?一個世紀以來,這些問題一直困擾著鳥類學家。
如今我們知道,鳥類體內擁有多種導航機制,包括利用太陽和星星導航,以及利用嗅覺導航等,而最新也最神奇的發現是鳥類利用地球磁場導航的能力。這曾經被認為是不可能的,但上世紀80年代,越來越多的人開始相信鳥類確實擁有這種神奇的“第六感”。我們不知道鳥類是如何做到這一點的,但我們知道它們確實擁有這種不可思議的神奇能力。
最近的研究發現,鳥類不僅能夠檢測到地球磁場的方向,甚至還能通過某種化學反應檢測到磁場的強度。早在上世紀70年代,物理學家就已經知道,某些化學反應能夠因磁場而發生變化。更奇異的是,科學家在對歐洲知更鳥的研究中發現,通過鳥類右眼的光線可產生這種變化。目前研究人員正在研究這種反應具體發生在鳥類身體的哪個部位。一些科學家猜測,鳥類甚至可以“看見”地球磁場的輪廓線。對人類來說,這確實是非常難以想象的。
看似不可思議的鳥類感官研究有著改善和提高人類健康水平的巨大潛力,鳥類身上還有許多我們不知道的秘密等待我們去發現。那么,關于鳥類的感官,下一個有趣的問題會是什么呢?
在鳥類所有的感官和感知中,最為有趣的是情緒。那么鳥類真的有情緒嗎?它們能感覺痛苦和快樂嗎?一些人認為,非人類無法像人類一樣體驗這類情緒,因為它們沒有情感意識。這確實是一個棘手的問題,因為意識究竟是什么,很難清楚并具體地加以定義,也很難以任何客觀的、科學的方法來加以衡量。然而,如今有證據表明,鳥類也擁有豐富的情緒。例如,許多鳥類都能維持長久的伴侶關系,也不乏鳥類久別重逢表達喜悅行為的傳聞軼事。這些都表明,一些鳥類也擁有維系情感的紐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