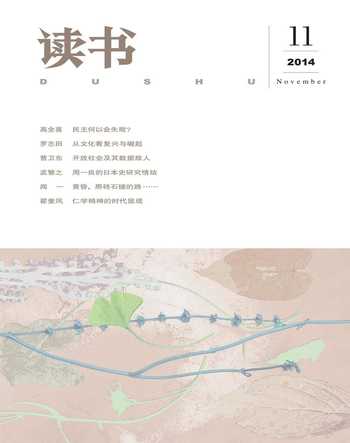何處是“地方”?
吳昱
就古代史而言,職官制度研究歷來被認為是歷史學的“四把鑰匙”之一。但在近代史領域,事件和人物研究似乎更受關注,因此近代中國職官制度的研究,凸顯兩個相互關聯的缺陷:其一,在研究方法上,一些研究者往往將章程條文簡單等同于制度設置及運作實態,忽略制度發生的淵源以及因時、因地、因人而異的流變;其二,由于近代中國的制度變革大都移植模仿東西洋列強,且此后的制度又基本延續了變革的基本方向,以致今人很容易用后來的觀念理解前人的意思及行事。
關曉紅逾十年之功研究晚清的官制改革問題,其新著《從幕府到職官:清季外官制的轉型與困擾》抓住理解整個清朝職官設置的關鍵,即省制的淵源流變,重點考察一九零六年開始的外官制改革,如何“改變了隋唐以來皇朝體制的傳統結構”。尤其是政體變革蘊涵“近代中西觀念與制度的對接與差異、移植與傳承的成效及問題”,關系十分重大。閱讀這一段歷史,會令人想起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中的名言:“對于一個壞政權來說,最危險的時候就是剛剛開始改革的時候。”既往在民族主義話語及革命思維影響下的清末歷史書寫,大多將清代失去統治的合理性歸結于沒落腐敗,但如果將目光放遠,深入到體制內部,或許更應該思考,為什么“旨在挽救統治危機的改制,反而激化各種矛盾”,從而加速清朝的覆亡?問題的答案,只能從清代官制前后截然不同的設置本意,以及新政變制遭遇的困惑去尋找。
清季的外官改制,最為關鍵及令人困擾的問題,就是直省的屬性與地位。今人習慣于用中央與地方的觀念來考察與認識京師與各省的關系,實際上與清代原有體制相去甚遠。只有從梳理直省及其長官(督撫)在清代職官序列中的狀況入手,探究當時人和后來者用近代西方憲政中央與地方的架構認識清朝乃至民初制度的不相鑿枘,才能發現與理解其中的困惑與糾結,厘清歷史文化在制度興革過程中的復雜作用及影響。
晚清取法西洋的官制改革,設計思路與實際舉措較此前有著明顯的區別。原來官制重在“內外相維”,自上而下地分權制衡,竭力杜絕歷代導致皇朝崩潰的弊端之一—藩鎮割據的出現。這種分權制衡的體制,在清朝鞏固統治的過程中曾起了關鍵作用,其中分省和督撫的地位成為聯結這一體制的樞紐。
清代的行省,與分事而治的京師部院平行,其作為皇權的分身,代行分地而治的職責。行省并不是一級行政,更不是最高層級的地方行政。督撫作為清代職官內外聯系的重要樞紐,一身二任,身兼兵部尚書或侍郎、督察院右都御史或右副都御史之銜,其考核亦屬于京官的“京察”而非外官的“大計”。
清中葉以后,傳統體制面臨內憂外患,開始悄然發生變化。隨著行省變為直省,分省的意識日漸強化,原來以府廳州縣為單位的舊行政格局發生變化,省的地位與作用更日益凸顯。晚清的洋務和新政,無論辦實業、練軍隊還是派留學、興學校,大都以省為單位舉辦施行,使得督撫和省的地位角色大為強化。傳統的“幕友制”難以滿足行政事務劇增的需要,督撫因事而設的各種專門或臨時性局所,實際上逐漸演變成為辦理各項事務的職能部門。
不過,雖然“內外相維”的體制逐漸被打破,但清廷始終把握督撫的黜陟權,而避籍制度又使得督撫及其屬官對轄區難以產生鄉梓情結,因此無法形成盤根錯節的地方勢力。再加上清代督撫調動頻繁,即使想要占山為王,也受限于規制的重重約束。
近代中國的制度變革雖然取法西方,將省指為地方行政層級,卻是東洋人的說法。與此截然相反,此期到日本游歷的中國官紳,卻認為日本的府縣只相當于中國的縣。故清末仿行日本的地方自治,只涉及府廳州縣,省并不在地方自治的范圍之內。
清季官制改革,主導方向是模仿列強的政體,將內外相維變成上下有序,以提高效率。這的確有讓直省變成地方行政最高層級的趨向。只是無論從歷史的延續還是現實的考量,要將直省變成地方,督撫變成地方官,都有“剪不斷、理還亂”的麻煩,甚至連當事人也常常陷入無法溝通古今中外的困擾。從法理上看,“皇權與部院,其實并非近代意義與地方相對而言的中央。皇權天授的絕對權力,使得直省的督撫,也不等同于地方官”。而近代意義的“地方自治”,指的是“選地方人、用地方財、辦地方之事”。就此而論,所有必須避籍的州縣以上官員,都不是這種意義上的地方官。
如果中央與地方之辨僅僅只是權力之爭,清季外官改制的意義和影響也就相當有限。辛亥革命結束了兩千年雄踞帝制頂層的皇權,卻使得省制問題重新具有藩鎮的色彩。省是否地方、省級軍政長官是否地方官員,不但涉及專制與民主的兩極對立,還和集權與分治、統一與割據等等矛盾相互纏繞。清末地方自治的嘗試只到府縣,民初朝野中有人主張聯邦制或邦聯制,卻因妨礙大一統而最終被否決,表明中國歷史文化中始終有濃厚的統一情結,而朝野輿論亦以此為底線。北伐打倒軍閥之目的,就是結束割據混戰。地域遼闊、人口眾多卻不適宜西方的聯邦或邦聯制的中國,如何確保統一而避免專制,實行民主又防止分裂,省制問題,正是問題癥結所在,亦是兩難抉擇。
一言以蔽之,清末民初改革的曲折反復表明,由于省的屬性與地位,及其與中央政府的關系沒有現成的模式可以套用,百余年來摸著石頭過河,至今仍有必要不斷借鑒、探索和調整。盡管今日“省”一級架構已被明確標識為“地方”代表,但在實際行政中仍存在與中央直屬權力體系發生糾葛與爭執的風險,行政權力的縱橫矛盾依然沒有得到有效解決。由此,則重新認識清代內外官制的原來面貌,可為今后的改革提供有效的歷史借鑒,而審視清末外官制改革的成敗得失,弄清楚東西方歷史文化的差異,避免移植與借鑒外來政體的淮橘為枳、東施效顰,又能為今人警覺改革的風險提供足夠的準備。
除了在具體研究領域大幅度提升認識水準,關著更重要的還在于方法上的啟示意義。即借鑒前賢研究中古制度史的成功經驗,加以豐富發展,應用于史料極大豐富的近代史研究。主要體現于三方面:一是貫通新舊材料、官私文獻以研究重大問題;二是將制度研究從靜止的條文鋪陳變成講究淵源流變的動態,尤其注重章程條文與社會常情及其變態的相互作用;三是將近代知識觀念的更新與制度變動聯系考察,并注重區域與階段的差異、實際成效與存在問題。
將中古史大家的研究良法運用于近代史事,最大的挑戰是如何在浩如煙海的各類史籍中去粗取精、去偽存真,這對研究者的體力、精力與學識都是巨大的考驗。除了政典、文書之外,日記、書信、報刊這類零碎但卻可協助深入當事者內心世界的材料,經過細致甄別,可更直接幫助體會當時人的心境與選擇。關曉紅新著中,有不少此類例子。
在古今中外社會的常情與變態中考察晚清外官改制的章程文本,將靜態變為動態,全面甄別與駕馭資料,揣摩把握形似而實異的立意與設置,能夠將思想、制度還原為歷史,不僅可以呈現知識與制度發生演化的歷史軌跡,還有助于對觀念制度的認識深入一層。例如“地方”中外之意的差別,與專制民主關聯,伴隨著“地方自治”理論進來的西方憲政,與中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皇朝體制完全不同,而歷史上的分合循環,使得穩固王朝的統治與維護國家的統一相輔相成。西方憲政移植到中國,在專制與民主的考量之外,增加了分裂與統一的權衡,朝野都力圖避免內部的紛爭導致國家的解體,因而自治只行于府州縣,縮小省區劃分以防體大失控的設計,也由此而興。該書從一脈相連的歷史發展中梳理改制癥結與方案的權衡,涉及清季外官改制的全過程和各方面,都值得認真借鑒,
一般而言,歷史研究不必刻意強調有用,不過中國文化一脈相承,近代歷史又距今不遠,尤其是晚清以來的知識與制度轉型,可以說是百年來中國知識與制度發展演化的起點。正如該書的結語所言:“清季政體改革的成果,則成為共和國繼承的重要遺產,其內外官改制過程的種種教訓,亦給未來中國的發展以珍貴啟迪。”今日中國同樣處在改革的十字路口,從歷史發展的真切角度去體會過往的成敗得失,方能認準癥結,予以破解,尋找到一條真正合適國情時勢的復興之道。
(《從幕府到職官:清季外官制的轉型與困擾》,關曉紅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二零一四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