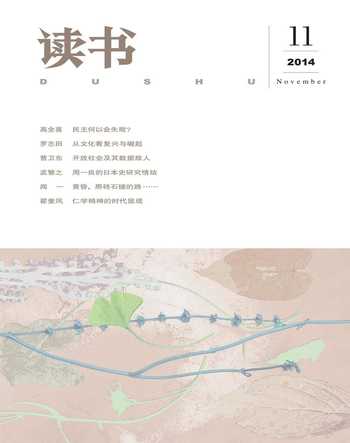美育之難
黃大剛
田家青新作《和王世襄先生在一起的日子》出版后,我讀了很久,因為,我每讀到一些關于王世襄先生的故事和對話,就不由自主地把書放下,王先生講笑話的樣子、聊到高興處的樣子和不高興的樣子,還有當年藏在我心里的事情,一一涌上心頭……
我在書中細品著王先生的為人、做事、治學、鉆研,之后卻又有了幾分憂慮——王先生曾憤憤談到明式家具“能使用”的優點,反而讓它不能算作藝術品——“這純屬一個荒唐悖謬的理論”(第28頁)。本來這是一個再簡單不過的事情。在芳嘉園十五號住過的張光宇、王世襄、袁荃猷、黃苗子、郁風以及許多常來串門的藝術家看來,美是判斷物件是不是藝術品的唯一標準,不管它是器物還是繪畫、雕塑抑或文物。像面人湯、泥人張的經典作品,明式家具(注意,不是所有明代的家具)都是藝術品,都凝聚著創作者的思想感情,凝聚著可以恰如其分地反映那種思想感情的高超技藝,從而具有獨特美感。反過來說,繪畫作品也不見得都是藝術品,有些也就是垃圾——畫家幾乎都有把自己不滿意的作品撕掉扔掉的事,當然也有自己很得意,卻被別人當作垃圾處理的事。
這本來不是事的事,竟然成了讓王先生憤憤不平的事了!
由此我又想到了“工藝美術”這個詞。《現代漢語詞典》是這樣解釋的:“指工藝品的造型設計和裝飾性美術。”那么再看看“藝術”這個詞:“用形象來反映現實但比現實有典型性的社會意識形態,包括文學、繪畫、雕塑、建筑、音樂、舞蹈、戲劇、電影、曲藝等。”似乎不包括工藝美術,這符合今天世人的理解。
但是,“工藝美術”一詞在張光宇先生那里卻是另一番意義。早在上世紀二十年代他就提出:“研究人生日常生活中所需要的藝術便是工藝美術。”在三年后出版的《近代工藝美術》這本書中,人們更可以清晰地看到張光宇先生心目中的工藝美術是什么樣子的,他以九個部分來介紹、評論近代工藝美術:近代建筑、室內裝飾、小工藝、染織工藝、商業繪畫、雕塑與廣告、書面裝飾、攝影廣告、舞臺工藝,都是“人生日常生活中所需要的藝術”。
細數王先生的研究和收藏,很多也都是“人生日常生活中所需要的藝術”,為此,他付出了常人難以體會和理解的心血。明式家具自不用說,葫蘆、鴿哨、漆器、竹刻……每每看到他的收藏,他的朋友都是愛不釋手、贊不絕口。王先生和他的朋友們都是懂美的人,他非常希望讓更多的人分享這些藝術,并將其發揚光大。因為,正是這些“人生日常生活中所需要的藝術”,不僅在美化我們的生活,也潛移默化地提高著人們的審美情趣。
然而,理想和現實的反差有時實在太強烈。例如王先生的研究在海內外引起很大反響后,明式家具終于被重視了。同時,也出現了一個魚龍混雜的新市場:仿古家具市場。田家青曾在王先生支持下,編著了《清代家具》一書。應收藏者的要求,其中一件扶手椅的坐面到地面的尺寸故意標錯,以防作假。他認為:一看這尺寸就該知道不對——不是樣兒啊!在不知道實際尺寸的情況下,也就不去仿制了。誰知,竟真有人用紫檀全盤照抄,做出來的扶手椅上下比例失調,“難看至極”,暴殄天物。
今天,明式家具真的“值錢”了,就像紅木家具廣告說的,“不怕我家沒有人民幣,就怕我家沒有好家具”。于是也帶著古舊家具都“值錢”了,過去老舊家具散架了,就當劈柴燒;現在都得留著。可這個“值錢”和王先生說的“值錢”大不一樣,王先生是按藝術品級衡量,在拍賣市場上與同品級的藝術品價格大致相當,說的是“值不值錢”,看的是藝術高下。而在一些人那里,看的是價錢,以為價高藝術價值也不會低;更有些人看的就是值錢,藝術價值不重要,求個增值,這種人還真不少。
二零零三年嘉德為王先生和袁先生舉辦了“儷松居長物志”拍賣會,我曾陪父母去參觀了展覽,事后得知拍賣會氣氛異常熱烈,父親就打電話表示祝賀,我清楚地聽到王先生說:“這人都瘋了,好些東西都不值那個錢!”顯得很淡然,似乎也有些不以為然。淡然并不讓我意外,為什么不以為然呢?這次,我在家青的這本書里找到了答案:拍賣會結束后,王先生對來訪的客人曾說過這樣一句話:“這不是為了買去‘說山’嗎?”
王先生不幸言中:他收藏的紫檀龍海獸筆筒,二零零三年以三百萬元成交,二零一二年又以七千萬元拍出;二零零三年以一千萬元落錘的十只香爐,二零一二年又以十倍的價格拍出(第171頁)。
看到這種情況,我不知道是該高興還是該難過?
收藏品買來是為了“藏”的,股票買來是為了“賣”的。然而,黃鐘不語,瓦釜雷鳴。真正的藏家不事張揚,我們平日里聽到和看到的卻是在炒文物、炒藝術品,甚至到了置道德誠信于不顧,不擇手段炒高價格的地步,以致人們把收藏與股票等同看待。
由此看來,當明式家具的經濟地位飆升以后,其藝術地位與經濟地位仍不成正比,“荒唐悖謬的”不只是“理論”,還有市場。
美育補課之難,全說成是因為“金錢標準”這只手,怕是也不盡客觀。
有人說:“國畫”、“油畫”、“雕塑”是高雅藝術,而“工藝美術”長期附麗于所謂高雅美術之“化外”。……工藝美術的教育及其功能,則先后淪為宣傳的、技術的、平庸的、低端的行業。這種上百年來形成的觀念,就像一座象牙塔,一旦進入了,就越來越不關心外面的事情,而津津樂道于“純繪畫”、“純藝術”,無暇光顧其他。“人生日常生活中所需要的藝術”則被關在高雅藝術的大門之外,以致沒有多少話語權。
在現代的日常生活中,可以沒有一般人認為的傳統意義上的國畫、油畫、雕塑,但是不能沒有家具、燈具、廚具。其潛移默化的審美作用,決定了人們的審美情趣。如果說在古代,書法是美育的基礎,那么在現代,“人生日常生活中所需要的藝術”就是美育的氛圍。江南之老幼婦孺,幾乎人人利索得體,因為那些水鄉村鎮的房屋街道、日常用具所映射的文化精神影響著他們的審美情趣,所以明式黃花梨家具,出自江南核心地帶的“蘇作”,就不足為奇了。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人生日常生活中所需要的藝術”沒有話語權、難進藝術殿堂,自然也就難得提高,其美育、美化兩大作用,很難有上佳的發揮。
當我們的“人生日常生活所需要的藝術”還在高雅藝術的門口徘徊的時候,歐美的時尚與設計卻在不斷地影響、引導著所謂高雅藝術,或者說是在互相滲透,彼此分界越來越不清楚。在中國,時尚與設計以及相應的科學技術,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出現在我們的生活里。或許是來得太突然、太快,讓人措手不及,加上多有“舶來”面目,又與“商業”合流,不僅依然難入“主流”法眼,也與當今本國大眾的習慣、生活尚有不小距離。
由此我又想到王世襄先生,他特別注意發現中國“人生日常生活所需要的藝術”,把明式家具、葫蘆、鴿哨、竹刻、漆器之美提煉、推廣、發展,把這些離我們漸漸遠去的美妙,把這些我們記憶中具有生命溫度的大小物件,不僅帶進了藝術殿堂,也重新帶入到現實生活中。王先生與家青“合謀”的新制“明韻”家具,就是成功的實踐。
王世襄先生的收集、研究、發現、發展,是不是可以給今天的藝術家一些啟發、一些靈感呢?
(《和王世襄先生在一起的日子》,田家青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二零一四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