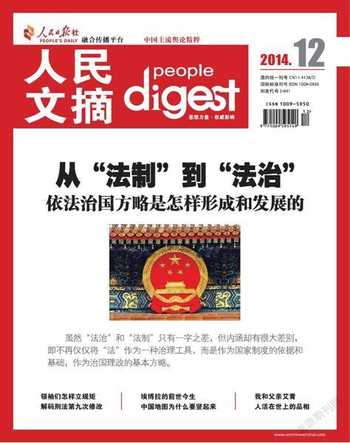雍正山西治腐
李冉


民間流行著這樣一句話,“當官不為民做主,不如回家種紅薯”。然而,現實中不為民做主的官員卻不在少數。近年來,山西頻繁爆發官場地震,大批官員落馬。這些落馬官員不但不為民做主,反而利用手中的職權牟取私利。
由今追古,山西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興盛的商業一直備受政府重視。尤其到了明清,山西官員已經占據朝中多數席位,而山西也因此屢現巨貪,成為反腐焦點。
京師大賈數晉人
太原門戶危都城
明代中后期,山西社會經濟便已有了極大的發展,商業興盛。而明朝“開中制”政策的實施,也為晉商的發展提供了契機。山西礦產資源豐富,手工業和加工制造業當時已初具規模,這又為晉商的發展提供了物質基礎,使得晉商逐步走向輝煌。晉南一帶地窄人稠,外出經商成為人們的謀生手段,晉中商人當時已遍及全國各地,當時在北京便有“京師大賈數晉人”的說法,而在《廣志繹》曾有這樣的記載“平陽、澤、潞,豪商大賈甲天下,非數十萬不稱富”,可見晉商之富。
到了清代,晉商已成為國內最有實力的商幫。這一時期,晉商雄踞中華,飲譽歐亞,在取得輝煌業績的同時,為山西帶來了巨大的財富,也為腐敗提供了標的物。
山西自古便是兵家必爭之地,特別是北京成為都城后,太原便成為京師的門戶,直接關系著京師的安危。政府向山西投入巨大的人力和物力,以確保山西的穩定,可在軍餉方面卻發生了五花八門的腐敗現象,吃空餉、冒濫軍功成為軍隊中的常見現象。
中央晉籍官員多
地方盤根錯節廣
由于深受“學而優則仕”的影響,許多發達起來的山西商人讓自己的孩子讀書應試,于是許多商人子弟走上了入仕做官之路。例如,隆萬年間的總督宣大、山西等處軍務兼理糧餉的王崇古,萬歷時的首輔大臣張四維就是其中的典型,王家和張家都是大鹽商。
與此同時,一批熟悉地理的山西籍文臣武將迅速崛起。僅明代中后期的晉籍官員中,身為宰輔者便有5人,官至六部尚書、侍郎、都御史、通政使、總督、巡撫、總兵的高官則多達30人。而這僅僅是在中央,地方的官員尚未計算在內,由此可見晉籍官員在政府中的比重之大。
到了清代,晉籍官員在政府中的比重較其他地區有了更加明顯的優勢。而且清代高級官員,尤其是一二品的高官,一般都兼有商人、地主、高利貸者等多重身份,這使他們的社會關系變得格外復雜,盤根錯節,牽一發而動全身。所以許多高官既是政策的執行者,同時又以手中的權力牟取財富。
此外,在山西任職的官員之間的關系往往也是千絲萬縷。如康熙朝噶禮貪污案中,噶禮就任山西巡撫時,與太原知府趙風詔及地方官員勾結,全然不顧民生,大肆貪污搜刮,相互勾結包庇,牽連官員人數甚廣,最終查處的涉案官員多達200余人。涉及范圍之廣、人數之多令人咋舌。而且,官員腐敗形式多樣:貪污受賄、買官鬻爵、橫暴豪奪、敲詐勒索、經商牟利、瀆職失職、盤剝百姓等。貪官們成為利益群體,官官相庇,腐敗呈現出集團性特點,使腐敗之風迅速蔓延。
推行“火耗歸公”
山西作為起點
雍正帝登基后,一改康熙帝在位時對官場“潛規則”的縱容,推行了一系列的反腐措施。
就反腐方面,雍正帝以山西為起點推行“火耗歸公”與“養廉銀”。由于地方官在征收錢稅時,會以耗損為由,多征錢銀,稱為火耗或耗羨,但耗羨的范圍大于火耗,耗羨還包含雀鼠耗等。通常,地方官征納運到京城的谷物,由于路途遙遠,交通不便,被雀鼠偷食損耗,稱為雀鼠耗。此項政策在漢代便有,而在雍正二年(1724年),雍正帝正式實施耗羨歸公,最早在山西推行,二年七月,正式推廣至全國。并且明確規定了耗羨征收的比率標準,據孫嘉涂在《辦理耗羨疏》中對耗羨征收率的記述,耗羨征收率被統一定為一成。雖然不知當時的耗羨征收率是否如孫嘉涂所說只有一成之數,但可以明確的是耗羨征收率是統一規范。將“耗羨”附加稅改為法定正稅,以此打擊貪腐,而首當其沖的便是山西。
與此同時,由于清初承明朝舊制,官至極品的俸銀也不過180兩、祿米180斛,而七品知縣年俸僅45兩。這使州縣官員不能借以維持生活,而“火耗”成為正稅之外無定例可循的附加稅,其實質上是默許州縣官在收稅時加征銀兩,以補給俸祿的不足。雍正皇帝在實施“火耗歸公”后便推行了“養廉銀”政策。“養廉銀”顧名思義,給官員以高薪,來培養鼓勵官員廉潔習性,避免或減少貪污發生,因此取名為“養廉”。
最初湖廣總督楊宗仁上奏雍正帝,提出了火耗提解藩庫的建議,正合雍正帝的心意。雍正帝對此的批諭是:“所言全是,一無瑕疵,勉之。”“養廉銀”出現雛形。隨即在雍正元年四月(1723年),雍正帝命曾任戶部主事的諾眠任山西巡撫。而諾眠五月到任后,上書雍正帝希望將山西省一年的火耗銀兩,提取存入司庫,并且留二十萬兩,補貼財政虧空,剩下的分給官員為養廉的費用,此建議得到了雍正帝的贊賞。“養廉銀”便由此推廣。由于“養廉銀”來自地方火耗或稅賦,因此視各地富庶與否,“養廉銀”數額均有不同,而一般來說,“養廉銀”通常為薪水的10倍到100倍。清政府希望以此打擊貪腐問題。
一系列反腐手段對山西的貪腐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但是,由于清代的法律、制度、政策存在系統性漏洞,使之在運行中出現了一系列問題,雍正的高薪養廉沒有也不可能徹底解決山西乃至全國的貪腐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