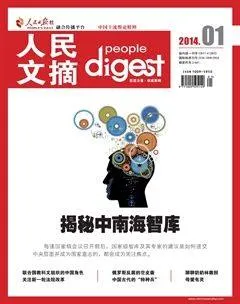關注新一輪法院改革
王全寶

司法改革再出發
在十八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建設法治中國成為關鍵詞之一。這份改革的綱領性文件指出,建設法治中國必須深化司法體制改革,加快建設公正、高效、權威的社會主義司法制度,維護人民權益,維護憲法、法律權威,深化行政執法體制改革,確保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檢察權,健全司法權力運行機制,完善人權司法保障制度。
由此可見,司法體制改革將是下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內容之一。
司法是社會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線。司法體制改革的方向是,讓其回歸到它本來的邏輯起點,即解決糾紛,在糾紛的解決過程中實現司法公正。
十八屆三中全會《公報》中提到,“建設法治中國,必須深化司法體制改革,確保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檢察權,健全司法權力運行機制,完善人權司法保障制度。”據了解,在十八屆三中全會召開之前,新一輪法院改革已經做好鋪墊,蓄勢待發。其改革脈絡業已逐漸清晰,以司法公開為抓手,輔以“去行政化”和“去地方化”的改革輪廓逐漸呈現。
2013年10月中旬,最高法院下發通知,要求上海、江蘇、浙江、廣東、陜西5省市部分法院進行深化司法公開和審判權運行機制改革的試點工作。據知情人士透露,試點改革方案將主要圍繞法院“去行政化”和“去地方化”兩大方面展開。而更有突破性的改革,是允許一些試點法院探索推行法院“省以下垂直管理”。
“但方案也強調,要求試點地區改革要漸進式,防止冒進。”上述知情人說。
規范審判權
據悉,在試點地區即將推行的審判權運行機制改革,將在四級法院職能定位、審判組織以及審委會方面有所動作。
長久以來,法院內部行政化問題廣受詬病,由此帶來的人情案、關系案、腐敗案層出不窮。在司法實踐中,人民法院審判組織存在合議庭“合而不議”問題,審委會制度存在“審者不判、判者不審”問題,以及下級法院向上級法院請示制度存在弊病等情形,嚴重影響了司法公正。因此,深化審判權內部運行機制改革,成為新一輪司法改革的重要內容之一。
在1999年之前,審判權是以一種高度行政化的模式運行的,當時法學界對審批制、請示制、審判委員會制等“泛行政化”的司法機制提出了諸多批評。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出臺了《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綱要》,明確提出了司法改革的目標是“還權于合議庭,充分發揮合議庭的作用,逐步取消院長、庭長未經審判程序個人決定案件的做法”。
上述“一五綱要”實施后,合議庭審案的自主性得到發揮,但實踐中法官的權力得不到有效管理和制約,裁判不公正、案件審理不透明、腐敗案件屢屢發生。
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發布了《人民法院第二個五年改革綱要》,要求院長、庭長參加合議庭審理案件,以提高審判質量和效率。但這一決定的消極影響,是人民法院的院長、庭長等審判管理者有時會以行政管理權力介了案件裁定過程和結果,致使法官的獨立裁量權遭到削弱。
此外,“二五綱要”明確要求“改革下級人民法院就法律適用疑難問題向上級人民法院請示的做法”,但由于行政化運行機制已經根深蒂固,最終導致“二五綱要”中,“去行政化”這一目標沒有實現。
2009年,“三五綱要”發布,對于之前要求“逐步取消個案請示”的改革目標,“三五綱要”卻表述為要求“規范下級法院向上級法院的請示報告制度”。在這個文件里,用“規范”替代了“取消”。
由此,經歷三個五年綱要,法院“泛行政化”問題始終沒有徹底解決。在新一輪司法改革中,解決這個問題無疑成為重中之重。
2013年10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關于切實踐行司法為民大力加強公正司法不斷提高司法公信力的若干意見》,要求貫徹人民法院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的憲法原則,完善合議庭的議事方式及合議庭成員的職權與責任。該文件突出法官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同時要求深化院長、庭長審判管理職責改革,加強對院長、庭長行使審判管理權的約束和監督,防止審判管理權的濫用。
財權事權改革
審判權運行機制改革,既涉及到審判機關內部制度的改革,亦涉及到審判機關與其他國家權力機構的協調。司法機構的財政經費來源以及人事任免問題,是其中的核心內容。
據知情人士透露,在有些審判權運行機制改革的試點地區,將探索推行“去地方化”。“其大方向是省級直管,即人、財、物由省級法院統一管理,相當于國稅與地稅之間的關系。不過,‘去地方化’問題涉及太多部門的利益,所以現在只是內部探索性改革。此外,還要看三中全會的具體指導精神是什么樣的。”這位知情人士說。
司法實踐中存在著嚴重的司法“地方化”傾向,其突出表現是司法機關工作人員管理的“地方化”和司法財政管理的“地方化”。人事權以及司法經費體制問題一直被理論界詬病。普遍認為,司法機關人事權由地方掌控,財政依賴于地方,極易形成司法“地方化”,獨立行使職權時也極易受地方控制。
2002年,中共十六大報告中就曾提出,改革司法機關的工作機制和人財物管理體制,逐步實現司法審判和檢察同司法行政事務相分離。兩年后,人民法院司法改革的內容之一,就是探索建立人民法院的業務經費由國家財政統一保障、分別列入中央財政和省級財政的體制,但此項改革進展緩慢。
2009年,財政部下發了文件,將政法經費劃分為人員經費、公用經費、基礎設施建設經費和業務裝備經費四大類。規定前三者由同級財政負擔,而業務經費和業務裝備經費則由中央、省級和同級財政分區域按責任承擔。
“這一政策沒能得到較好執行,也使得它的效果打了折扣。”北京理工大學法學院教授徐昕評價說。
據前不久參與司法改革座談會的專家透露,主導司法改革的有關部門設想,“兩高”經費以及高級法院和省級檢察院的經費由中央保障,省以下的法院和檢察院則由省一級負責,中央在轉移支付方面加大力度。
對此,清華大學教授張衛平認為,這就意味著,需要在省一級專門為司法設立一個財政的盤子。但是在這方面阻力比較大,因為各個地方經濟發展是不平衡的。
除了經費束縛之外,法院在人事、事權上也受制于同級黨委、人大、政府,這也被視為導致司法“地方化”的另一個因素,這一觀點在學界和實務界已成共識。
如果說經費改革緩慢,那么,人事改革則更為復雜。不僅受到地方阻礙,更受制于現有法律制度的牽絆。
比如,實行省以下法院垂直管理,將地方法院的人事權收歸省一級統管,則要突破《憲法》和有關組織法的現有規定。根據《憲法》規定,各級法院院長由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產生;此外,《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組織法》以及兩院組織法也明確授權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對法官有任免權。如此一來,人事權收歸地方管理的可能性將更為渺茫。
另據知情人士透露,新一輪司法改革,在解決人事的問題上,采取了變通策略——上收提名管理,“比如提到省級法院、省級檢察院,由省級院統一管理,統一向所在地的人大來提請、任免,這樣干部的提名權實際上就上收了,不提名肯定任命不了,這樣就解決了人的‘地方化’問題。”
該知情人士還表示,解決人事“地方化”的問題,以提名權代替任免權的變通方式改革可能阻力相對會較小,但這還需組織等相關部門達成一致意見,至于最后能否通過,目前不得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