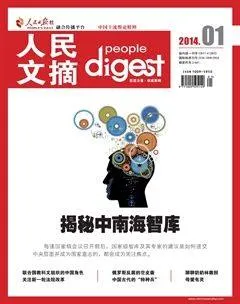德國司機在北京
焦東雨

德國人拓筆找了位中國太太子娟,結婚多年,兩人從來沒為感情問題吵過架,倒是交通問題差點兒讓他們離了婚。
原諒你,
但這是最后一次
“你的做法足以讓我因為鄙視而離開你。”拓筆憤怒地沖著子娟大聲說。那次“離婚風波”距離現在已經8年了,子娟偶爾還會提起,并笑著問丈夫:“你因為我不遵守交通規則要跟我離婚,為什么到現在還沒離?”
子娟有中國駕照,但在德國,中國的駕照不被認可,她想開車,必須考取德國駕照。這讓子娟很生氣,一天早上,她偷偷開車出門購物。拓筆知道后,氣憤地跟她大吵了一架。作為地道的德國人,拓筆不但自己遵守交通規則,也把這一點當作評判一個人品質的標準之一。那次風波的最后,拓筆對妻子說:“我原諒你了,但這是最后一次。”
2003年,拓筆第一次隨子娟來到中國,在2007年決定定居中國以前,從事藝術工作的拓筆對這個古老的國家充滿了仰慕之情。2008年,拓筆領取了中國駕照。按照規定,他參加了交規考試,并輕易地通過了考試,他發現,其實兩國的交規沒有本質區別。可當他開車上路后才發現,區別不在紙上,而在路上。
最危險的駕駛員
在北京5年,拓筆充分領略了中國式駕車風格。
一次在中關村,拓筆正要從右車道并到左車道去,一輛車突然從自行車道上殺出來,試圖搶在他之前開到左車道去。拓筆的第一反應就是剎車,然后摁喇叭。對方則下車來到拓筆的車門前,大吼著拉開了他的車門。拓筆極為惱怒,從那以后,每次開車,他都會把車門鎖上。
很多有斑馬線卻沒有紅綠燈的路口,有行人通過,拓筆都會停車,禮讓行人——德國有一條基本規則,公共交通的參與者永遠要讓著弱勢的一方。中國的現實規則卻是要保證交通順暢,不能耽誤別人時間。于是,每次禮讓行人時,總有很多司機在拓筆后面不停地摁喇叭。
不久后的一次經歷則告訴拓筆,什么叫車比車貴。那次是別的車違章,拓筆摁喇叭以示不滿。對方搖下車窗沖他大喊:“你一破‘飛度’,有什么好摁的!”拓筆不解,子娟解釋:“他是說你的車不值錢,輪不到你摁喇叭。”拓筆反問:“那我什么時候可以摁?”子娟啞口無言。
從2008年到2010年,夫妻倆沒少吵架。“爭吵時,我覺得他一點人情味兒都沒有。我說‘這事兒你改變不了,你不可能成為全中國的駕校老師’。他就會說,‘我說的是原則,你為什么不承認這個原則’?”拓筆這樣看待兩人的爭吵:“表面上看,我們是在吵別人如何開車的事,吵北京的交通,但本質上我們是在為各自的認識而吵。”
有好幾次,拓筆撂出了氣話,要在中國開一所駕校,教中國人重新學駕駛。子娟給他潑冷水:“你是客人,不可能改變這個國家,只能去適應。”其實,子娟是理解丈夫的:“他想不通,對他那么重要的事情,對我怎么那么不重要。”
在這種憤怒的情緒下,終于有一次發生了剮蹭事故。那一次,他們遇到堵車。按照交規,車輛應該在路面劃定的車道上行駛。但很多車輛往往哪兒有空往哪兒走,甚至形成一條違規的車流。拓筆堅持要按車道走,但剛把車從斜行的車流中掰出來,后面沖過來的一輛摩托車就剮上了他們的車。當所有人都按照另一套不成文的規矩開車時,那個按照規則開車的人,反而成了最危險的駕駛員。
規矩與習慣
兩年前,拓筆在小區門口拍了一張照片,那是交警支隊的警示牌:上周我區因交通事故死亡3人,截止到8月11日,全區已死亡122人……每次子娟晚上出去,拓筆都要求她在胳膊上纏上熒光帶,“為了自己的安全,也不給別人添麻煩。”
對比中德兩國的汽車文化,拓筆和子娟覺得人們不懂車的原因,一是駕照拿得太容易了;二是中國提供的服務過剩了,加油、修車都有人打理,導致人們越來越懶,很多人天天開車,卻不懂汽車。在德國,就沒有汽車保養之說,有駕照就必須得會換機油,加油是自助的,換機油也是自助的。
拓筆介紹了德國的“拉鏈規則”,如果有條路因為事故成了單車道,兩個車道的車會一左一右、一前一后,一輛一輛先后并道,就像拉鏈一樣,實現有序且高效的通行。但實際經驗告訴他,此法在目前的中國不可行,因為相互禮讓、提高安全意識的整體社會環境還沒有形成。
他們有些外國朋友,在北京開車比中國人還不守規矩——他們在陌生國度遭遇文化沖突,受到了傷害,然后就會沒底線地放縱,這更危險。
拓筆偶爾回德國。一次,開車右轉時,他很自然地沒有停頓便打了方向盤,嚇住了一個要踏上人行道的人。一個金發女郎沖他甩出一句:“混蛋!”在德國,這常常是無能的代名詞。拓筆這才意識到,按照德國的開車習慣,即使是右轉,看到要過馬路的行人,也應該主動停下來,并舉手示意“您先請”。
這一刻,拓筆百感交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