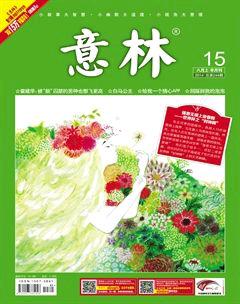紐約黑與歐洲白
Daisy Jing
紐約客將永遠穿黑色,直到他們找到更深的顏色。
初夏午后,在樓下露臺樹蔭底下喝茶發呆,突然想起小時候的一個場景:梅雨季,我用烏賊中間抽出的白色弧形骨棒反復擦拭剛洗凈的白球鞋,眼看著鞋子漸漸幾近熠熠閃光,白得透亮。
身邊是梔子和茉莉的清香,有時還有繡球和芍藥,都是我喜歡的白色香花。
成年后,漸漸穿深色衣物居多。搬到紐約后,仿佛墮入黑色海洋。多數紐約女子的衣櫥里有超過兩件以上的黑外套、黑大衣、小黑裙,更不必提黑鞋子和黑手袋。男士也多數穿深色。華爾街更是權力西服(power suit)的天下。下雨天,多半也是人手一把黑色雨傘。
當然細看之下,也不全是黑色,還有不少低調細膩的海軍藍。紐約客十分懂得在質感和層次上作微妙搭配,并不刻板單調。
有人奇怪,為何作為時尚之都的紐約,黑色永不落伍,一季一季,最暢銷的永遠是黑色?在這個全世界最為多元的大都會里,黑色將其中的各色人等聯系起來,又并不湮沒他們的個性。在黑色面前,眾生平等,和而不同。
《紐約》雜志有個老牌欄目“21 Questions”,向各行各業、形形色色的紐約名人提問。其中有一個問題:“是什么讓人成為紐約客? ”讓我印象最深的回答是:“紐約客將永遠穿黑色,直到他們找到更深的顏色。”
有好事者追溯,自荷蘭人在紐約建市,直到18世紀,布料都是由英國進口,且多為暗色面料。一方面,當時城市尚在建,街上無人行道,塵土飛揚,人與牲畜共享通路;另一方面,雖然紐約當地開始設立織染工坊,但染料成本高昂,交易也受各種繁文縟節約束,黑色可以長久持續,不失為務實的選擇。
這讓我想起在日光灼灼的大漠、非洲高原和潮濕炎熱的東南亞,外來的殖民者,尤其白人,總是穿一身漿洗發亮的白衣。即使汗流如雨,男士們還是鎮定自若地身穿一絲不茍、無懈可擊的三件套白色西服。
除了便于散熱之外,白色異常脆弱金貴,需要隨時有人濯洗呵護的特質,也是彰顯權勢地位的一種方式吧。
電影《走出非洲》中,凱倫的衣服多數是深淺不一的白色和土地色系:從干練颯爽的馬褲長靴狩獵裝,白襯衣加領帶,米色長裙的莊園女主人打扮,到隨著留聲機中音樂曼舞時的鑲蕾絲白色裙子。最令人難忘的,自然是在溪澗邊,她披著白色大毛巾,頭后仰,愛人丹尼斯為她洗頭,從白色瓦罐中倒下清水,一面還背著柯爾律治的詩句。此時日光明媚,空氣清透,兩人相悅的神情如此浪漫動人。
我的白襯衣情結,則始于一幀時裝設計師格蕾夫人的黑白舊照。照片中的她側身而坐,柔順如水的白色尖領絲襯衣,深色絲長裙,頭發藏在深色頭巾里,神情若有所思,溫婉沉靜。
幾年來,我輾轉穿過好多種白襯衣,質地廓型上的不同,也帶來感官上的不同感受。沒有什么比白襯衣更美,但也更難找到完美的了——每一個有微微完美主義傾向的人都會同意我的吧。
黑與白,仿佛夜與晝,又如月圓月缺,合起來才是完整完滿。剛工作的時候,我不無奢侈地買下過一條白色雪紡裙子。那條裙子,只穿過一回,見過一個人。有些衣服,像落櫻一樣,只存于一季。我始終覺得,年歲漸長,看世情自當越發分明,黑色也許是在人群中保護我們的小小盔甲,而內核,我總是想要保留純粹的白色光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