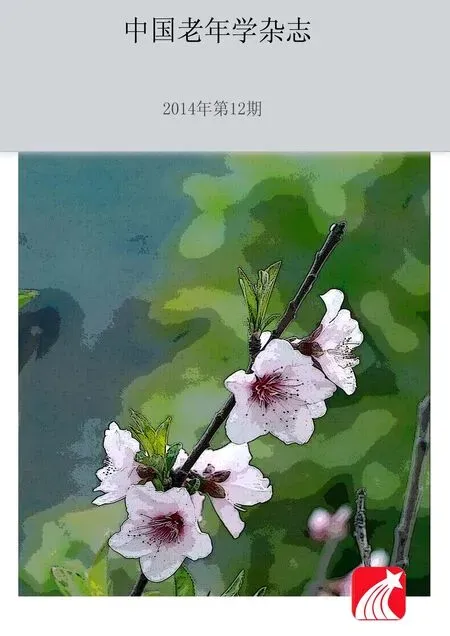高齡缺血性腦卒中患者危險因素及臨床預后
趙久晗 商秀麗
(中國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神經內科,遼寧 沈陽 110001)
由于高齡缺血性腦卒中(IS)患者常常合并其他疾病、較少使用溶栓藥物,藥物代謝能力下降及腦對缺血應激反應能力差等問題,因此高齡患者IS的預防及治療面臨著較多的問題〔1〕。本研究旨在發現85歲以上IS患者與年齡相對低的患者之間危險因素、病因、臨床表現、神經缺損嚴重度、主要并發癥、功能殘疾程度及死亡率的不同。
1 對象與方法
1.1研究對象 回顧性收集我院神經內科2006年8月至2011年3月首次發生IS的患者,分為426例85歲以上研究組及418例65~84歲對照組。研究組平均(88.2±5.3)歲,男228例;對照組平均(72.8±7.8)歲,男203例。兩組間性別無明顯差異。所有患者住院期間行頭CT,心電圖(ECG),頸動脈超聲,血常規,肝腎功能,離子及血脂分析檢查。
1.2方法 收集包括人口統計數據,腦卒中類型,血管風險因素包括高血壓、糖尿病、高脂血癥、房顫(AF)、肥胖、大動脈粥樣硬化及吸煙等資料。臨床評估主要通過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腦卒中量表(NIHSS)評分及更年期生活質量評分量表(mRS)評分〔2〕,由有經驗的臨床神經科醫師進行。mRS評分被用來評估患者殘疾程度。腦卒中分型主要根據TOAST分型標準〔3〕。對血管風險因素,臨床表現,住院時間,并發癥及功能恢復情況進行比較。
1.3相關定義 ①高血壓:使用抗高血壓藥物(或)收縮壓≥140 mmHg或舒張壓≥90 mmHg;②糖尿病:使用口服降糖藥物,胰島素或糖化血紅蛋白>7.0%。③高脂血癥:使用降脂藥物或血清膽固醇水平>220 mg/dl。④AF:既往心血管科醫師診斷或入院后行心電圖檢查發現。⑤肥胖:體重指數(BMI)≥30 kg/m2。⑥大動脈粥樣硬化:既往心血管科醫師診斷或入院后行彩超檢查發現。
1.4統計學分析 采用SPSS13.0統計軟件包進行t檢驗和χ2檢驗。
2 結 果
研究組中AF比率比對照組明顯升高(P=0.002)。研究組34例患者(8.0%)和對照組32例患者(7.5%)應用了華法林。大動脈粥樣硬化在研究組更常見(P=0.002)。糖尿病、吸煙、高血壓、肥胖及高脂血癥的發生率在對照組中更高(P<0.01)。在腦卒中分型上心源性栓塞在研究組常見,而大動脈粥樣硬化型及小動脈閉塞型在對照組更常見。入院時NIHSS評分對照組明顯比研究組高(P=0.001),但出院3個月后mRS評分(殘疾程度)研究組更高(P=0.001)。住院期間研究組中沒有患者行溶栓治療,對照組中有1例患者進行了溶栓治療。住院期間在肺炎、尿路感染、深靜脈血栓或肺栓塞的發生上兩組沒有明顯的不同。研究組住院時間明顯更長(P=0.016)。見表1~3。

表1 兩組患者血管病危險因素比較〔n(%)〕

表2 兩組患者腦卒中亞型分布情況〔n(%)〕

表3 兩組患者臨床及康復情況〔n(%)〕
3 討 論
本研究發現,與其他風險因素相比AF是高齡患者唯一的血管風險因素。老年AF發生率的升高可能是因為一些傳導組織細胞的丟失及起搏功能的下降,從而導致竇房結功能不全及房室結的傳導異常〔1〕。本結果與Wolf等〔4〕的研究結果是一致的,研究中發現非瓣膜病引起的AF的發生率隨年齡平穩升高,從40歲1 000人中的0.2到80~89歲的1 000人的3.9。與AF相關的腦卒中的腦比例也平穩的升高,從60歲的6.7%到80~89歲的36.2%。而高血壓的影響隨年齡的升高而出現了下降。雖然,目前診斷AF很容易,但因為老年人藥代動力學下降,血漿白蛋白水平下降,引起血藥濃度的升高這些問題,在是否給予高齡患者華法林治療的問題上往往會出現爭議。目前研究證實,盡管應用華法林有潛在的嚴重出血的風險,但AF患者發生腦栓塞的風險超過出血〔1〕,而且這類患者的預后也往往不良〔5〕。Mant等〔6〕研究結果顯示75歲以上AF的老年人予以抗凝是安全和有效的。在這個研究中華法林抗凝與阿司匹林相比較可以減少50%的缺血事件,而顱外出血的概率是相似的。本研究也支持抗凝的重要性,認為在老年人中進行抗凝治療可以大大加重出血風險的想法是不正確的,年齡不應該成為不使用抗凝治療的條件。
本研究關于高齡患者糖尿病、高脂血癥和吸煙發生率低的結果與Lee 等〔7〕的研究結果是一致的。推測這個不同可能與兩代人的生活方式有關。盡管研究組在入院時具有好的臨床評分,但3個月后mRS評分更差。推測出現這個結果可能與研究組患者護理質量差有關,但在兩組間沒有發現明顯的不同;另一種推測認為與住院期間出現的并發癥有關,但兩者間也沒有明顯的不同;再之,認為是否與治療強度有關。本研究認為出現此結果可能是因為老年患者腦卒中前健康及功能狀態比較差,沒有進行入院前的mRS評分,這就構成了腦卒中后殘疾度的一個偏倚。另一個偏倚可能是兩組腦卒中亞型的不同。
綜上,高齡IS患者表現出不同的血管風險因素,臨床及康復過程。提示在高齡IS患者中要采取特殊的二級預防及治療康復過程。要重視AF的診斷,強調華法林的應用以阻止腦卒中的發生,不應過分考慮年齡的因素。
4 參考文獻
1Shuaib A,Hachinski VC.Mechanisms management of stroke in the elderly〔J〕.CMAJ,1991;145(5):433-43.
2Goldstein LB,Bertels C,Davis JN.Interrater reliability of the NIH Stroke Scale〔J〕.Arch Neurol,1989;46(6):660-2.
3Gordon DL,Bendixen BH,Adams Jr HP,etal.Interphysician agreement in the diagnosis of subtypes of acute ischemic stroke:implications for clinical trials.The TOAST Investigators〔J〕.Neurology,1993;43(5):1021-7.
4Wolf PA,Abbott RD,Kannel WB.Atrial fibrillation:a major contributor to stroke in the elderly.The Framingham Study〔J〕.Arch Intern Med,1987;147(9):1561-4.
5Candelise L,Pinardi G,Morabito A.Mortality in acute stroke with atrial fibrillation.The Italian Acute Stroke Study Group〔J〕.Stroke,1991;22(2):169-74.
6Mant J,Hobbs FD,Fletcher K,etal.Warfarin versus aspirin for stroke prevention in an elderly community population with atrial fibrillation the Birmingham Atrial Fibrillation Treatment of The Aged Study(BAFTA):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J〕.Lancet,2007;370(9586):493-503.
7Lee M,Huang WY,Weng HH,etal.First-ever ischemic stroke in very old Asians:clinical features,stroke subtypes,risk factors and outcome〔J〕.Eur Neurol,2007;58(1):4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