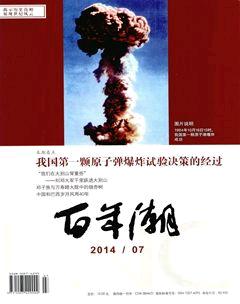上海工人造反派頭目王洪文
上海工人造反派代表無疑首推王洪文。王洪文是全國第一個被中央文革小組明確支持的跨行業全市性工人造反組織“上海革命工人造反總司令部”(簡稱“工總司”)的發起人和主要負責人。1966年王洪文正值而立之年,是國棉17廠的保衛科干事。
國棉17廠是上海最大的三家紡織廠之一,當時有8000多名職工。工廠前身是日本人經營的裕豐紗廠,1945年抗戰勝利后收歸國有,改為中國紡織建設公司第17棉紡織廠。1949年后改名國營第17棉紡織廠(簡稱“國棉17廠”),20世紀70年代又改名為上海第17棉紡織廠(簡稱“上棉17廠”)。工廠地處上海東北角的楊樹浦(也稱“楊浦”)工業區,是這個工業區引人矚目的大型國營企業。
王洪文1934年出生于東北吉林長春的一個貧農家庭。他曾經對人回憶過自己小時候家里的窮日子:“可苦啦!兩三歲那年生過一場大病——其實不是病,那是餓的呀!父親以為我死啦,就把我丟到了荒郊野外,后來摸摸好像還有點熱氣,又抱了回來。”他1950年入伍,1951年隨所在的第27軍80師作為中國人民志愿軍參加抗美援朝。在部隊先是當警衛員,后來在師部通信科當通信員(班長級)。履歷表上顯示他在志愿軍軍樂隊吹過小號。徐景賢曾問過王洪文,王洪文說是吹黑管。而據王洪文妻子崔根娣的回憶,王洪文還會拉手風琴,吹口琴。手風琴雖然拉得不是很專業,但能拉出曲調。1951年6月王洪文加入中國共產黨。1952年王洪文隨部隊調往江蘇省無錫市。1956年王洪文進入南京預備軍官訓練團。同年9月,他以副排級預備役少尉從部隊復員,分配進上棉17廠工作。王洪文從一個東北農村的青年,參軍、復員,成為中國最大城市上海的大廠工人,完成他身份轉換的重要幾步。
王洪文小時候家里條件差,只念過3個月私塾,不識幾個字。他后來對人回憶說:參軍后部隊組織學文化,起初他不愿學,情愿上山去打獵。在朝鮮時,有一次家里來了一封信,他請人給他念。旁邊的人說:他不肯學文化,不要幫他讀。“這句話很刺激我,這樣我就開始發奮學習,我托人從國內帶來一本詞典,就是這樣學習了文化”。進國棉17廠之后,他又堅持讀夜校,讀到初中。在夜校,他認識了同班的女工崔根娣,她后來成為他的妻子。據崔根娣以后回憶說,王洪文的語文特別好,以后又比她多讀了幾年夜校。
進廠后,王洪文最初在四紡車間當揩車工,不久調到二紡車間,成為技術含量較高的保全工,后來又擔任二紡車間的治保主任。雖然進入科層當上管理人員,但此時編制仍是工人。1960年3月,王洪文被借調到廠保衛科做民兵工作;7月,他被正式調往廠保衛科任保衛員,人事關系從工人編制轉為干部編制,成為工廠的科室人員。從工人轉為管理人員,編制從工人轉為干部,王洪文實現了又一次身份轉換。轉為干部編制,是對他的提拔,也顯示他受到信任。到“文革”前夕,王洪文的月工資是64元。
“文革”后,對王洪文“文革”前的經歷,有兩種評價。一種評價是正面的,都是朋友、同事的回憶:說王洪文很喜歡看書讀報,而且口袋里老裝著本艾思奇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有空就讀。這是當時毛澤東推薦給干部們看的書,工人中絕少有人閱讀這類形而上的書籍,可見王洪文“文革”前就對政治比較感興趣。王洪文的人緣也比較好,1958年二紡車間長日班黨支部改選,他得票較多。王洪文的同事更回憶說:“王洪文這個人過去表現不錯的,不能因為他是‘四人幫就把他的過去說得一無是處,這不符合事實。他以后的表現是以后的事。王洪文與其他人的關系也都不錯。”
另一種評價則比較負面:說他在朝鮮當通訊員時“貪生怕死,不愿在前線,一直鬧情緒,吵著要求調到后方軍樂隊”。在南京預備軍官訓練團時,“鬧著要復員”。說他1956年剛進廠時,“吵著要補助,還煽動四五個復員軍人一起鬧補助”。說他進工廠當揩車工時“吵著要當技術工,當上技術工后,又對師傅說自己不想吃技術飯而想吃政治飯”。說他那次“因改選得票最多,便想當脫產的黨支部書記。后來到廠保衛科,又想當科長”。說他在1960年國民經濟衰退時期說:“我東北老家沒有吃的,安徽餓死幾萬人。我們工人應該在廠里做工,怎么到崇明去圍墾。”說他因闌尾炎從崇明回上海動手術是“裝病”,說他講過:“‘天災,我看是人禍!”而且當“黨組織號召黨員分挑困難,節約糧食定量,他卻說:‘他媽的,叫老子餓著肚子干活,這是什么社會主義?什么政策?要把人都餓死了!”說他收聽短波,被人發現,自辯說“我聽聽臺灣在講什么”等等。又據一份資料顯示,1958年,王洪文被選為二紡長日班黨支部委員,但沒當上支部書記。他認為自己得票多可以當上脫產(即專職——筆者注)的支部書記,但上級決定由原來的支書連任,王洪文當不脫產的宣傳委員。“王洪文很惱火,經常拒不參加支委會,并事事與支書對立”。
后一種評價都是“文革”結束后對王洪文的揭發和批判,有著明顯的時代話語特征。但剝去話語的政治外殼,還是可以大致看出王洪文的性格脈絡:雖然是黨員、政工干部,但又不像當時一般黨員和政工干部那樣“聽話”,那樣“黨叫干啥就干啥”;他知道爭取自己的利益,有著自己的人生設計或目標;他關心政治,注意掌握各種信息,不但閱讀公開發行的報刊,而且收聽不被允許的海外信息;他敢說話,也比別人敢出頭。但是,王洪文畢竟是共產黨員,長期在共產黨嚴密的組織紀律下工作生活。上面所列舉的所有負面評價,即使在當時政治背景下,也不算太“出格”,那些話也充其量只能算是牢騷話。
不過,許多當年同事對王洪文有個共同感覺:想當官。當時和王洪文一個保衛科的同事馬驥,“文革”初期是與王洪文造反組織對立的保守派組織負責人。他認為王洪文平時為人不錯,隨和、講義氣,喜歡出頭為別人說公道話,在工人中有威信,“就是官癮太重”。而王洪文的妻子崔根娣,“文革”后對王洪文的評價,則說他“愛管閑事”。崔根娣的意思是說王洪文好打抱不平,好幫人調解糾紛、有公共意識。她說:
王洪文為人熱心,愛管閑事。里弄里有位80多歲的老人,與子女吵架想不開喝鹽鹵自殺,王洪文將老人的子女叫去狠狠批評了一頓。為這類事情他也得罪了一些人。“文革”起來,他越發起勁了,真是沒日沒夜了,好像廠里的事,市里的事,全都要他去操心似的。后來就鬧起了“安亭事件”,嚇得我時時刻刻提心吊膽,整夜整夜睡不著。我也勸過,可他那個牛脾氣,哪里肯聽啊,還罵我死落后。endprint
1966年6月12日這天,聶元梓大字報廣播后不久,廠醫務室旁的大字報欄貼出一張大字報,題為《剝開黨委畫皮看真相》,轟動全廠。這張大字報由王洪文起草并領頭簽名,后面還有6人簽名,其中5人都是保衛科干部。王洪文說:“聶元梓大字報是7個人,我們也來7個人”,這7人全部都是共產黨員。
國棉17廠黨委當時沒有正書記,由黨委副書記張鶴鳴主管工作,王洪文大字報就是針對他的。當時廠黨委規定“貼大字報要經過組織審閱”,這是廠里第一張未經審閱并針對廠部主要領導的大字報。“文革”結束后的1980年,王洪文在受審時,交代他寫這張大字報的原因:
我們認為廠黨委執行修正主義的干部路線。我當時在保衛科工作,有兩個人,應定為反革命,廠黨委未表態。我在第一張大字報《剝開黨委畫皮看真相》上,點了兩個人。黨委停止了我的工作,派人盯我的梢,我思想不通,就寫了第二張大字報,點了5個人,家庭出身不好。
第二張大字報貼出后,群眾不滿,說我罵廠黨委,是野心家,陰謀家,全廠寫了六千多張大字報。
寫第一張大字報后,廠黨委和我有對立情緒。有一天,我在屋里寫大字報,別人把門倒鎖上,黨委副書記來敲門,問有沒有人,我心里想,你們還派人監視我,我不吭聲。書記覺得屋里有人,叫了武裝部長帶十多人到保衛科搜查,我就火了,罵了黨委書記……
王洪文說的書記就是張鶴鳴。張鶴鳴是地下黨出身的上海本地工人干部,對上海社會環境和工廠的人事關系以及生產環節都比較熟悉。他處理事情也比較實際,不像有些干部那樣生硬和“革命”;在對管理人員的聘用上,他起用和信任有“歷史問題”的“留用人員”,即1949年共產黨執政前,工廠的科層管理人員和技術人員以及學有所長的專業人員。總之,張鶴鳴的“階級斗爭”之弦不那么緊繃。這是王洪文大字報上所說的黨委不抓階級斗爭的由來。
當年與王洪文一起造反,在他第一張大字報上簽名的7人之一唐文蘭,30多年后分析王洪文寫大字報的原因:
王洪文為什么要反張鶴鳴?這是因為當時廠黨委規定批判8個人,這8個人有的有政歷問題,有的在當時看是反動學術權威。但是廠黨委不許超出這個范圍批判別人。王洪文認為這是畫圈圈、定調子,所以就貼了張鶴鳴的大字報。另一個副廠長張元啟提出,對別的有問題的廠領導也可以貼大字報。我們當時也認為廠黨委領導自己也有很多問題,卻不允許揭發,揭發了就說你反黨,這樣做其實就是保護他們自己。所以同意王洪文的觀點。.
由此看來,王洪文造反,是因為與廠黨委在“文革”運動的批判對象上有不同意見,“文革”中這些不同意見被上升到階級斗爭高度的政治分歧。但實際上,如果再深入分析,我們還是可以看到這種“政治分歧”背后的人際關系因素。對于王洪文的行為,還有另一種解釋:
我們廠在“文革”中引起爭論的那兩個廠長張元啟和張鶴鳴,張元啟是部隊轉業干部,文化不高,但資格老,山東人。做起報告,一口山東話,上海工人聽不懂。他做報告,即使有時下面聽報告的工人走光,他也照念稿子,繼續做報告。而張鶴鳴是地下黨出身的上海本地工人干部,浙江寧波人,一口上海話。我覺得,比起張元啟,張鶴鳴與工人的關系更密切。二張有矛盾,我看主要原因在張元啟。當時他倆都是副廠長。張元啟想當正廠長,大概因為他資格更老些。張元啟“文革”前分管人事、教育和保衛,和王洪文關系很好。“文革”中他支持王洪文。(李遜1989年7月6日對馬驥的訪談)
兩個廠長有矛盾,張元啟分管保衛科,分管生產的張鶴鳴就從不去保衛科,以避嫌疑或矛盾。王洪文所以說張鶴鳴從1963年起,從沒到保衛科坐過哪怕半小時,這是不抓階級斗爭。可見,王洪文貼大字報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受兩位廠長矛盾的影響。分管保衛工作的張元啟,因為工作關系與保衛干部主洪文比較熟悉,而張元啟與另一個廠長張鶴鳴有矛盾,于是影響了王洪文。
王洪文6月12日就貼黨委大字報,這在上海工廠職工中是相當早的。王洪文大字報貼出不到一小時,國棉17廠的上級管理公司——棉紡公司的黨委書記立即趕到,召開廠黨委緊急會議,作三點指示:保衛科大字報是大毒草;1957年反右斗爭的形勢又來了;反到黨委頭上來了,不能稀里糊涂,這就是階級斗爭。廠黨委也找其他幾個大字報簽名者談話,追查誰是起草者。立即,上百張反擊王洪文的大字報貼出。這種階級斗爭過敏癥,是“文革”初期點燃群眾造反情緒的重要原因。國棉17廠群眾中最初的兩大派,也在這樣的批判和對立中形成。
6月20日,上海紡織工業管理局(紡織局)黨委派工作隊進駐國棉17廠。工作隊在全廠職工代表大會上批評張鶴鳴,肯定王洪文貼廠黨委大字報的行為。隨后,又連續召開各種會議,揭發批判張鶴鳴。但是,這個工作隊在國棉17廠沒待多長時間便被撤走,市委又派出150人左右的市委工作隊,于7月20日進駐國棉17廠。市委為什么要撤走第一個工作隊?應該是和劉少奇6月30日對毛澤東的那個建議有關,當時上海其他工廠也有召回之前派駐的“四清”工作隊,再改派文化革命工作隊的情況。
市委統一組織了一批工作隊,這批工作隊派得十分匆忙。以往派工作隊,總要先集訓幾天,學習有關文件和政策,再下工廠農村;這批工作隊連集訓和學習都沒有來得及,人員一配齊,馬上就下工廠。國棉17廠的工作隊是其中之一,陣容十分強大:隊長是上海市總工會副主任施惠珍,另外幾個副隊長,分別是黃浦區副區長張六吉、楊浦公安分局副局長趙戈,上海絲織一廠黨委書記焦鳳嶺,以及上海市總工會教育部部長余文光。
7月20日,新的工作隊進廠。第一天就召開全廠8000職工大會,隊長施惠珍做報告。據廠里后來整理的“文革”大事記說:
這個報告不強調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而強調“搜索一切牛鬼蛇神”,要全廠職工“到深山密林中尋老虎”。這個報告對前一階段王洪文等同志與舊黨委斗爭的革命行動只字不提,對張鶴鳴鎮壓革命群眾的反革命罪行只是輕描淡寫地提一句。endprint
市委對工廠如何開展“文革”心中無數,一切靠隊長們自己去摸索,能夠借鑒的只有“四清”模式:先發動群眾,待群眾揭發后,再決定運動對象。在工作隊進廠報告后的10天之內:
全廠共貼出2800多張大字報,屬中層以上干部的占14%,而貼群眾的卻占70%以上。把矛頭指向群眾。
到1966年9月底,全廠共排出四類對象114個,其中廠級干部只有1個,而一般干部和工人群眾卻有98個,其中已整理成書面的,也-大多是工人群眾。在4個月中,全廠150多個車間級以上干部進行批斗的只有4人。
(《控訴以施惠珍為首的市委工作隊殘酷鎮壓國棉十七廠的滔天罪行》,上海市國棉十七廠工作隊“保衛毛主席革命路線”戰斗組1967年1月,上海市國棉十七廠“永遠忠于毛澤東思想”戰斗隊1967年2月翻印)
對于王洪文所反對的副廠長張鶴鳴,施惠珍在報告中說是“壓制大字報的嚴重事件”,但沒有提及前一階段王洪文他們對張鶴鳴的揭發。工作隊為什么沒有對王洪文他們前一階段的行為表態?據說是因為他們不知道前面發生過的事情。因為工作隊派得非常匆忙,兩個工作隊之間沒有交接,他們進廠前不知道王洪文曾經貼過張鶴鳴的大字報,甚至不知道“王洪文”這個名字。(李遜、金光耀、金大陸2009年12月20日對1966年7月市委派駐國棉17廠工作隊隊長施惠珍及工作隊秘書王曾元的訪談)進廠后,才逐漸了解國棉17廠的情況。工作隊認為兩個廠長的糾葛是“領導核心爭權奪利破壞團結的問題”。對于這第二個工作隊,王洪文1980年的交代中說:
工作隊由市總工會副主任任隊長,一進廠就支持我,正式宣布要我列席黨委會。起初,我和他們合作,后來,由于他們和黨委觀點一致,我又和工作隊對立起來。
工作隊進廠后,也從一些工人和干部的反映中,了解到王洪文的一些動向。但王洪文此時沒有公開反對工作隊,所以工作隊采取的策略是,“不受王洪文影響,不受干擾,你打你的,我干我的,不激化矛盾,用事實最后說話”。
工作隊進駐后,另一派繼續貼張元啟的大字報,王洪文認為這是受工作隊指使。他反對批判張元啟,認為他“雖有缺點,但抓階級斗爭是狠的”。
毛澤東接見紅衛兵后,作為民兵連長的王洪文馬上與其他負責民兵工作的人商量,想將廠里的民兵也組織成紅衛兵。工作隊不希望王洪文掌握紅衛兵,便想出了個辦法:既然紅衛兵是學校青少年的組織,那么工廠的紅衛兵也應是青年工人的組織。他們因此將紅衛兵年齡規定在30歲以下,因為按當時對基干民兵的年齡要求,上限是30歲。王洪文當時32歲,被出局。8月19日,國棉17廠按“十六條”要求,籌備成立廠文化革命委員會。造反派們提名王洪文為候選人,但王洪文所在的廠部科室兩種觀點爭執激烈。廠部科室不但包括廠保衛科,也包括其他生產、技術、人事和黨政部,廠部科室一派支持王洪文,一派堅決反對王洪文,結果廠部科室的文化革命委員會始終沒有成立。而要當選為廠文化革命委員會代表,必須是自己所在部門的文化革命委員會代表,王洪文于是沒有當上廠文化革命委員會主任。王洪文和造反派們認為這是工作隊干擾的結果,工作隊則認為這是群眾選舉的結果。
北京紅衛兵沖擊上海市委時,國棉17廠工作隊也接到電話,讓緊急抽調幾百名工人趕往市委大樓,與其他工廠的工人們一起組成糾察隊,保衛市委大樓。工作隊的秘書組副組長找擔任民兵連長的王洪文談話,讓他帶領民兵去市委門前。工作隊此舉顯示,當時他們沒有將王洪文看作異己。王洪文帶著工人到舊市委門口后,“發現卻是圍攻紅衛兵,馬上叫大家撤走”。
10月7日,毛澤東“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指示剛由《紅旗》雜志的社論提出,王洪文與唐文蘭等6個廠部科室人員便貼出大字報《就目前形勢談看法》,公開打出了反對工作隊的旗幟,對全廠震動很大。不過,工作隊沒有正面組織對王洪文的反擊:
我們工作隊與王洪文的矛盾,不是因壓制王洪文而起,而是因為對二張的態度而起。因為我們根本沒有壓制過王洪文,我們只是對王洪文一定要打倒張鶴鳴的做法既不支持,也沒有表態。工作隊那時對于張鶴鳴,認為還要再看大家的揭發,不能馬上表態。不過工作隊也沒有批評過王洪文,我們沒點過保衛科的名,也沒點過王洪文的名,我們沒說過任何一句針對王洪文的話,沒有做過任何回應。
(李遜、金光耀、金大陸200g年12月20日對1966年7月市委派駐國棉十七廠工作隊隊長施惠珍及工作隊秘書王曾元的訪談)
但是,王洪文他們還是感到了來自工作隊的壓力。工作隊通過廠文化革命委員會組織了4次全廠大辯論,辯論的中心是國棉17廠的“文革”對象和方向,實際是對著王洪文他們的。10月10日的辯論中,王洪文被圍住,正在此時,國棉17廠技校學生廖祖康,帶來一幫學生紅衛兵為王洪文解了圍。晚上,反工作隊的工人們在王洪文家聚會,王洪文提出:“我們現在只有一條路:到北京去向黨中央告狀。”當即,決定派15個人赴京。第二天,又在唐文蘭家里開會,成立了“誓死將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戰斗隊”(簡稱“誓死”),成員共30多人,王洪文被推為負責人。10月12日下午,王洪文等15人赴京告狀,他們離開上海的第二天早上,國棉17廠大道旁貼出了他們15人署名的《給全廠革命同志的一封公開信》:
一小撮資產階級當權派和頑固保皇派如此欺侮我們,難道我們就沒有說理的地方嗎?有!黨中央和毛主席就是我們有力的靠山。偉大領袖毛主席是一定會支持我們的,為此,我們暫時分別幾天,到他老人家那里去吸取更大的智慧和力量。
他們去北京的火車票錢是大家共同湊的。1966年的10月,還很少有工人敢于離開生產崗位去北京,赴京告狀顯示王洪文比其他工人有更多的造反勇氣。王洪文回來后,曾被國棉30廠的工人造反派王秀珍請去介紹北京形勢;國棉31廠的工人造反派黃金海也專程去17廠,請王洪文介紹北京情況。王秀珍和黃金海都很佩服王洪文。王洪文后來受審判時,對他此次北京之行這樣回憶:endprint
上訪期間,我們參加了毛主席第八次接見紅衛兵,到北京大學、國棉3廠等很多地方,把當時中央領導人講話抄了不少,有陳伯達、江青、關鋒、王力、張春橋、姚文元等人講話。
這些對我影響很大。
回上海,廠黨委已經靠邊站,全廠工作由工作組領導,我對工作組的情緒更厲害了。
我對人說,在北京,工作組已經被扔進歷史垃圾箱,可是,在我們廠,還是工作組的天下。
在王洪文們赴京期間,廠里情況發生了些變化:一是造反派又拉起一支新的戰斗隊“永遠忠于毛澤東思想戰斗隊”(簡稱“永忠”),許多“誓死”隊員也加入了“永忠”;二是廠里保守派工人也以保衛科干事馬驥為首,成立“捍衛毛澤東思想工人赤衛隊”,有5000多人參加,得到工作隊支持。國棉17廠工人已明顯地分裂成兩大派。
10月25日,王洪文一行回上海。回廠第二天正是廠休日,在王洪文提議下,“永忠”和“誓死”合并,仍名“永忠”,王洪文仍被推為負責人。他提出“永忠”的首要任務,就是趕走工作隊。當天深夜,“永忠”全體出動。第二天清晨,上班的工人們發現廠里到處貼著大標語,尤其工廠大門口和工作隊辦公室門前,貼著針對工作組的對聯,每個字都有乒乓球桌的桌面那樣大:“焦鳳嶺哼哼哈哈捧上壓下,施惠珍嘻嘻笑笑奸刁儲腹。什么東西”;“熱淚盼來絆腳石,紙船明燭送瘟神。滾滾滾”;“落水狗禍國殃民,施惠珍罪該萬死。一對寶貨”。這天夜里,王洪文又指揮“永忠”查封工作隊辦公室里工作隊員的抽屜。11月1日,“永忠”貼出《工作隊十大罪狀》大字報,刷出大標語“工作隊靠邊站!”11月4日,“永忠”占領廠廣播臺……“永忠”向工作隊發起全面進攻。
王洪文與工作隊的分歧,在于究竟誰是“文革”對象,究竟如何開展“文革”。王洪文依據的是當時《人民日報》《紅旗》雜志的一系列社論,尤其是“十六條”。“十六條”公布時,王洪文在廠部食堂高興地說:“好像中央在直接指我們廠的形勢。”在整個造反過程中,王洪文始終努力學習和領會各種文件和社論,據徐景賢后來的回憶:
我在和王洪文共事的過程中,多次聽他說過:他在造反的過程中,反反復復認真閱讀毛澤東關于“文革”的指示和《紅旗》雜志的社論,甚至深夜不寐,以此作為自己行動的依據。
而工作隊依據的還是17年的政治運動模式,運動的主動權要掌握在工作隊手里。兩套話語體系不斷發生沖突,工作隊那套話語體系運轉得越來越艱辛而且滯后。往往市委的布置或精神,沒有幾天,和報刊的社論對照就又對不上了。到1966年的10月底,全國驅趕工作隊更是已成大趨勢,主管全市工作隊的市委“社會主義教育辦公室”只得讓駐國棉17廠的工作隊檢查錯誤。
國棉17廠可說是上海工人造反派發源地,王洪文所在的廠保衛科,共有6名黨員與王洪文一起造反,保衛科因此被稱為“紅色堡壘”。和王洪文一起造反的一個黨員“文革”后回憶說:
我們廠黨員造反的很多,而且我們也不像其他廠,派性鬧得那樣厲害,我們廠從沒有武斗過。開批判大會,也從來不給批判對象戴高帽子,即使是對張鶴鳴,也只是叫他站著聽批判,沒有其他侮辱性的措施。后來,干部們絕大多數都解放,擔任各級革委會負責人,除了少數有政歷問題的干部掛著。張鶴鳴后來要求去一紡機廠,王洪文也答應他,讓他擔任一紡機廠的廠革會副主任。
與王洪文對立的保守派,40年以后說起王洪文,說他“到底是共產黨員,比其他的造反派講策略”。“講策略”一詞,在中國的政治語境里還有“講道理”之意。王洪文響應毛澤東號召造反,但他骨子里并不是個完全藐視權威和規則的人,所以他的造反行為不像有些造反派那樣肆無忌憚。這也是以后“文革”在社會秩序恢復階段時,許多造反派紛紛被整肅,而王洪文仍被接納甚至上升的原因。
工作隊沒有公開組織圍攻王洪文,只是不表態,你干你的,我布置我的。但是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上級的不表態支持,實際就是反對;正如下級的沉默,也被上級看作是反對態度。所以王洪文感覺到壓力。實際上,對于王洪文的行動,工作隊始終密切注視并上報市委社教辦公室,前后共寫了15000多字的材料,還寫過一份題為《假左派王洪文大暴露》的簡報,報市委社教辦公室以及工作隊的上級領導紡織局工作團。
1966年9月以后,大批北京紅衛兵到上海串聯,以中共上海市委為批判目標。11月5日,在北京紅衛兵的組織下,上海工人造反派串聯成立了全市性工人造反組織“工總司”,王洪文參加了籌備會,并被推為負責人。從此,他從一個工廠的造反派組織負責人,成為上海最大的工人造反組織負責人。隨著毛澤東對上海“文革”的支持與推動,上海的工人造反派成為“工人階級參加文革”的典型與楷模。王洪文也因此被毛澤東看中,成為中共第十屆中央委員會副主席。1976年10月,“文革”結束,王洪文被判處無期徒刑,1992年8月3日,他因肝病逝于北京獄中,享年58歲。(編輯 王兵)
(作者為上海工運史研究人員)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