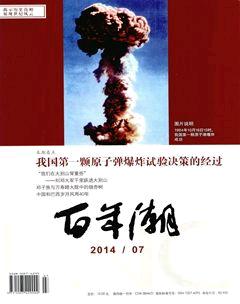促進中美交往的美國學者費正清
彭靖
1979年1月,鄧小平訪美,費正清應邀出席美國政府舉行的國宴,并與卡特總統和鄧小平同桌而坐。中美兩國正式建交后,費正清發自內心地感嘆:“1979年結束了中美兩國之間30年的疏遠狀況,也結束了我作為一個中國問題研究專家50年的奔走呼號。”
作為美國哈佛大學教授、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國際漢學泰斗,費正清是影響美國對華政策的重要智囊成員之一,對中國有著深厚的感情,一生中曾有5次以不同身份來到中國。20世紀40年代他曾受聘于美國政府,兩次被派往中國,與周恩來、喬冠華等人有過多次接觸。他的學術主張對中美關系曾產生重要影響;1972年中美《聯合公報》發表后,他曾率領美國第一批歷史學家代表團訪問中國,受到周恩來總理的熱忱接待。他的學術觀點曾經影響過世界格局的變化,而他與中國領導人周恩來、鄧小平的交往也成為后人津津樂道的一段佳話。
初次拜訪“周公館”
1941年8月,“珍珠港事件”爆發前4個月,已經在哈佛大學任教5年之久的費正清,作為美國研究中國問題的專家,被征召到華盛頓情報協調處(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前身,簡稱COL)。1942年9月,他以華盛頓駐華代表的身份,被該機構派往中國重慶,歷時一年零三個月,1943年12月返回美國,在這期間,他第一次接觸了周恩來。1945年9月,他又重返中國,這一時期,周恩來在重慶領導中共南方局的工作,與費正清又有過多次往來。
1939年1月,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慶秘密成立。同年4月,南方局正式組建對外宣傳小組,由王炳南任組長,陳家康任副組長,組員有喬冠華、龔澎、李少石、章文晉等人。1940年12月后,對外宣傳小組改稱外事組,組長仍為王炳南,副組長為陳家康和龔澎,工作人員有蔣金濤、羅清、李少石、章文晉、沈蓉等。當時在《新華日報》工作的章漢夫、喬冠華,在美國戰時新聞處工作的孟用潛、劉尊祺、劉思慕等,以及在“保衛中國同盟”工作的廖夢醒等同志也參與南方局的涉外工作。當時,這是黨的一支較穩定地開展涉外工作的隊伍。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后,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逐步鞏固,中共外事工作有了更加廣闊的舞臺,南方局與美英在華各機構的聯系更加密切了。除繼續保持與英美駐華大使館、美軍駐華司令總部的聯絡外,還加強了與美國戰時新聞處的聯系。
費正清也清楚地認識到,作為毛澤東和延安派駐重慶的代表,周恩來領導的辦事機構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延安共產黨方面的窗口,從那里可以得到外國新聞機構所需要的延安方面的消息。1943年6月,經他在哈佛大學的一位學生,時任《時代周刊》駐華首席記者白修德介紹,他結識了周恩來的新聞發言人,“一位聰穎而光彩照人的年輕女士”龔澎,并與她成為朋友。龔澎是1935年燕京大學新聞系的畢業生,“一二·九”學生運動的領導之一,早年在北京時就曾與費正清有過交往。通過龔澎,他開始結識周恩來、葉劍英等中共高層領導。
在1943年11月8日的日記中,費正清清楚地記錄了他第一次到中共駐重慶辦事處“周公館”的情景。
“周公館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地方。你需要走進一條臨近懸崖的死胡同,路過求進學校,這里有15個文化和賑災機構,以及美國大使館的辦事處,然后再經過蔣介石公館的大門、行政院,到達路盡頭的一幢白色大房子,那是戴笠的住處。接著突然拐入盤繞于懸崖邊的小胡同,胡同兩邊都是貨攤和各種店鋪,以及縫紉店、糖果店等,十分擁擠。然后再沿著擠滿人群而泥濘打滑的小路走50碼,這時突然又拐入一個門廊,這就是你要找的周公館。”
初次見面,周恩來非凡的領導能力就使費正清深深嘆服。“他英俊帥氣,眉毛濃密,智力超群,直覺敏銳。在我們用漢語談話時,時不時也蹦出一些英語,好在有龔澎為我們雙方作補充翻譯。”“隨后,龔澎介紹我認識她的未婚夫喬冠華。”后來,周恩來、喬冠華等人不僅與費正清建立了朋友關系,還介紹中共地下黨員通過各種途徑相繼參加到美國新聞機構中去開展工作,使戰時新聞處成了中共與美方聯系的一個成功通道。
在戰時的重慶和昆明,有許多被迫從北方南下的中國學者,生活窘迫。了解到該情況的費正清讓夫人費慰梅從美國把藥品和其他日常貴重物品,如名牌派克筆、手表等運往美國駐昆明領事館,分發給在昆明的中國教授、學者們,作為對他們微薄薪水的補貼。當時,一支美國派克鋼筆的價值是相當可觀的,生活急需時可以隨時變賣為現金,補貼家用。為了幫助生活窘迫的西南聯大學者,費正清還通過各種渠道,向美國政府和社會各界大聲疾呼,極力建議美國政府對中國的內政進行有限干預。
以周恩來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通過大量的外事宣傳活動,使國際社會逐漸了解和認識了中國共產黨與延安的存在和作用。費正清功不可沒。
主張美國與中共建交
1945年9月,當費正清以情報協調局駐華新聞處處長的身份第二次來華時,結合他的所見所聞,他以不同的方式提醒美國政府,不能簡單地將國民政府視為盟友。他還預測毛澤東及共產黨會獲勝,主張美國要與中共盡快建立關系。
1946年6月4日,作為美國駐華大使館新聞處處長的費正清和妻子費慰梅(時為美大使館文化專員)等一行,于當日下午四時由北平乘專機抵達張家口。
張家口作為華北重鎮,于1945年8月23日從日本侵略軍的占領下光復,是由八路軍收復的190多座城市中最大的一座。在短短一年多的時間里,共產黨第一次在城市中就政權、經濟、文化教育等方面建設進行了全面的嘗試,取得了豐碩成果,受到了中外媒體的廣泛關注和普遍贊譽。
這是費正清第一次到中共管轄的地區參訪,也是他唯一的一次。“我們拜訪了最高長官聶榮臻將軍,隨后我與威爾瑪(費慰梅的英文名)一同在擠滿熱情洋溢年輕人的劇院作了演講。”這是費正清在中共地區僅有的一次露面,“雖然當時也很想去延安看一看,但一直沒有憑空編造出合適的理由去延安”。
在重慶談判將要取得成果的時候,重慶中共代表團為答謝以費正清為首的美國新聞處,在當時最豪華的勝利酒店舉辦了盛大的雞尾酒會。費正清回憶道:“晚宴分為兩桌,周恩來坐在其中一桌,葉劍英將軍坐在另一桌。大家都顯得興奮而充滿活力。周恩來搖頭晃腦地唱起了歌,我們也跟著哼唱起來,而葉劍英則用筷子敲著桌子和玻璃杯進行伴奏。他們唱起了延安歌謠,相互敬了幾次酒后,我們也唱起了美國內戰時期的歌曲。”27年后的1972年,當費正清再次應邀來到中國,與周恩來見面后重提此事時,倆人彼此都記憶猶新。endprint
“被”出版第一部中文著作
從張家口訪問回來之后,1946年9月,費正清在美國著名的刊物《大西洋月刊》上發表了一篇反思美國政府對華政策的文章《我們在中國的機遇》,力圖糾正美國原有錯誤的對華政策。他在文章中指出:“一個旁觀者感覺到最觸目的一件事,是他們從中國農民最迫切的需要——經濟改善,這是作為他們立黨的基礎,而不是以政治言論自由作為黨的前提的。要知道經濟改善的迫切,我們可以從千萬中國人民所受的苦難中明白地看到。……當一個黨員加入以后,黨的訓練,改變了他的生活。為大眾而工作,為黨而效忠,變成了一個宗教式的信徒,這樣就逐漸磨滅掉少數的、自私的目的。這種大公無私的精神,使共產黨的領導居于有利的地位,而獲到廣大的民心。”他在文章的最后斷言:“如果我們盲目地反對中國革命,最終發現自己將會被群眾運動趕出亞洲。”
這篇文章發表后,不僅是在美國,在中國國內也引起了極大的反響。很快,著名翻譯家李嘉將此文翻譯成中文后,最早發表于1946年9月29日上海《新民晚報》上,并將文章的標題更改為《費正清論中國時局真相》,但對于原文有所刪減。后來,上海的《文萃》雜志和香港的各報,均按照《新民晚報》上的內容進行過轉載(詳見《美人所見:中國時局真相》,現實出版社,1946年)。新中國成立后的第一任教育部長馬敘倫,中國農工民主黨主席、第一任交通部長章伯鈞等人,當時都分別在1946年出版的《民主》《中華論壇》上發表文章,高度贊揚費正清在文章中所表現出的預見與膽識。
費正清在他的回憶錄中曾記載“我曾發表于《大西洋月刊》的文章,帶著謹慎的自豪重新于1974年出版成書《認識中國:中美關系中的形象與政策》”。從目前所能見到的相關文獻來考察,費正清本人未必知道,早在1946年10月,中國的現實出版社就將李嘉翻譯的全文,以《美人所見:中國時局真相》為書名出版,成為費正清出版的第一本中文著作,比后來他出版的《美國與中國》還要早兩年。費正清在日記、書信,以及晚年的回憶錄中,始終沒有提及這本書。而目前國內外的費正清研究學者,也一直將《美國與中國》作為他的第一部著作。
潛心研究中美關系問題
1946年7月,費正清回到哈佛大學,重新開始了他曾中斷5年的教學與科研工作,并積極投入到中美關系問題的討論之中。1948年7月,費正清根據其兩次到中國的經歷,形成綜合研究成果,出版了他的第二部對中美關系有重要影響的著作《美國與中國》,得到了美國政界、學術界,以及中美兩國廣大公眾的普遍贊譽。后來,該書成為尼克松訪華之前重點閱讀的書籍之一,1989年已修訂到了第五版。
作為哈佛學派的開創者,幾十年間費正清培養了1000多名年輕的中國學研究者,其中100多人在他的指導下完成博士論文答辯。他的學生分散在美國和美國以外的100多所大學和研究機構,其中不少已成為著名的中國研究專家。在半個多世紀里,費正清對中國問題的預見性和判斷力,甚至超過了中國人——他以自己獨特的視角審視和考察了中國,他的學術研究、著作和主要觀點代表了美國主流社會的看法,不僅影響了幾代美國漢學家和西方的中國學界,而且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了美國政界和公眾對中國的態度、看法以及美國對華政策的制定。
費正清對于推動中美關系方面的貢獻,最終得到了中美兩國政府的承認。有一次,基辛格就中美恢復邦交問題請教費正清。費正清向基辛格講述了中國歷代的朝貢制度,指出依照此種制度和傳統心理,任何外國元首的登門拜訪都將被毛澤東所接受;而美國總統出訪,則無歷史與任何現實政治上的負擔。費正清還將他在1966年12月發表的《中國的世界秩序:中國的外交傳統》論文,以及隨后出版的著作《中國的世界秩序》一書贈送給了基辛格。基辛格后來評價說:“那次談話改變了歷史。”
與周恩來的最后一次交流
1972年2月,隨著美國總統尼克松訪問中國和《中美聯合公報》的發表,中美之間結束了半個世紀的對立格局。“上海公報結束了尼克松的北京之行,此后,我們開始收到周恩來發出的訪問中國的邀請,一切都是間接的。”5月13日,應周恩來總理的邀請,費正清及夫人一行六人,作為中美關系破冰后第一批應邀到中國進行訪問和演講的美國歷史學家,受到了時任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和外交部副部長喬冠華的熱情接待。
6月16日,喬冠華陪同周恩來總理會見費正清和夫人,以及美國《紐約時報》聯合主編哈里森·索爾茲伯里和夫人等人。周恩來、喬冠華和費正清等人一起在著名的“迎客松”畫像前合影留念。周總理同費正清愉快地暢談了他們30年前在重慶初次見面的情境。費正清回憶起在重慶的一次宴請時,周恩來興致勃勃地唱起了中國當時抗戰歌曲時的場景,周恩來當時輕聲地笑了起來:“我想我不會唱得太多吧!”
合影之后,他們來到能容納20人用餐的安徽廳參加晚宴,周恩來親自挽著費正清夫人的手臂進入宴會廳。索爾茲伯里在他后來出版的《北京及更遠處》一書中,也記錄了當時的情境:“在人民大會堂安徽廳門口,我們站成一排,魚貫而入,費正清走在第一。周恩來身著灰色中山服,胸前戴著‘為人民服務的毛澤東像章,跟來賓一一握手。”
宴會中,“在座的人在周的要求下,都脫掉了上衣,大家談笑風生。席間共有中國人8個,美國人9個”。費正清提出了語言學生和教師的交流,詢問派遣留學生到哈佛大學學習的可能性,宴會持續了4個小時。費正清在會見中發現周恩來喜悅的面孔下“透出久經磨煉的剛毅與頑強”,他說周恩來是一位具有古典風格的總理大臣,一直在權衡時勢,修補殘局。
他們卻不知道,周總理當時已患膀胱癌,病魔正吞噬著他有限的生命,削弱著他那似乎無止境地為國為民服務的精力。而這一次會面,也成為費正清與周恩來的最后一次交流。
與鄧小平的會談輕松幽默
時間轉瞬之間到了1979年。
1月29日早晨,已有179年歷史的白宮顯得分外整潔,南草坪進行了裝飾。約1000名歡迎者揮舞小小的中美兩國國旗,向卡特總統和鄧小平副總理歡呼。endprint
上午10時,卡特總統走出白宮,歡迎儀式開始。美國國務院禮賓司司長多貝爾夫人向卡特介紹主賓鄧小平和夫人。然后,由卡特向鄧小平夫婦介紹美國副總統蒙代爾、國務卿萬斯夫婦、總統安全事務助理布熱津斯基夫婦、艾倫將軍夫婦等。
此時,白宮南面的國會大草坪上,按照接待國賓規格,禮炮鳴放19響。待最后一聲禮炮響起,卡特夫婦陪同鄧小平夫婦登上南草坪正中的演講臺。樂隊先后奏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和美國國歌。
這天,是鄧小平訪美過程中極為繁忙的一天。上午與卡特會談后,鄧小平在中午與國務卿萬斯一起來到國務院共進工作午餐。鄧小平爽朗地在席間簡短致辭,他說:“中美關系正常化,有人說是美國的勝利,有人說是中國的勝利。我認為,應當說是中美兩國人民的勝利。”
晚7時,國宴開始,共140余人赴宴。宴會完全是美國式的,國務院的一位美籍華人書法家用兩國文字書寫了菜單和座位姓名卡。從卡特的老家——佐治亞州穆爾特里運來的1500株紅色和粉紅色的茶花使宴會充滿溫馨的氣氛。
與卡特和鄧小平夫婦同桌的有眾院議長托馬斯·奧尼爾、參院民主黨領袖羅伯特·伯德、著名女影星雪莉·麥克萊恩。作為中國問題專家的費正清與夫人也應邀出席,主持人特別安排費正清在第一夫人和女影星之間就座。
“這真是莫大的榮幸!我大概是被視為30年來積極提倡中美關系正常化一派的代表,如今如愿以償。然而我并沒有為此制訂計劃,所做的貢獻還不足。”費正清在回憶錄中是這樣描述他當時的心情。
女影星雪莉對鄧小平波瀾壯闊的政治生涯表示了欽佩之意。鄧小平笑道:“如果對政治上東山再起的人也設立奧林匹克獎牌的話,也許我有資格獲得這項獎勵的金牌。”
鄧小平對于費正清40年代在美國駐華大使館工作,以及回到哈佛大學開始深入研究中國問題的細節都非常了解。這時他當面詢問:“您貴庚?”
費正清回答:“我已經72歲了。”
鄧小平說:“我今年74歲。”
費正清說:“您還是滿頭黑發,而我早已謝頂了。”
鄧小平幽默地說:“這證明您腦筋用得太多了。”
費正清本想通過敬酒的方式,來一同追憶周恩來,隨后再提議舉行一場中國式的聚會。“然而我什么也沒做,真的徹頭徹尾的失敗”,他后來回憶說。
1979年8月,費正清應邀陪同美國副總統蒙代爾,又一次來到中國,并在北京、西安和廣州進行了為期10天的訪問,還在北京大學進行了演講,以慶祝中美關系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這一次他獲得了補償的機會。“在人民大會堂的第二晚宴中,副總統陪同副總理突然出現在我的身后。鄧小平對我促進恢復中美關系所做出的貢獻給予了高度的評價,我對此并不十分驚訝,借此提議為紀念周恩來而干杯,我們碰了杯。”
1979年,當中美兩國正式建交后,費正清發自內心地感嘆:“1979年結束了中美兩國之間30年的疏遠狀況,也結束了我作為一個中國問題研究專家50年的奔走呼號。”(編輯 王鴿子)
(作者是香港國際商學院客座教授)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