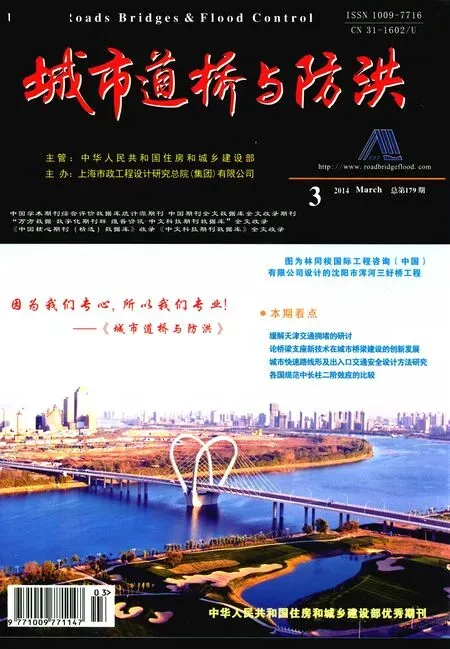不同礦物外加劑對C30引氣混凝土耐久性的試驗研究
曹曉婧,陳 斌
(1.蘭州城市建設學校,甘肅蘭州 730046;2.蘭州九州經濟開發區管委會,甘肅蘭州 730046)
0 前言
在混凝土中摻入引氣劑,引入大量均勻、穩定的微小氣泡,能夠有效改善混凝土的孔結構,是大幅提高混凝土耐久性的技術措施之一[1,2]。不過,適當引氣能夠很好改善混凝土的性能,含氣量較大則不利。在低強度引氣混凝土抗腐蝕性的試驗研究中表明[3]:C30引氣混凝土在目標含氣量為3%左右時對改善混凝土的性能最好,而在混凝土中使用礦物外加劑,也成為提高混凝土耐久性的主要措施[4,5]。常用的粉煤灰、礦渣、硅灰等活性礦物外加劑,由于化學組成、結構、細度等各不相同,其摻入混凝土后各有特點。本文根據已往的實驗資料分別加入不同含量的礦物外加劑來研究不同礦物外加劑對C30引氣混凝土耐久性的影響規律。
1 試驗概況
1.1 試驗原材料
(1)水泥:采用甘肅水泥永登祁連山水泥有限公司生產的42.5級普通硅酸鹽水泥,各項性能滿足標準要求。
(2)砂子:采用級配良好的中砂,細度模數為2.31,表觀密度2.64 g/cm3,堆積密度1 548 kg/m3。
(3)石子:采用級配良好的碎石,粒徑為5~10 mm,含泥量0.3%,表觀密度 2.369 g/cm3,堆積密度1 563 kg/m3。
(4)礦物外加劑:粉煤灰采用蘭州熱電廠的Ⅰ級粉煤灰,礦渣粉為安徽朱家橋水泥有限公司生產的Ⅲ級礦渣粉,硅灰為西北鐵合金廠所產,性能滿足要求,檢測依據為《高強高性能混凝土用礦物外加劑(GB/T 18736—2002)》。
(5)化學外加劑:所摻化學外加劑有減水劑和引氣劑,減水劑為陜西咸陽混凝土外加劑有限公司生產的SDJ聚羧酸高效減水劑,引氣劑為同濟大學研制的粉狀SJ-2型引氣劑。
1.2 混凝土的配合比
結合已往的試驗成果,所設計的混凝土是目標含氣量為3%的不同礦物外加劑的混凝土。其中,JQ表示基準引氣混凝土;FQ表示摻粉煤灰的引氣混凝土;KQ表示摻礦渣的引氣混凝土;GQ表示摻硅灰的引氣混凝土。其配合比情況見表1。
試驗所用的混凝土水膠比為0.5,新拌混凝土的塌落度通過控制水泥用量及減水劑用量控制在160 mm左右。
1.3 試驗方法
利用氣壓式含氣量測定儀來測定混凝土拌合物的含氣量;采用ASTM C1202直流電量法測試混凝土抗氯離子滲透性,根據所測庫侖值,判斷混凝土抗滲透性[6];混凝土抗鹽類腐蝕性測試方法如下:將成型的混凝土試件(40 mm×40 mm×160 mm)標準養護90 d后分別浸泡于強腐蝕鹽溶液和水中,腐蝕溶液中的試件采用干濕循環的腐蝕方式.在借鑒以往試驗的基礎上[7],本試驗干濕循環選擇在40℃(±5℃)恒溫箱中進行,烘干15 h+浸泡9 h,即每個循環為24 h。強腐蝕復合鹽溶液:含鹽總量22.36%,其中硫酸鈉的含量為10.36%,氯化鎂的含量為12.00%.定期測定各類混凝土試件的抗壓抗折強度,以強腐蝕溶液中的試件強度與水中養護試件的強度比值為抗蝕系數來評價混凝土的抗腐蝕性。

表1 各類引氣混凝土的配合比
2 試驗結果及數據分析
2.1 不同礦物外加劑對引氣混凝土物理力學性能試驗結果
由于不同礦物外加劑本身的活性不同,其摻入引氣混凝土后,對引氣混凝土強度的影響有所不同,不同礦物外加劑對引氣混凝土物理力學性能試驗結果,見表2。

表2 不同礦物外加劑對C30引氣混凝土的塌落度、含氣量和抗壓強度的試驗結果
從表2可以看出,摻入粉煤灰后,由于粉煤灰活性較低,造成引氣混凝土的早期抗壓強度較低,略高于基準混凝土,但后期抗壓強度增長較快;摻入礦渣,早期強度較低,后期強度提高較快;硅灰引氣混凝土早期和后期抗壓強度都明顯高于基準引氣混凝土。
2.2 不同礦物外加劑對引氣混凝土電通量的影響
各類型引氣混凝土抗氯離子滲透試驗的結果見圖1。

圖1 目標含氣量為3%的引氣混凝土電通量值(90 d)
在給定三種礦物外加劑相應摻量的情況下,粉煤灰引氣混凝土的抗氯離子滲透性最好,硅灰引氣混凝土的抗氯離子滲透性其次,礦渣引氣混凝土的抗氯離子滲透性能較前兩者略低,但均比基準引氣混凝土有較大提高。從電通量來看,基準引氣混凝土抗氯離子滲透性為中等水平(電通量在2 000~4 000 C),粉煤灰引氣混凝土和硅灰引氣混凝土均為極低水平(電通量在100~1 000 C),礦渣引氣混凝土為低水平,電通量略高于1 000 C。這是由于三者中礦渣的活性較低,硅灰的活性較高,而粉煤灰雖早期活性低,但后期活性較高所致。
2.3 不同礦物外加劑對引氣混凝土抗腐蝕性的影響
各類礦物外加劑的引氣混凝土在干濕循環作用下抗腐蝕試驗結果見圖2、圖3。

圖2 不同礦物外加劑的引氣混凝土在不同齡期的抗壓抗蝕系數

圖3 不同礦物外加劑的引氣混凝土在不同齡期的抗折抗蝕系數
由圖2可知,圖中不同礦物外加劑的C30引氣混凝土在干濕循環腐蝕的條件下,腐蝕60次時其抗壓抗蝕系數均大于1,腐蝕120次時,基準引氣混凝土和粉煤灰引氣混凝土的抗壓抗蝕系數小于1,而礦渣引氣混凝土和硅灰引氣混凝土的抗壓抗蝕系數大于1,加礦物外加劑的引氣混凝土的抗壓抗蝕系數都大于對應齡期基準引氣混凝土的抗壓抗蝕系數。
由圖3可知,腐蝕60次時,基準引氣混凝土的抗折抗蝕系數小于1,加礦物外加劑的引氣混凝土的抗折抗蝕系數大于1,腐蝕120次時,其抗折抗蝕系數都小于1,說明摻礦物外加劑混凝土的抗腐蝕性很強。
2.4 不同礦物外加劑對引氣混凝土的質量變化的影響
不同礦物外加劑的引氣混凝土在腐蝕環境下的質量變化的試驗結果見圖4。

圖4 不同礦物外加劑的引氣混凝土在腐蝕環境下的質量變化
由圖4可知,0~60 d時,FQ質量損失率最大,JQ和GQ非常接近,KQ最小,但四種混凝土總體相差都不大。60~120 d時,FQ質量損失率與0 d~60 d的質量損失率變化不大,而JQ、KQ和GQ的質量損失率都在遞增。
3 結論
(1)摻入粉煤灰,由于粉煤灰自身活性較低,其早期抗壓強度低于基準引氣混凝土,但后期有較大增長。而且可以較大程度提高混凝土的抗氯離子滲透性和抗腐蝕性。
(2)摻入礦渣,其早期抗壓強度低于基準引氣混凝土,但后期有較大增長。而且可以較大程度改善了混凝土的抗氯離子滲透性和極大提高了混凝土的抗腐蝕性。
(3)摻入硅灰,不僅提高了引氣混凝土的強度。明顯的提高了混凝土的抗氯離子滲透性抗腐蝕性。
(4)從試驗結果來看,綜合比較粉煤灰、礦渣和硅灰三種礦物外加劑,硅灰對引氣混凝土的耐久性能改善作用最明顯,礦渣其次,粉煤灰相對較差。
[1]科斯馬特卡,等.混凝土設計與控制[M].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2005.
[2]姚文杰.大摻量引氣劑混凝土在高寒干燥地區的抗凍性研究[J].煤炭技術,2006(8):94-96.
[3]曹曉婧.低強度引氣混凝土抗腐蝕性的試驗研究[D].甘肅蘭州:蘭州交通大學,2008.
[4]Tarun R N,Shiw S S,Bruce W R.Effect of source of fly ash on abrasion resistance of concrete[J].Journal of Mate2 rials in Civil Engineering,2002,9(10):417-425.
[5]Leng Fanguang,Feng Naiqing.An experiment study on the properties of restance to diffusion of ions of fly ash and blast furnace slage concrete[J].Cement and Concrete Re2 search,2000,30(6):989-992.
[6]吳中偉,廉慧珍.高性能混凝土[M].北京:中國鐵道出版社,1999.
[7]石明霞,謝友均,劉寶舉.水泥—粉煤灰復合膠凝材料抗硫酸鹽結晶侵蝕性[J].建筑材料學報,2003(6):350-3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