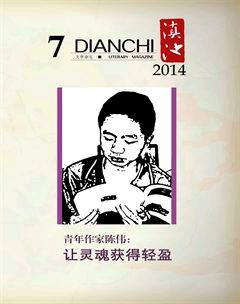兩棵樹的手語
萬利書
1
不知道穆爾克那天是否想到了上帝。“我的上帝啊!這下完了,我什么也做不了啦!”在心里,他會那樣呼喊嗎——“我真要死了嗎?”
二十多年前,一個橡樹般強壯的美國人,在直苴病倒了——那是云南永仁縣的一個偏僻彝鄉,古老,蒼涼,深深浸泡在神話與傳說之中。
病得很重。
深夜。躺在直苴小學那間小屋里,他絕望地掃視屋里冥寂的幽暗。一盞油燈,孤獨地立在桌上。燈光微弱,穆爾克感覺不到一絲溫暖。風悄悄溜進來,撕扯、搖晃著燈焰,屋子忽明忽暗,就像他的心情。床邊那張舊書桌上,一臺手提電腦,和高高一摞寫滿字、畫滿圖的筆記本,將長長的影子壓到他胸口上,讓他有些喘不過氣來——連影子似乎也有了重量。思緒紛亂:從美利堅到云南直苴,從父母妻子到李培森,從現代文明到野鬼時代,往昔一幕幕地,在他腦海中閃現。回憶,卻無法減輕身體難忍的疼痛。油燈倏忽一亮。靠在屋角的那個背囊,石頭般安靜,那里面,裝滿了父母寄來的信,妻子剛郵來的牛肉干和咖啡。你還能背起背囊,回到遙遠的家鄉嗎?他自嘲地撇了撇嘴。現在,他連走到背囊那里,打開它的力氣都沒有了。
近一米九的身高,二十多歲的年紀,他曾那樣精力充沛。每周一次,他會從直苴徒步走到中和鎮去,給在美國的家人打個電話,順便取回他們寄來的包裹。二十多里山路,他撂開長腿,半天一個來回,常常把走慣了山路的李培森,都甩得遠遠的——那時的李培森雖已五十開外,卻身板硬朗,健步如飛。而此刻,燈光下穆爾克那張原本白凈的臉一片蠟黃,全身無力,連翻個身都難。
舊木板房里沒有一點聲音,靜得讓他恐懼。平時也靜,但只要稍一動彈,哪怕在床上翻個身,樓板墻板都會吱嘎亂響,讓他覺著刺耳,心煩,但此刻他寧愿聽到那些聲音,哪怕是老鼠偷食、飛蛾撲火的聲音,以證明他感覺尚存。卻什么都沒有。死一般的寂靜讓他渾身顫栗。無助,恐懼,絕望,伴著腹部巨痛陣陣襲來。如同一個在沙漠中迷路又遭遇風暴的人,他手足無措,只能等待,唯一的希望是熬到天亮,等李培森如時到來。
WILD GHOST,野鬼,穆爾克那時或許就想到了這個詞?在直苴生活了上千年的彝族山民相信,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是有靈魂的,世上是有“鬼”的。幾年之后,當穆爾克將自己的博士論文擴改寫展成一本引起學術界關注的人類學著作時,就用它做了書名:《THE AGE OF WILD GHOST》。那時他肯定再次想起了直苴的那個夜晚。同時也會想起,如果沒遇到李培森,可能他真會成孤魂野鬼,長眠在異國他鄉了。
那樣,也就不會有兩棵樹的故事了。
幸運的是,直苴用一種近乎靈異的方式,拯救了他。
窗外越來越亮,穆爾克心中涌起一絲希望:哦,太陽正在升起!果然,有人推門而入。一道光瀑無聲地涌入,小屋頓時亮堂起來。來人背光,看不實在,只是個森黑輪廓。但穆爾克確信那就是李培森,他不看也知道是他,只會是他。門打開的那個瞬間,李培森正像神一般地向他走來,帶著熹微的光芒和神秘的氣息,而窗外的藍天與群山,只是那個“神”的輝煌背景。他是來救他的,他相信。
——那個逆光畫面,永遠留在了穆爾克心里。世事就是如此,某些清晰明亮的東西會漸至模糊,而對那個森黑輪廓的記憶卻越來越深刻。
李培森一眼看到奄奄一息的穆爾克,也大吃一驚。坐到床邊,他盯著穆爾克看了一陣說:“穆爾克啊,你的肝病嘜,嚴重了!”
穆爾克一驚,他怎么知道?!來中國前,在美國,他就得了嚴重的肝病,治過,沒全治好。臨行前家人還勸他,說中國醫療條件差,你就不要去了。他沒聽勸告,執意來到中國,來到了這個偏僻的山村。他從沒對人說過自己的病,李培森怎么會知道呢?
“來,快起來,去中和或是昆明看病,不然嘜,你會死的。”
“我不去,死也要死在直苴。”在李培森面前,穆爾克近乎撒嬌。
“吔,瞎說!你死不得!你要死在直苴嘜,我麻煩了。”李培森想想又說,“嘜我找藥給你吃,咯要得?你咯相信我?”
穆爾克點點頭,幾未思索。憑什么相信李培森能給他治病?是頭一次見李培森,就被他的直率與見識折服?還是在直苴,李培森是惟一一個他最親近也能指望的人?何況,在直苴這片生活著WILD GHOST(野鬼)的神秘大地,總會有奇跡,李培森正是那個表面粗獷卻內心如神的人。穆爾克知道,即便理性如他,人生有時也需要相信奇跡。
人類學誕生二百多年以來,西方學者慣于將現代西方現代技術文明之外的地方,統統歸結為“野蠻的”、“原始的”、“部落的”、“傳說的”,穆爾克也未能幸免。但他心中的“鬼”,其實是中性的,介于人、神之間,是那些有著某種特質與異能的人。多年之后,在一位中國學者對其《THE AGE OF WILD GHOST》(《野鬼時代》)一書的評述中,依然能明顯看出,他并沒有蔑視直苴彝族的意思。(見吳喬:《人類學家的眼,哲學家的腦,文學家的嘴》——評讀《野鬼的時代》)
從那天起,穆爾克每天三次,按時服用李培森為他配制熬好的中草藥。那些該死的藥湯,苦得他直想罵娘,但在神一樣的李培森面前,他期待著奇跡。
最終,李培森還真把穆爾克從死神手里拉了回來。
不可思議!在美國也沒治好的重癥肝病,居然讓無師自通的李培森用幾副草藥,治好了。難道他真是神?或是神派來的人?他心里充滿了感激。感謝上帝,感謝李培森。
人類學的起源,正是從研究人的體質開始,進而探索人的精神世界的。故事聽到那里,我很想知道,對為他治好了病的李培森,穆爾克是否真正了解呢?他關注過李培森強壯的體質與深幽的靈魂嗎?
2
直苴賽裝場后的山坡,至今,仍是彝人先祖的靈地。按彝人觀念,先祖之靈,世世代代為他們守護著那片名為“斯拍資”的滇樸樹林,由此,那里無形中便有了一個“氣場”。滇樸,那是一種在石縫里也能生長的樹。沒人說得清,那些樹是什么時候種下的,百年,還是千年?也沒人數過有多少棵,幾十,還是幾百?于是那些滇樸,便多了一份神秘。滄桑的枝干,葳蕤的枝葉,或許早已將似水流年寫進了萬千傳說一部史詩,記錄著直苴上千年的悲歡離合,格外透出了些歲月的質感,可觀,亦可觸。
一棵樹,興許就是一份歲月的檔案。
此刻,我就站在直苴村的那個山坡,靜對那片滇樸林,沉思默想,恍惚間覺得,曾與李培森一起在林中漫步,侃侃而談。我似乎聽見他說,你看那棵樹像不像只鳳凰?順著他手指的方向,一棵老樹,樹干粗糲,樹尖蔥郁,映襯于藍天白云之下,還真像一只正以喙梳羽的大鳥。帶著一份虔誠,我走近那棵樹。就在那一刻,我感到了那個“氣場”的力量。靠近樹的根部有個大洞,身材瘦小的成年人能輕易藏在其中。想象不出,那樹曾遭受過怎樣的磨難,是天災,還是人禍?順著光溜溜的樹干往上看,樹冠枝繁葉茂,一無秋盡冬至的肅煞。那些深深刻在樹干褶皺里的滄桑,反倒呈現出那種讓我喜歡也讓我沉思的姿容。
突起一念:那棵樹,不就像李培森嗎?
李培森幼時先天不足,體弱多病,十二歲才進學校念書。那還真是顆頑強的種子,任疾病怎么折磨也沒夭折,直到長成一個滇樸似的彝族漢子。為治好自己的病,他找來各種醫書,晚上點著油燈讀,白天翻山越嶺去找草藥。翻遍幾百本醫書,喝下無數碗藥湯,不光病治好了,身體強壯了,至今七十多歲仍精力旺盛,思維敏捷;順便,還積攢下無數草醫方子,成了遠近有名的土醫生,常有人慕名來請他看病。
“涅槃”。不知怎么,我想到了這個詞——并非所有人,都能從厄難中,獲得一筆人生財富的。
奄奄一息的穆爾克,正是喝了他配的草藥,漸漸好起來的。我曾試圖打探那些藥方,李培森一句話岔開,沒說。不說自有不說的道理,何況他的藥方,從來都在他心里,或亦從無定規。其實就算他說了,我又能在哪里找到那些根根草草呢?治好穆爾克這事,或許遠不止望聞問切開方采藥那么簡單,多多少少,還與神秘直苴那種神秘的氣場有關。
換個方向再看那棵樹,樹形變得像只手了,臂微曲,手平托;像是人手,在邀請四方賓客;亦復佛指,在撫慰世上俗人……反正那像是個手勢。突然想到,穆爾克和李培森的交談,除了半是李培森的初級英語,半是穆爾克會的簡單漢語,是否還要靠雙手比劃呢?如果穆爾克是棵橡樹,李培森就是那棵滇樸,樹的姿勢正是他們的手勢,一種無需翻譯的手語。
如今,李培森已住在永仁縣城,穆爾克也回到了美國,只有那棵樹,那個妙然手勢依舊沒變,一如經典。土生土長的李培森,外出闖蕩了幾十年,又回到直苴,像棵滇樸那樣,撐起了一片綠蔭。想想也真有趣,在這充滿靈性和神秘的地方,兩棵文化背景、生存理念完全不同的“樹”,相遇了。橡樹,現代西方文化,滇樸,傳統彝族文化,就靠著手語與心靈,擦出了生命的火花,并以此為炬,照亮了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博士研究生穆爾克的前程,和云南永仁直苴這個古老彝鄉走向世界的道路。
如今,穆爾克偶爾還會回到直苴,事先卻從不打電話,他知道李培森已經站成了直苴的一棵樹,會在那里等他。李培森甚至說,只要穆爾克踏上旅程,他就會在冥冥中感知。
說起來,李培森和穆爾克的相遇,多少有些偶然。那天,在一個直苴老人的葬禮上,一口行將入土的棺材,吸引了穆爾克。棺木前端刻著一個圓形圖案,似花非花。他問翻譯,那人說是花。“怎么是花呢,那圓圈里是一個篆書的‘壽字。”旁邊一個人開口了。循聲望去,是逝者的一個親戚,臉色平和,眼里卻透著堅毅與自信。粗知中國文化的穆爾克又問:“是嗎?壽是長命的意思,怎么會刻在棺木上?”“哦,中國人希望長壽,又希望能入土為安,所有老人的壽材都是提前制好的,刻上個‘壽字就成了祝福,入土后也告知下界,此人是壽終正寢,別來打擾。”
穆爾克聽得一愣一愣的,當即決定請李培森作他的翻譯兼助手,并干脆把考察地從別處轉到了直苴。
一切都來得那么突然,似乎冥冥中注定,李培森就是彝族先祖派給這個年輕西方學人的文化使者。從此,穆爾克什么都離不開李培森了。一年后,穆爾克即將回國時,決定帶走在直苴的所有記錄,包括他請李培森手繪的一張直苴地圖,那是李培森憑自己的記憶與感覺畫出來的。生活在直苴的人,對這片土地的熟悉,遠遠超過人們的想象。哪里有條路,哪里有道坎,哪里有塊石頭,哪里有棵樹,哪家住地什么地方,轉幾個彎,都一清二楚。直苴盡管從來沒有一幅現代意義上的平面圖,卻人人心里都有一幅活地圖。李培森給穆爾克的,是一幅手繪地圖,是他心里那幅直苴地圖的外化,或許不像用現代測量儀器繪制的那么精準,卻絕對比現代地圖鮮活、豐富,上面標注的,不僅是村寨房舍道路等等的地理方位,更多的是直苴彝族的文化源頭,遷徙、繁衍的世代流向,習俗、風情的現場描摹。那是深愛這片土地者用心繪制的,現代技術絕然無法替代。
穆爾克的論文和著作里,是否提到過李培森,是否有那幅地圖?我不清楚,至今,他的著作沒有中文譯本。但有一點是清楚的,穆爾克的家人,曾將這個論年齡可做穆爾克父親的直苴彝人,用他神秘的草藥和紅糖水治好穆爾克的肝病一事寫成文章,刊登在《紐約時報》上。用穆爾克的話來說,從那時起,全世界都知道了,在中國云南直苴有個“神醫”李培森。
——說到那事時,李培森神情既超然淡定,又不無某種含混的炫耀,那是李培森的一種經典表情。他有那個資本。
3
如今,人到中年的穆爾克,已是密歇根大學人類學系副教授,不時還會到中國來。為研究藏族文化,他已學得一口藏語,就像他當年在直苴,講得滿口彝話一樣。二十多年后的今天,他跟李培森還通過電話、網絡時有聯系,雖然不多,但對李培森這個忘年之交,至少在一件事上,他始終心存感激與敬佩。
當年,為報答李培森的救命之恩,穆爾克曾給過李培森一個極具誘惑的承諾:到美國他舅舅所在的醫院,專治肝病,每月薪水二萬五千美元。條件優厚得令人難以置信,要知道當時一個中國鄉村教師的月工資,只是一百五十元人民幣,李培森給穆爾克當翻譯,每月也不過掙三百元。作為西方國家的盟主,美國和美國人或許始終自信:美國是世人向往的天堂,那樣優厚的待遇,也是所有人的期盼,能將自己的名字登上《紐約時報》這家世界上最重要的報紙,更是每個人夢寐以求的。
但他偏偏沒能說動李培森。
現在,穆爾克或許明白了:李培森是直苴的一棵樹,離不開這片土地,他習慣了這里的水土,也渴望用自己的枝葉,為這片土地投下一片綠蔭。李培森不是沒有思量過,去,還是不去,最終卻堅決地回絕了穆爾克。他的擔心不無道理:美國有直苴這樣的山嗎?山上有那些神奇的草藥嗎?離開了這些,他還能治病嗎?他的那些小小成功,都離不開這片土地。他的根已經深扎在直苴的土地,根根須須的,豈能是說走就走的?再說,他從穆爾克身上已經看到,中國和美國的生活習慣、文化背景差異太大,他是不是能適應那里的生活,別人是不是能接受他,都很難說。
那兩棵樹,都是自信的。穆爾克的自信,張揚。李培森的自信,內斂。那天,像個大孩子的穆爾克收到家人寄來的報紙,連自己都感驚訝,見到李培森,便又是摸臉又是拍肩。在他看來,上了《紐約時報》是天大的好事,李培森會像他一樣欣喜若狂,沒料到李培森卻平靜如初。二十多年后,李培森說起那段往事,就像是在說別人,和自己無關。除了一閃而過的欣慰,看不出他有一絲遺憾和后悔。而那時,穆爾克還沒從骨子里理解李培森,直到知道自己的這位翻譯兼助手是個如有神助的奇人,才對李培森有了一種特別的尊重。
文明與進步是人類共同的追求,但價值取向卻由文化背景決定,沒有統一的標準。
“請你轉告他們,我們這里是文明的地方,不能這樣!”一天,李培森對穆爾克說,神情嚴肅得異乎尋常。起因是一對從加拿大來的夫妻。自打穆爾克來到直苴,直苴人對這些金發碧眼的洋人早已見慣不怪了。那天,那對夫妻也不知是因為什么,高興得又是擁抱又是親吻。李培森剛好看到這一幕,當時什么都沒說,心里卻老大不高興。幸虧沒別人看見,要不還得了?李培森知道那是西方禮儀,沒什么好大驚小怪的,但這里不行,這里是直苴。在李培森和所有直苴人眼里,那是不文明的,有傷風化的。別說李培森不能接受,直苴的每個人都無法接受。
穆爾克有些尷尬,但他知道李培森并非惡意。他把李培森的意思,轉告給了那對夫妻,又給他們講了講直苴的風俗禁忌。入鄉隨俗,對李培森的好意提醒,夫妻倆自是既愧疚又感激。沒想到自己的無意,差點造成不必要的麻煩。
也許有人會對此不屑:嘁,老土!李培森的確“土”,他有著彝族山民特有的面孔大地一般的膚色,身著少數民族最普通的衣服,純粹一個普通農民,怎么還敢去指責洋人?殊不知,那些自認為洋派、高貴的人,靈魂是不是有李培森干凈,純潔,還真是個疑問。
不同文化間,需要溝通和理解,更需要相互尊重。通過考察,穆爾克意識到,直苜人的時間觀是前后交疊,呈螺旋狀發展的。也就是說,每個新的時間段,既重復著前段時間的某些因素,又添加了一些新的內容,如此往復;而直苜人的空間觀念是所有空間范疇互相包含、彼此重疊的。在這個空間里,所有的物質與精神都遵循著從上到下,或說從“頭”到“尾”的單向流動規律。在李培森心里,直苴那片古老山地是“上”,是頭,是河之源,別的低地是“下”,是尾,是河之尾。據此,那天,直苴“野鬼”李培森代表的,正是先人和“上面”,向他人宣示他理解的當地文明。而穆爾克對加拿大夫妻的提醒,表現的也是對李培森和直苴的尊重。這很難得。完成這個交流,靠的不是理論,而是李培森個人的言行舉止。最終,穆爾克將它提升成了理論——他的那本著作,正是這樣論述的。
穆爾克的書中還有這樣一個觀點:現代社會常見的空間觀念,是小空間包含在更大的空間范疇內,是一種從內到外一級級包含的同心圓模式。政權處于同心圓的最核心,即權力金字塔的最頂端,外圍一層層擴散,而偏遠貧窮的地區則處在這個同心圓的最外圍,政治上、經濟上乃至宗教上都被嚴重地“邊緣化”,或說處在金字塔的最底層。他對這種現象頗為不滿。其實,反過來,此說或正可用來觀照他自己的國家:美國從來都自認是“同心圓”中心,金字塔的頂端,他們據此觀察世界,指點江山。但作為一個有良知有操守的學者,穆爾克依然顯示了他的基本素養和科學態度。他對李培森的尊重和敬仰證明,一個自信、有底氣的人和民族,不用低聲下氣,也會贏得別人的尊重。正是這種自信和底氣,讓他內心堅強,無所畏懼。
穆爾克心里的李培森,就是這樣一個人。
4
美國作家、《麥田的守望者》一書的作者塞林格在其短篇小說集《九故事》里寫道:“事情往往都是過后很久才看清,不過,幸福與快樂之間唯一的不同,就在于幸福是實在的固體,而快樂則是一種流體。”
說得好!但這話放在李培森身上,頂多說對了一半。每做決定,他從不盲目,早就想清楚了自己要做什么,怎么做。
譬如當初,當他決定辭去公職回鄉時,所有人都目瞪口呆,以為他是瘋了,豈知他早已深思熟慮。走過千山萬水,回頭一望,是告別,也是重新啟程。那時,已注定他將與穆爾克相遇。沒想到為辭職他寫了數十份申請,為在家鄉落下戶口,又不得不去送禮,盡管那“禮”只是一雙高幫解放鞋。聽上去如天方夜譚,卻千真萬確,發生在李培森身上。
辭職回鄉的理由很簡單——管家,管孩子。這事放在一個工作出色的男人身上,怎么都讓人驚訝。長期兩地分居,也許是李培森決心回家的一個理由——心懷天下是男兒本色,兒女情長也是人之常情——但那肯定不是最根本的理由。
依據穆爾克的論述,在直苴人的空間觀念里,身體不僅“象征”了房屋,或房屋“象征”了社區,而是身體直接“等于”房屋,房屋直接“等于”社區,社區直接“等于”宇宙。李培森的回歸,正是一種認知的回歸,是大到宇宙觀、小到男人責任的回歸——在他心里,家庭即是宇宙。“不安一室,如何安天下?”如此,許多胸懷大志者,或該到永仁到直苴,了解了解李培森這個“野鬼”的家庭觀,不定會對自己的人生有所啟示。
相比當今許多人心的無根流浪,李培森的那次毅然“回歸”,既是從遠方回到家鄉,是身體的回歸、實體的回歸,更是精神的回歸,靈魂的回歸。回到直苴,生活空間似乎小了,精神空間卻變大了。穆爾克所描述的“螺旋狀的發展”,在李培森身上體現得更為鮮明。外出幾十年,讓他對那片鄉土的認知,提升到了一個新的層面。穆爾克的出現,作為一種外來對照,則讓他時時都在比較中,感受著故土的親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