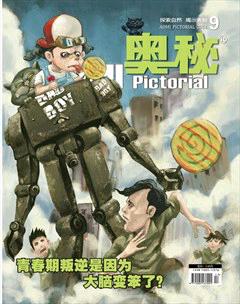“讀夢(mèng)機(jī)”再現(xiàn)夢(mèng)中人
王曉楓

把夢(mèng)投影在大屏幕上
用機(jī)器讀取人類夢(mèng)境內(nèi)容,這聽上去像是電影《盜夢(mèng)空間》里的情節(jié),但科學(xué)家們確實(shí)在努力“追夢(mèng)”。英國《每日郵報(bào)》報(bào)道,美國科學(xué)家研制出一臺(tái)機(jī)器,能在你睡覺的時(shí)候讀出你的夢(mèng)境,并將其投影在大屏幕上。
來自加利福尼亞大學(xué)的神經(jīng)學(xué)家柯文是“讀夢(mèng)機(jī)”實(shí)驗(yàn)的主導(dǎo)研究者之一,他表示,“我們?cè)趯?shí)驗(yàn)中采用的方法能夠進(jìn)行極其準(zhǔn)確的臉部信息神經(jīng)重構(gòu),這不僅為人臉識(shí)別技術(shù)研究提供了一種新穎的方法,還令重構(gòu)夢(mèng)境、記憶和想象有望成真。”
這項(xiàng)新技術(shù)究竟是怎樣“讀夢(mèng)”的?研究人員招募了6名志愿者,向他們展示了300幅不同的人臉圖像,并利用核磁共振掃描儀記錄其大腦運(yùn)動(dòng)。通過這些信息,研究人員可以分析:當(dāng)志愿者看到不同的面部特征時(shí),例如金發(fā)碧眼或絡(luò)腮胡等,他們的大腦神經(jīng)作何反應(yīng)。
研究人員將這些反應(yīng)方式集合起來建立一個(gè)數(shù)據(jù)庫,而后給志愿者看一組新的人臉圖像,并觀測他們的大腦反應(yīng)。通過將記錄下的大腦反應(yīng)與數(shù)據(jù)庫進(jìn)行比對(duì),研究人員得以重構(gòu)志愿者第一次看到的人臉圖像。
研究者們認(rèn)為,“神經(jīng)關(guān)聯(lián)”存在于所有人類活動(dòng)中,人類的思想和感覺僅僅是一種復(fù)合模式的化學(xué)反應(yīng)。而部分神經(jīng)學(xué)家認(rèn)為,只要能夠研制出足夠敏感的儀器,就有可能讀懂這種模式。
“讀夢(mèng)機(jī)”的研究團(tuán)隊(duì)認(rèn)為,這項(xiàng)技術(shù)在未來能夠被重建人類大腦中的記憶、想象和夢(mèng)境。還可以被應(yīng)用到生活中,例如,在犯罪案件調(diào)查中,調(diào)查人員可以利用核磁共振掃描幫助目擊者重建對(duì)犯罪嫌疑人的記憶。
科學(xué)家發(fā)明“夢(mèng)境捕手”
紐約大學(xué)科學(xué)家布庫爾解釋,利用“讀夢(mèng)機(jī)”提取人腦中的面部信息,是成功研究出先進(jìn)讀心術(shù)的第一步,“我們正在向重建夢(mèng)境邁進(jìn),雖然像高清電影那樣的夢(mèng)境不可能很快成為現(xiàn)實(shí),但我們已經(jīng)找到改進(jìn)方法,完整讀取大腦活動(dòng)只是時(shí)間問題”。
這種方法可能有助于人類理解夢(mèng)境,但從人腦中提取信息卻引發(fā)一些擔(dān)憂。柯文向公眾表示,這項(xiàng)技術(shù)不會(huì)強(qiáng)制提取信息,“這項(xiàng)技術(shù)只能讀出大腦活躍部分的內(nèi)容,而不能讀出靜態(tài)記憶,因此你必須讓接受實(shí)驗(yàn)者去想象,讓大腦動(dòng)起來,我們才能讀取信息。”但他也指出,也許在未來,技術(shù)的進(jìn)步可能會(huì)有助于讀出靜態(tài)記憶,這將面臨一個(gè)難題——如何精確掌握大腦的構(gòu)造,因?yàn)槲覀儗?duì)大腦的了解并不多。
柯文所言非虛,大腦的神經(jīng)網(wǎng)絡(luò)總長約16萬公里,由被稱為白質(zhì)的神經(jīng)纖維所組成,聯(lián)結(jié)了心智的各個(gè)區(qū)塊,我們的所思、所感、所知都來自于此。這也正是美國為何耗資逾30億美元繪制大腦地圖。人類研究大腦雖已有數(shù)百年歷史,但直到今天仍未完全理解大腦構(gòu)造。
無獨(dú)有偶,要發(fā)明“讀夢(mèng)機(jī)”的并非只有柯文,《科學(xué)》雜志上發(fā)表了日本國際電氣通信基礎(chǔ)技術(shù)研究所堀川友慈的一篇文章,文中談到了堀川友慈設(shè)計(jì)的一款電腦程序——“夢(mèng)境捕手”,能夠讀取人類夢(mèng)境,精確率達(dá)到60%,這與《盜夢(mèng)空間》的劇情十分相似。
堀川友慈的實(shí)驗(yàn)方法與柯文從原理上類似,他們招募了3名20歲至39歲的男性志愿者,參與為期10天、每天3小時(shí)的讀夢(mèng)實(shí)驗(yàn)。
志愿者入睡后,研究人員先利用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技術(shù)將志愿者睡眠時(shí)的大腦活動(dòng)記錄下來,6到7分鐘后再喚醒他們,請(qǐng)他們描述夢(mèng)境,這個(gè)過程重復(fù)200次。
研究人員把志愿者的描述與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儀記錄的腦圖像對(duì)照,建立數(shù)據(jù)庫,據(jù)此整理出3人睡夢(mèng)中常見的內(nèi)容,并將這些內(nèi)容分成20個(gè)類別,再與3人清醒狀態(tài)下見到相似場景時(shí)的腦活動(dòng)相比較,就得出每個(gè)類別的腦活動(dòng)特征。通過這些特征,研究人員推測出志愿者在夢(mèng)里看到什么,準(zhǔn)確度達(dá)60%。
能讀取的只是“睡前幻覺”?
對(duì)于這種研究夢(mèng)境的方法,也有科學(xué)家表示了不同意見,他們認(rèn)為,通過這種方法研究的可能不是夢(mèng)境,而是睡前幻覺。牛津大學(xué)認(rèn)知神經(jīng)科學(xué)家馬克·斯托克斯表示,一臺(tái)“讀夢(mèng)機(jī)”不可能解讀所有人的夢(mèng)。還有神經(jīng)學(xué)專家稱,在這一實(shí)驗(yàn)中,志愿者只進(jìn)入淺層睡眠。因此,從嚴(yán)格意義上講,這些志愿者在實(shí)驗(yàn)中并未處于夢(mèng)境狀態(tài),他們所謂的夢(mèng)境其實(shí)只是幻境。
哈佛大學(xué)醫(yī)學(xué)院精神病學(xué)家、夢(mèng)研究專家阿倫·霍步森也指出,從技術(shù)角度而言,受試者描述的這些影像根本不能稱為“夢(mèng)”,它們是“睡前幻覺”,與發(fā)生在睡眠階段的夢(mèng)在生理學(xué)上有本質(zhì)區(qū)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