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電影華麗逆襲的交流革新
□文/楊 會,常州信息職業技術學院藝術設計學院講師,華東師范大學傳播學院博士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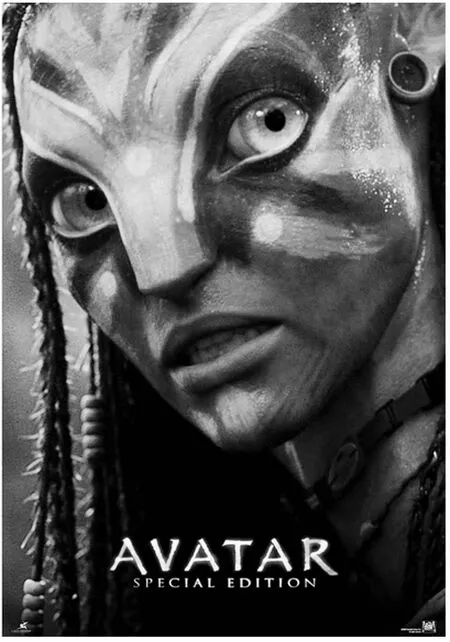
電影《阿凡達》海報
一、3D電影的華麗轉身
隨著3D版《阿凡達》的上映,3D電影再次激發了人們的觀影熱情,對于大眾而言,3D電影似乎是方興未艾,但從電影的發展歷史來看,現時炙手可熱的3D電影熱潮無異于其重裝后的華麗逆襲,因為3D電影實際上興起于19世紀20年代,而其技術的產生則可以追溯到18世紀。
3D成像技術最遠可以追溯到1844年,一位名字叫做D.B的外國人通過一個立體鏡拍下了世界上最早的3D照片。
1890年前后,英國電影先驅威廉·弗里斯格林(William Friese-Greene)發明了雙機放映3D電影技術,是3D電影的最早起源。[1]
1922年,第一部3D電影:《愛情的力量》誕生,早期的3D電影通常以展示立體效果為主,片中常以扔向觀眾的物體等鏡頭制造噱頭。
早期的3D電影最終因為其自身技術及題材的限制而逐漸淡出人們的視野并最終在歷史的舞臺中暫時沉寂,20世紀90年代以后,隨著電影拍攝技術及特效技術的進一步成熟,3D電影得以重裝再整,并帶來了全新的視覺體驗。
二、3D電影的視覺成像原理
3D電影的觀看需要利用人的左右兩只眼同時識別真實世界里的空間這一原理,人以左右眼看同樣的對象,因為兩眼所見角度略有不同,在視網膜上成像的位置并不完全相同,這兩個像經過大腦綜合以后就能區分物體的前后、遠近,從而產生空間感。立體電影的原理是通過兩臺攝影機模仿人眼的視角同步拍攝,在放映時也通過兩臺投影機同步放映至同一面銀幕上,通過立體眼鏡分別還原左右眼的影像,進而在大腦中合成立體的視覺影像。觀眾看到的影像與真實世界有極大的相似性,有些物體離觀眾很遙遠,有些似乎觸手可及,這些獨特的視覺效果給觀眾以身臨其境的真實感。
三、3D電影中的感知與交流
3D電影中近在咫尺的物體:旋轉于我們周圍的花瓣,激蕩而出的水滴,迎面而來的子彈,讓觀眾在觀看時不由自主地試圖用身體去觸摸眼睛所感知的世界,這一觀影環境已經突破了2D影像時代“窺視”觀影的環境,觀眾在真實與虛幻的建構中闖入了類真實的時空領地,并尋找到了自身與這一時空交互的可能性,觀影中的交互使得觀眾在影片的時空中尋找到了自身的存在感。可以說,觀眾視覺的強烈體驗和身心的積極參與開創了觀影的新篇章。
(一)3D電影中的“感知”
1.Z軸:創建類真實的時空感受
法國的現代電影理論宗師安德烈·巴贊在《攝影影像的本體論》中提出“攝影影像具有獨特的形似范疇。”[2]在2D電影中,這一觀點被“新浪潮”借鑒并形成了寫實主義風格。從拍攝及展示的層面而言,2D電影中的場景只具備水平X軸和垂直Y軸兩軸,因而在空間的表現上欠缺真實感及現場感。而在3D電影中,3D電影的拍攝及展示均是通過模擬人的雙眼的視差,從而形成類似真實世界的現場感。從拍攝及展示的層面看,3D電影中的場景具備真實空間的水平軸x、垂直軸y、縱深軸z。在Z軸參與場景中建構藝術作品的表現時,巴贊所言的“逼近現實”才具備了被觀眾體驗和感受的可能性。
當3D電影突破二維空間限制向三維空間建構邁進時,3D電影的場景進一步向真實的物質世界靠近。從觀眾的角度來看,則意味著觀眾的空間體驗不再完全是依靠經驗建構或想象建構的空間,而是實實在在能夠通過人體感官感受到的空間,這一空間感顛覆性的建構意味著3D電影在視覺體驗上的全新變革。
2.存在感:身體介入,心理融入
傳媒大師麥克盧漢在《理解媒介—論人的延伸》一書中提出了“人的感覺—一切媒介均其延伸。”[3]3D電影恰恰體現了人體感官的延伸,3D電影使得雙眼與大腦機制聯合建構類似于真實世界的立體影像成為常態,這一身體介入機制也導致了觀影心理的改變,2D電影觀影中的“間離感”逐步抽離出觀影過程,觀眾因感官的介入及心理感受的變化,而在類真實的觀影時空中重新建構了自身的存在感。3D電影利用其成像上向前延伸的立體性而出現某一物體突然迎面而來的視覺效果,這種視覺效果從生理反應上來說極富刺激性,當某一物體突然超過這個距離接近人時,人會條件反射性地退讓。此時,人的這一生理反應,已使人與他所見之物發生了聯系,人已經參與了作品中。[4]自身存在感意味著觀眾觀影的身心融入,Z軸的運動鏡頭或出畫鏡頭的使用,均充分考慮了觀眾存在感的介入,這一存在感的發展將是3D電影技術的獨特優勢。
阿恩海姆在《視覺思維——審美直覺心理學》一書中認為,“視知覺不是對刺激物的被動復制,而是一種積極的探索與選擇的活動。”[5]在2D電影中,觀眾的審美是被動的接受影片所建構的虛擬時空,而3D電影的類真實時空能讓觀眾積極參與到觀影之中,并自主選擇需要關注的重點,所以觀看3D電影時的主動權在觀眾手上。
這就意味著,3D電影的視覺體驗的變革及因此帶來的觀眾的存在感的建立,均可能帶來觀影觀眾的交流方式的改變。
(二)3D電影中的交流
人類生活中,交流是最普遍、最常見卻極為難以表述的一種行為,而華慈拉威克曾說過,“人不能不交流。”[6]人的交流是人的一種本質化存在。現實的狀況是,交流無處不在,同樣,在藝術作品中,交流也無處不在,不過對于華麗轉身后的3D電影所帶來的視覺與心理震憾中,孕育其中的交流的獨特性,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
1.“交流”
正如《柯林斯詞典》解釋的那樣:“交流,是指信息、思想、感受的發送和交換。”[7]通過這一定義不難發現,人類交流無非是通過語言系統或非語言系統兩種交流方式實現信息、思想等的發送和交換。
語言系統的交流意味著,人們能夠成功交流的前提條件是說話者通過約定的發音表達出某一概念,而這一概念是被大家的經驗所認可的對象,這時說話者與聽眾達成了共同的認知,這時的交流才能夠實現。
不過,人們的交流除了語言系統外,非語言系統的交流也很重要,人類初始的交流便是非語言系統,如手勢、身姿、表情等作為交流的基本手段,即便是語言交流占重要地位的今天,非語言交流依舊是不可替代和無可比擬的。
在3D電影的觀看過程中,觀眾與3D電影的交流往往是語言系統與非語言系統并用的一個交流過程。
2.藝術作品中的交流
藝術作品是創作者試圖用自己創造的符號系統與觀眾交流的一種方式,無論是文學作品,音樂還是電影,均致力于與觀眾的溝通交流,艾布拉姆斯在《鏡與燈》中提出了“作品、作者、宇宙、讀者為文學四要素”[8]的說法。這種說法至今仍被沿用。在艾氏的描述中,藝術作品可以通過作品、作者、宇宙、讀者四要素的相互作用形成人與人、人與世界的交流,而作品創作的目的是為了讀者,也即通過交流引起讀者的關注和思考。
同樣,在3D電影中,作品、世界、作者、讀者之間交流也是不斷的發生,但這樣的交流是否與傳統的2D電影中的交流有著不一樣的地方,如果存在不同,有何不同?這是我們試圖弄清楚的問題。
3.3 D電影中的交流
正如麥克盧漢理解的一樣,大眾傳媒的使用派生出了一些心靈的習慣:“我們塑造了工具,工具此后又塑造了我們。”[9]電影這一大眾傳媒不外乎借助電影這一媒介講故事,在講故事的過程中實現對話與交流,因而對于3D電影中交流的分析,主要試圖從講故事的傳播過程這個角度來探究其究竟帶來了哪些改變。
首先,從傳播的角度看2D電影的交流和3D電影的交流,存在著很大的區異性,2D電影的創作者通過鏡頭語言的編碼,通過影片放映將信息傳遞給接收者,觀眾獲取信息后進行解碼,這一交流過程趨向于線性的交流過程。而3D電影的創作者在創作之初,就已經將觀眾作為影片的組成部分進行鏡頭語言的編碼,因而在影片的放映過程中,觀眾能夠適時的與影片內容進行語言的或身體的及情感的直接互動,在互動的交流中參與編碼及解碼,這一交流過程打破了被傳播系統所禁錮的線性交流模式,3D電影的交流出現了新型互動的交流特點。
本雅明認為講故事的人和聽眾之間存在聽說互動,而隨著小說的興起,講故事的傳統慢慢消失了,由此他得出一個驚人的結論:“個體經驗的可交流性正在消失。”[10]實際上,借鑒本雅明關于講故事與寫小說的區別的界定,2D電影的講故事與3D電影的講故事有著實質性的差異。2D電影中講故事時的強制思維的方式使受眾成為被動的消費者,以至于他們沉溺于孤獨而疏離的思考狀態。而3D電影中講故事時的特殊視覺效果則使得觀眾在觀影中身心融入影片構建的類真實時空中,這一融入使得自我從自己占據的獨一無二的存在方位和時間出發來應對其它的自我和世界[11],融入后,自我內心的存在感使得觀眾在面對一些場景時不有自主的發出聲音或在身體或表情上有所回應,這一直接的交流使得3D電影的交流與2D電影時代相比具有實質性的突破,3D電影的交流似乎回歸了古老的講故事傳統,也在這一新型講故事式的交流方式中為個體經驗的獲得提供了契機。
巴赫金的對話理論將對話分為人與人之間的對話及人物與其內心的對話兩種形式,電影作品的交流就是人物內心關于想象世界的對話,通過個體的思維去構建事件發生的時空,這一交流過程中涉及了作者、世界、作品、讀者的多邊的基于想象界的交流,從對話的角度講,2D電影是一個觀眾與作品的直接對話及觀眾與作者的間接對話的過程。而觀眾與世界的交流是通過與作品及作者的交流而逐步形成的。而3D電影中的交流凸顯了視覺感官的直觀作用,觀影過程更像是在游樂場乘坐云霄飛車一類的驚險游戲,讓人激動得透不過氣。[12]這一交流過程不論在感官上還是在心理上均縮短了讀者與世界的距離,也就意味著3D觀影中通過觀眾直接與類真實世界的對話,在這一對話中,實現了觀眾與世界、觀眾與作品中的人物的直接的情感、動作的勾連。也即意味著觀眾與類真實世界的交流是不間斷的、持續的過程,觀眾在與類真實世界的對話中不斷思考,整合觀點,形成自己的經驗。作者或作品試圖表達的觀點只有在融入類真實的世界,才能被觀眾所體驗并實現與觀眾的交流。3D觀影的觀眾通過這一對話進程完成自我與世界的交流。
小結
人總是在與世界的交流中實現自己的認知和價值的,在我們認識世界時,我們必須與世界有實質性的接觸,不論是身體感官的,還是內心的,只有讓觀眾在與世界的接觸中形成思考和認知,個人與世界的真正交流才得以實現。3D電影構建的類真實世界通過與觀眾的感官的及內心的互動提供了個人與世界多元、互動交流的新途徑,觀眾在類真實的時空間可以體驗生命歷程,重新思考自我與世界的關系,迅速形成認知并獲取經驗,并為自我與真實世界關系的思考提供關照。
[1]田長樂.3D電影及其發展展望[J].當代電影,2011(4):153.
[2]楊遠嬰.電影理論讀本[M].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2:193.
[3][9](加)麥克盧漢.理解媒介—論人的延伸[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50,17.
[4]胡奕顥.3D電影美學初探[J].北京電影學院學報,2009(4):86.
[5]魯道夫·阿恩海姆.視覺思維[M].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87:56.
[6]周曉明.人類交流與傳播[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0:1.
[7][10](英)D·H 梅勒.交流方式[M].北京:華夏出版社,2011:102,106.
[8](美)艾布拉姆斯.鏡與燈:浪漫主義文論及批評傳統[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4.
[11]丁亞平.藝術文化學[M].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5:63.
[12]張悅等.從窺視到闖入:3D電影的藝術美學之思[J].電影文學,2013(1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