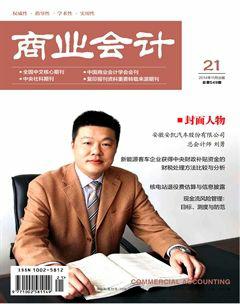股權結構、董事會特征與財務報告舞弊
(鄭州大學商學院 河南鄭州 450001)
一、引言
上市公司股東作為資本的所有者,不直接負責經營;直接負責經營的經理層,對資產不擁有所有權,委托代理關系造成了所有權、經營權相分離。根據經濟學理性人假設,個體都有追求私人利益最大化的動機。信息優勢地位會促使管理者做出對自己有利的決策,生產管理中,會選擇自己最受益的方案,信息披露時,會錯報或漏報財務信息,誤導投資者和債權人。這種蓄意錯報或漏報財務信息的行為稱作財務報告舞弊。
財務報告舞弊行為影響因素很多,其中公司治理尤為重要,而公司治理又受股權結構和董事會特征影響。大股東持股比例過高可能會與管理層合謀舞弊;股權過于分散會產生“搭便車”問題。董事會兼有所有者的代理人和管理層的委托人的雙重身份,在公司治理結構中具有重要地位,是公司內部治理的核心。良好的董事會構成是董事會有效運作的前提,對財務報告舞弊的發生具有明顯的抑制作用。優化股權結構,提升董事會運作效率,約束監督管理者行為,對于遏制財務報告舞弊行為具有重要意義。
由于農業上市公司是近年來財務舞弊案的高發區,所以本文對其2003-2012年樣本數據進行Logit回歸分析,檢驗其股權結構、董事會特征對財務報告舞弊的影響度,以期為證券投資者、分析師、監管機構提供參考,監督和防范財務報告舞弊行為;為股東、管理層提供啟示,提升公司內部治理水平。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一)股權結構
1.股權集中度與財務報告舞弊。Shleifer&Vishny(1986)認為,股權集中可以弱化股權分散導致的“搭便車”問題,大股東密切關注自身利益,有足夠的動機監督管理者行為,管理者的舞弊機會減少。 La Porta(1999)指出,股權過度集中會產生較高的控制權和現金流權分離度。利益動機驅使大股東與管理層合謀進行利益侵占,舞弊可能性加大。 Jesen&Meckling(1976)發現,股權集中度與財務報告舞弊呈U型關系。過低的持股水平易導致機會主義行為,較高的持股會產生公司利益趨同效果,容易因權力集中發生舞弊行為。
故本文提出假設1:股權集中度與財務報告舞弊呈U型關系。
2.管理層持股比例與財務報告舞弊。雷光勇(2006)認為,管理層是否舞弊一定程度上取決于其對公司業績的貢獻、剩余索取權大小和對會計信息的控制能力。職位和股權賦予了管理層對公司的領導權和控制權,使其對會計信息有較強的控制能力。在缺乏有效的內外部治理情況下,管理層擁有實際上的絕對控制權,這種絕對控制權與剩余索取權的錯位易誘發舞弊行為。更進一步,管理層持股比例的增加擴大了其剩余索取權,在效用最大化的心理作用下,舞弊行為極易發生(洪葒,2012)。
故本文提出假設2:管理層持股比例與財務報告舞弊正相關。
(二)董事會特征
1.董事長、總經理二職合一與財務報告舞弊。陳關亭(2007)實證研究表明,由總經理擔任董事長的董事會易淪為擺設,造成監督缺位,財務報告舞弊易發生。故二職合一的職位設置與財務報告舞弊正相關。我國農業上市公司大多數是家族式企業,董事長兼職總經理這種一元領導權結構較為普遍。總經理在會計政策選擇方面擁有獨斷權,形成實質上的內部人控制,董事會的監督職能大大減弱。
故本文提出假設3:董事長、總經理二職合一的組織結構與財務報告舞弊正相關。
2.董事會規模與財務報告舞弊。Jensen(1993)研究發現,小規模董事會在溝通上存在優勢,對經理層舞弊行為的監督更有效。Beasley(1996)認為,較大董事會規模并未對應較高董事會會議出席率,決策時搭便車現象較為嚴重,而且容易造成實際上的管理層操控。伊志宏(2010)認為,過小的董事會規模限制了投資者參與公司治理行為,難以有效監督經理人;過大的董事會規模也會造成決策效率低下,難以起到應有的監督作用,故董事會規模與財務報告舞弊存在U型關系。大規模董事會允許更多的投資者參與公司治理,管理層所接受的監督更多,財務報告舞弊可能性降低。
故本文提出假設4:董事會規模與財務報告舞弊負相關。
3.獨立董事數量與財務報告舞弊。 Fama&Jesen(1983)認為,董事會監控職能強弱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其構成情況,經理層本已占據信息優勢,若在董事會中再占據主導地位,則股東財富很容易受到損失,獨立董事的引入可解決這一問題。王躍堂(2008)認為股權缺乏制衡大大削弱了財務信息質量,獨立董事的介入使董事會能夠擺脫外界的干預,提高財務信息的真實可靠性。
故本文提出假設5:獨立董事數量與財務報告舞弊負相關。
4.董事會會議次數與財務報告舞弊。關于董事會會議次數與財務報告舞弊的關系,實證研究主要存在兩種觀點:一種是顯著的負相關關系(Anderson,2004;陳關亭,2007);另一種是不存在顯著的相關關系,代表學者主要有楊清香等(2009)、洪葒(2012)等。頻繁的董事會會議對應兩種可能情形:一是活躍的內部溝通;二是對隱患的被動反應。董事會會議次數越多,表明董事會為公司的經營管理付出的時間和精力較多,越有利于問題的及時有效解決。
故本文提出假設6:董事會會議次數與財務報告舞弊負相關。
三、研究設計
(一)變量測量
被解釋變量舞弊表示農業上市公司是否被中國證監會、財政部、上海證券交易所及深圳證券交易所等監管機構判定為存在違法行為。具體包括虛列資產、虛構利潤、虛假記載、推遲披露、重大遺漏、會計處理不當、占用公司資產等。公司當年存在違法事實并被監管機構給予懲罰時,該變量取1;否則取0。為控制其他變量對財務報告舞弊的影響,本文考慮引入5個控制變量。被解釋變量、解釋變量和控制變量的選取及定義見表1。

表1 模型變量及其解釋
(二)回歸模型與方法
考慮被解釋變量是取值為0、1的虛擬變量,本文采用Logit模型進行估計。為檢驗假設1,本文建立了非線性多元回歸模型 (1); 如果FIRST與FRAUD滿足二次函數關系,則表明股權集中度的機制存在,使舞弊行為得到最大程度的抑制。為檢驗假設2-6,本文建立多元回歸模型(2)。
模型 (1) 中,X1為解 釋變量FIRST;模型(2)中,Xi(i=2,3,4,5,6)代表 解 釋 變 量 MSH、DUAL、DIREC、IND、BOMEET。
四、樣本選擇與描述性統計
(一)樣本選擇
本文以2003-2012年我國農業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分財務報告舞弊樣本組和未舞弊配對樣本組兩組。舞弊樣本組是指研究期間至少有一次被監管機構判定為存在違法行為的公司。研究期間內,CSMAR數據庫記錄的農業上市公司共49家,其中發生過舞弊行為的有15家,構成本文的舞弊樣本組。另采用Beasley(1996)的方式選擇15家公司構成無舞弊配對樣本組:(1)2003-2012年間從未被監管部門處罰的中國農業上市公司;(2)與舞弊公司首次舞弊前一年資產規模最為接近。最后,剔除缺乏完整資料的公司,共得樣本數據225條。
(二)描述性統計
下頁表2給出了除虛擬變量外各變量的描述性統計。解釋變量股權集中度最小值為10.3%,最大值為79.6%,二者相差近70%,標準差為0.161,樣本間差異較大,適合做多元回歸分析;均值為0.366,中位數為0.326,為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的一般水平,體現了我國農業上市公司股權集中的特點。管理層持股比例最大值為64.9%,最小值為0,中位數為0,說明至少有一半的農業上市公司管理層未持股,差異很大,故研究其對舞弊的影響有一定意義。董事會規模最大值為18,最小值為5,二者相差13,標準差為2.105,樣本間差異較大,適合做多元回歸分析。獨立董事數量最大值為5,最小值為2,標準差為0.657,分布較為集中;中位數為3,表明有50%的農業上市公司在2-3人之間,人數較少。董事會會議次數在2-33之間,最小值最大值相差31,標準差為4.367,差異較大。

表2 全樣本描述性統計
五、實證結果與分析
(一)顯著性檢驗和相關性檢驗
1.顯著性檢驗。為檢驗公司治理對財務報告舞弊的影響,本文對各指標進行了兩配對樣本t檢驗,分析舞弊公司和未舞弊公司樣本間各指標的差異情況,統計分析結果因篇幅限制未列示。檢驗結果表明:舞弊公司與未舞弊公司的董事長與總經理職位設置、董事會規模在1%水平差異顯著;管理層持股比例、獨立董事數量在5%水平差異顯著;差異性檢驗初步支持假設 2、3、4、5。 大股東持股比例、董事會會議次數兩個指標在兩類公司之間差異不顯著,假設1、6無法得到驗證。六個變量中有四個變量存在顯著性差異,舞弊樣本組和未舞弊樣本組之間有較大區別,本文所做的研究有一定意義。
2.相關性檢驗。為了避免指標之間的高度相關對研究結果產生影響,本文對全部指標作了相關性檢驗,結果因篇幅所限未列示,各指標之間不存在顯著的相關關系,可以進行回歸分析。
(二)回歸結果
本文采用Logit模型方法進行,得到模型 (1)、(2) 的回歸結果。(1)FIRST 與 FRAUD 之 間 系 數 為28.874,在 1%水平上顯著;FIRST2與FRAUD之間系數為-37.750,在 1%水平上顯著。總體呈先降后升的U型關系。假設1得到驗證。 (2)MSH與FRAUD之間系數為 4.705,在 5%水平上顯著。過高的管理層持股比例易引發“內部人控制”及自利行為,進而發生財務報告舞弊。假設2得到驗證。(3)DUAL與FRAUD之間系數為1.460,在1%水平上顯著。二職合一的職位設置減弱了董事會的監督作用,加大了財務報告舞弊發生的機會。假設3得到驗證。(4)DIREC與FRAUD之間系數為-0.289,在1%水平上顯著。較小董事會規模不僅使經營決策權集中,而且也不能得到多方面的意見,財務報告舞弊行為容易發生。假設4得到驗證。(5)IND與FRAUD之間系數為-0.520,在10%水平上顯著。內部董事可能會與經理層合謀,獨立董事的立場相對中立,能夠擺脫外界干預,客觀地評價經理人的行為。假設5得到驗證。(6)BOMEET與FRAUD之間系數為-0.045,但不顯著。驗證了二者的負相關關系,但并不顯著。假設6未得到驗證。造成這一結果的原因在于:較高頻率的董事會也可能是因為隱患而采取的被動反應。
(三)穩健性檢驗
為檢驗研究結論的穩定性,作穩健性檢驗:縮小樣本規模。剔除屬于FIRST變量上下10%的樣本,剩余樣本Logit回歸,結果因篇幅所限未列示,主要變量系數的符號和顯著性,和原回歸結果保持一致。由此說明研究結論基本上是穩定的。
六、政策建議
本文研究結論的政策意義可以總結為:完善股權結構、董事會制度的安排,將有助于抑制財務報告舞弊行為。具體表現為:第一,適度的股權集中。股權分散化會產生股東與經理層之間的代理問題,不利于對經理層行為的監管;一股獨大導致權力過度集中,為獲取控制權私有收益,大股東會侵害中小股東利益,為掩飾其侵害行為,披露的財務信息可能失真。第二,加強監督管理層的自利行為。持股管理層對公司股價有很高的關注度,為使私人資產不縮水,在拋售股票前管理層會努力使股價維持在高位。合法手段無法將目標實現時,很可能會采取財務報告舞弊。第三,強化公司治理。首先,董事長與總經理不得由一人擔任。其次,在符合公司法規定的基礎上,公司應結合自身資產規模及不同發展階段來確定最佳董事會規模和獨立董事數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