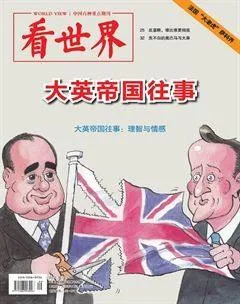古巴:窮人的幸福感
陳芬



提起古巴,你會想到什么?雪茄、朗姆酒、老爺車,還是格瓦拉?當然,如果恰巧你還是位文青的話,你也許還會提到何塞·馬蒂、阿隆索、海明威、古巴爵士還有那些殖民風格的建筑……
這片土地上孕育著天然的樂觀主義與幸福感。人們拿著出了名的低收入,卻有著不匹配的高幸福指數。這似乎在提醒世人:幸福指數與收入無關。
每家每月一瓶食用油
在趕走歐美殖民者后,菲德爾·卡斯特羅與他的好朋友切·格瓦拉經過不懈努力聯手推翻了國內親美的巴蒂斯塔政權,并于1961年成立了革命政府。好萊塢電影《教父2》里古巴的戲份即以這一事件為背景,一群野心勃勃的美國企業家的“發財夢”在古巴就此破滅。1962年,美國宣布對古巴實行經濟、金融與貿易封鎖,并實施禁運,物資匱乏的古巴不得不實行配給制度以作應對。作為古巴計劃經濟的一大特色,配給制度采取國家補貼的形式,以象征性價格向國民提供日常用品。
根據美國佛羅里達大學的調查研究,從1962年起,每個古巴家庭每月憑購物本供應的食品和日用品包括:一瓶食用油、一袋洗衣粉,每人每天80克面包,每月2.7公斤大米,雞蛋8個,黑豆900克,雞肉900克,白糖1.4公斤,咖啡65克,巧克力粉70克,此外還有肥皂、香皂、火柴各一盒,外加7歲以下兒童的少量奶粉。這些配給品物價比在市場或商店購買要便宜得多。比如,一塊香皂,憑本購買只需25分,去市場買則要5比索左右。自這一制度實行以來,政府的配給標準在不同時期也有一定程度的適時提升。正是得益于這一制度, 解決了數十年來古巴人的基本溫飽問題。
然而,古巴作為一個加勒比島國,自身物資非常匱乏,80%的糧食和食品依賴進口,因此政府每年要掏出15億-18億美元的補貼,這不能不說是一筆沉重的財政負擔。美國長年的經濟封鎖與阻撓,外加1990年代的東歐劇變與蘇聯解體使得古巴失去了來自社會主義國家盟友與伙伴的援助,古巴陷入了經濟困境,國內實行的配給制度讓政府財政入不敷出,配給弊端日益凸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國際糧食價格大幅上漲更是讓古巴的這一境況雪上加霜。“窮則思變”,對于古巴來說,一場經濟領域的變革似乎是勢在必行,而這一變革的發起人便是菲德爾·卡斯特羅的弟弟——勞爾·卡斯特羅。
“大豆和大炮一樣重要”
“頭發灰白、留著小胡子、戴著金絲邊兒眼鏡,作風務實、低調謹慎、平易近人”,這是公眾給他貼的標簽。同兄長一樣,在古巴,他在民眾心目中也享有極高的威望。
2006年7月,勞爾從兄長老卡斯特羅的手中接過國家權力重任,成為古巴新一任國家領導人。國際媒體對他的評價是“政治上跟兄長一樣強硬,經濟上則比老卡有彈性”。
經濟學專業背景出身的勞爾早在上世紀90年代就發出過感慨“大豆和大炮一樣重要,甚至更加重要”。上任之后的勞爾推行了一系列“獲取大豆”的改革措施,并進一步積極推動了一場“更新生產模式”的經濟變革。
2006年,政府允許民眾用可兌換比索購買彩電、電腦等電器,這一初期的改革措施只專注于一個面,還比較零散。
2011年的4月,古巴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大會通過了《古巴社會經濟政策指導綱要》,正式拉開了古巴經濟全面“更新”的序幕。有中國媒體將這次會議形象地稱之為“古巴的第十一屆三中全會”。
對于一向在“從搖籃到墳墓”福利制度庇護下的古巴人來說,要適應政府的經濟變革模式,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然給,配給制令政府負擔過重,同時又不能激發民眾的積極性,外界評論這一體制是“養懶人”,改變這一體制似乎刻不容緩。不過,古巴民眾對于取消生活必需品配給制的反對聲非常高,因此政府選擇性地先取消了幾種生活用品的配給作為過渡。
平均工資約20美元
2011年1月,不堪重負的古巴政府開始陸續取消一些生活用品的配給,牙膏、香煙等非必需品政府已不負責供應,完全由市場提供。大米、雞蛋等基本食品依然由政府低價供應。如果想多買,民眾可以去自由市場,只是價格要高出2-3倍。
政府取消配給,民眾生活成本上升,但收入并沒有增加,結果自然是生活壓力陡增。
自1994年古巴開始實行貨幣雙軌制以來,古巴國內就一直流通著兩套貨幣。一套是古巴比索(簡稱CUP,1美元約合25比索),這是普通古巴人領取工資、生活消費使用的主要貨幣,而發行于1995年的可兌換比索(簡稱CUC,1美元約合1比索) 是外國人在古巴消費的主要貨幣。古巴人平均工資在20美元左右,約500古巴比索。如今,一塊普通的肥皂要6比索,一管牙膏也要8比索。工資低,生活成本高,滿足基本生活已不容易,更別說能負擔得起其他的消費了。筆者去年7月在古巴旅游時,光是在酒吧喝杯莫西多(Mojito,古巴有名的雞尾酒,由朗姆酒、檸檬、薄荷以及蘇打水調制而成)要花費10個可兌換比索(約10美元)。因此,低工資的古巴人對于物價的波動十分敏感。
拮據的生活迫使一些人走上街頭,將饑渴的目光投向外來游客的身上。古巴的街頭,常常游走著一群上了年紀的艷妝街女,她們濃妝艷抹,身穿艷麗長裙,頭戴配有大紅花的絲巾,通過吸引游客與其合照以索取小費。有時候,你也會遇到幾個上了年紀的婦人,她們走在街上四處乞討,要錢或者要一些生活用品。在參觀古巴的一家煙草種植園時,筆者親眼見到一個智利女人在買雪茄時快速地將一盒普通的化妝品塞給了女售貨員,女售貨員輕快地接了過去給了她更多的雪茄。超低的收入,匱乏的物資,日漸增加的生活成本,普通古巴人的生活大多已經越來越窘迫。
出租車司機通多國語言
Manuel是古巴一名普通的出租車司機,約莫三十歲的樣子,跟其他古巴人一樣,樂觀開朗,幽默健談。筆者一到古巴走出何塞·馬蒂機場就上了他的出租車,剛上車,他扭過頭操著一口流利的英語問我想用什么語言交流,英語、西班牙語、法語、意大利語還是葡萄牙語?筆者驚訝不已,問他這些語言他是否都會,在得到他肯定的答復后,心生佩服之余,更多的是好奇:一個會多國語言的人才怎么會做出租車司機呢?難道是因為高工資?于是,一路上,筆者索性跟他聊了起來,當他告訴我他每月的工資只有25美元時,我簡直不敢相信。原來古巴的出租車分國營和私人兩種,國營出租車主要針對外國游客,價格不菲;私人出租車車費不貴,往往是古巴人的選擇,只是車子比較破敗,且沒有空調。Manuel是國營出租車司機,只有基本工資,沒有外快,收入跟私人出租車司機沒法比。endprint
“為什么不買輛車自己干呢?”我急切地問道,“買車?太貴啦!起碼要好幾千美元呢,我根本沒錢買!以前不能買,現在可以買了,可是這對于我又有什么差別呢?”他無奈中帶著調侃的語氣回答我。實際上,古巴政府也是到2011年9月才頒布法令,允許私人自由買賣汽車的。
Mario夫婦是筆者在古巴租住的家庭旅館的主人。除了在哈瓦那市區的這旅館外,他們還在郊區有一套房子。看得出來,他們在古巴算是富裕家庭了,不但有兩處房產,而且家里還有電腦、電視機、電壓力鍋等家用電器。妻子Rosana告訴我,他們能過上還不錯的生活得益于政府的經濟政策。原來,Rosana是一名教師,Mario曾在政府工作。雖工作都還體面,但兩人工資都不高。兩人結婚9年,有2個孩子,都在上小學。2011年,政府為了精簡機構,進行了大裁員,而Mario就是那不幸的被裁員的一分子。家里頓時失去了一半的經濟來源,陷入了困境。為了減輕家庭負擔,兩人把政府分配的房子騰挪出一兩間來做私人旅館,主要針對外國游客。同時,憑借著曾在政府旅游部門的工作經驗,Mario很快找到了一份導游的工作,這在古巴算是一份收入相當不錯的工作。很快,日子便有了起色,家庭收入不斷增多,不但添置了家電,還在政府解禁私人房產買賣后于去年購置了位于郊區的那套房子。
相比之下,Rosana告訴我,她的表姐就沒有那么幸運了。同樣從政府部門被裁員的她,至今也還沒找到工作,除了政府的基本配給外,沒什么收入來源,家里一貧如洗。
2010年9月,古巴政府決定在5年之內從政府和國營企業中裁員100萬人,這在總人口1100萬的古巴曾引發軒然大波。不久,政府出臺了相應的配套政策,放開對178種私營經濟的限制,鼓勵下崗的政府和國有企業員工從事個體戶、自主創業。政府或國有企業職工在下崗后的第一年,可以享受到國家支付的這一年的工資,但此后政府就概不負責了。
這意味著下崗后的國有機構人員如有一技之長,則可選擇從事個體戶;而沒有一技之長的,如Rosana的表姐,在下崗一年后,將面臨困頓的境遇。
要繼續幸福下去
2014年1月,第二屆拉美加勒比共同體(CELAC)峰會在古巴哈瓦那舉行。峰會宣布建立拉美和加勒比國家共同體和平區,古巴向世界展示了其正逐步擺脫國際孤立的步伐。
今年7月15日,中國、俄羅斯、印度、巴西、南非等金磚五國領導人在巴西發表《福塔萊薩宣言》,成立了金磚國家開發銀行,首要解決的是新興市場與發展中國家開發性資金錯配的問題。過去,因為美國的原因,古巴一直被排斥在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門外,無法得到其提供的貸款。此次金磚國家開發銀行的成立對于古巴日后的貸款與融資或許是一個利好消息。
只是,有了“大豆”的古巴還會繼續幸福下去嗎?
那位快樂的出租車司機Manuel跟我說,他很喜歡他的工作,跟其他人相比,環境不錯,還有空調,在古巴工資也不算最低。他已經很幸福了。
今年1月8日起,古巴實施出租車管理新規,古巴出租車公司的司機可以與公司簽訂承包合同,由國企員工變為個體經營者。Manuel或許跟以前一樣,還是一個國營出租車司機,或許他已經成為了承包國營出租車的個體經營者,又或許他現在已經能買上一輛老爺車成為開私人出租車的個體經營者呢。他應該還是幸福的吧?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