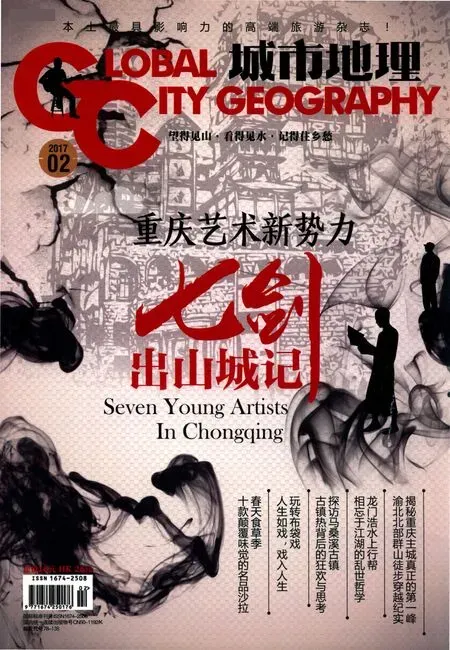張之洞的工業帝國從漢陽鐵廠到重鋼的百年興衰
文+陳石 陳超圖+寒溪夜浣 文梓光
英文導讀: It tells us about a brief hitory of Chongqing Iron and Steel Plant and stories about Chang Chih-tung.
一百多年前,長江邊上的大渡口還只是一處了無人煙的荒地。那時,沒有誰會想到,在日后這里會成為一段輝煌的工業史的見證者。從漢陽鐵廠到重鋼,百年的興衰演變就像一部跌宕起伏的大戲,直到現在,依然還會有人對當年的重鋼老廠區的場景津津樂道——
重鋼曾是那么紅火,就算是到了夜晚,晝夜不停的爐子也能把整個天際映得紫紅;重鋼曾是那么忙碌,一列列的小火車滿載煤炭呼嘯而過;重鋼曾是那么時尚,第一架手扶電梯,還有氣勢恢宏的電影院……
締造這一切的背后藏著一個人,他的名字叫:張之洞!

右頁圖:當時重慶的報紙常常刊登亞洲火油公司的各式廣告。All kinds of advertisement about Asia oil companies were often been printed in newspapers

一個時代的終結
2011年8月22日,大渡口香港城附近的一家江湖菜餐館人聲鼎沸,3張圓桌坐滿了近30位身著藍色制服的工人。大號啤酒杯被不斷裝滿,桌上的火爆鱔段、辣子肥腸冒著辣油油的香氣。煙霧中,一位工友將啤酒杯舉起,“來,為了120年,碰一杯!”,眾人舉杯,揮手回應,“干嘍!”
此刻,在與菜館一街之隔的廠區,重鋼股份有限公司型鋼廠棒材車間內,最后一根棒材經過加熱爐,穿過粗軋線、中軋線最終傳送到了冷床。整個過程持續了短短40秒,建廠120年的重鋼大渡口老廠區生產隨之關停。
那一刻,有人拍手歡呼,有人笑著流淚,有人哭到哽噎。這是開始,也是離別。大渡口,這個從1938年就與重鋼相依成長的地方,一半以上人口都是“重鋼人”,另一半人口或多或少都與重鋼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重鋼的外遷,宣布了大渡口一個時代的終結。
重鋼股份有限公司前身是1890年洋務運動時期創辦的漢陽鐵廠,它是中國最早的現代鋼鐵廠,也是亞洲最早最大的現代鋼鐵企業,其產品行銷美國、澳大利亞及南洋各國,被西方稱為“東亞雄廠”。1938年,重鋼從武漢西遷至重慶大渡口,73年后,重鋼完成至長壽新區的全部搬遷,老廠區將轉身成為集酒店、高檔寫字樓、住宅開發為一體的濱江商務居住區。
一代名臣張之洞
說到重鋼,繞不開的一個人便是張之洞。這位晚清名臣字孝達,號香濤,晚年自號抱冰老人。他祖籍在直隸南皮(今河北南皮),1837年9月12日出生于貴州興義府。張之洞博聞強識,文才出眾,年方十一歲,就為貴州全省學童之冠,作《半山亭記》,名噪一時。咸豐三年(公元1853年),他在直隸南皮應順天鄉試,名列榜首。同治六年,考取進士。后歷任翰林院編修、教習、侍讀、侍講學士及內閣學士等職。

張之洞處事果絕,人情練達,自然是官運亨通。先任山西巡撫,后又調任湖廣總督,成為封疆大臣。那時候,江南人愛自夸江南地杰人靈,多山多水多秀才,有些瞧不起北方人。每當北方人到南方作官,他們總要想方設法出點難題,將他作弄一番。
說是有一年夏天,張之洞到江南某城巡察。當地大小官員出城迎接。這天正值五月十三關帝廟會,城里非常熱鬧,看戲的人擠滿了廟院。張之洞也被請了過來,剛坐下還未來得及喝水,會首就來跪稟:“列位大人,臺上還沒貼對聯,請張總爺快寫一副吧!貼上好開戲啊。”說著把早已準備好的文房四寶端了上來,并把裁好折好限定字數的紅紙放下,要求上下聯各為十二個字。他們想給張之洞來個措手不及的考試。這時,在場的文武官員和文人學士,一個個搖頭晃腦,傲氣十足。張之洞早就料到他們會有這一手,胸有成竹地拿起筆來,用目光掃了他們一眼,“唰唰唰”一揮而就。這副對聯是:匹馬斬顏良,河北英雄齊喪膽;單刀會魯肅,江南名士盡低頭。
這副對聯,通過歌頌關公的英雄氣慨,巧妙地回敬了那些盛氣凌人的大小官員和文人學士。在場的人都被張之洞的才華和魄力驚呆了,個個點頭稱贊,再不敢小看他了。
亞洲最大的鋼鐵之城
提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張之洞,一生創辦了各種洋務。而辦鋼鐵,就是其眾多貢獻中最突出的一點。當時海軍衙門奏請修筑京通鐵路,臺諫官員因循守舊,紛紛陳述鐵路之害,請求停辦。面對眾口一致的反對,張之洞則舉雙手贊成:“修路之利,應以疏通各地物產、造福百姓生活為最重要,征兵運餉次之。現在應該從京城外的盧溝橋開始,經河南到達湖北漢口鎮。這是干線樞紐,中國大利聚集之地。一旦黃河以北鐵路建成,三晉的道路就可以和井陘聯接,關中甘肅的車馬貨物就可以聚集到洛口。自黃河以南,向東聯接安徽、江蘇,向南接通湖北、四川,萬里之外的音訊消息,短時間內便可通達。”


下頁圖:作為洋務運動的中流砥柱,一開始,漢陽鐵廠的主要職責就是生產軍事裝備。As the mainstay of the westernization movement,the main duty of Hanyang iron works is to product military equipment.
一邊力挺鐵路修建,張之洞一邊上書朝廷,陳述其七大有利之處:“鐵路處于腹心內地,不擔心會引敵而入,是第一利;鐵路所經之處原野廣闊,容易避開墳地房屋,是第二利;鐵路沿線工廠多車站多,做工和經商的人可以舍棄舊行當,得到新生計,這是第三利;以一條鐵路帶動八九個省份的交通主道,商人貨物集中,足可以充裕糧餉的來源,這是第四利;京師附近有意外事變,安徽、湖北精兵一個早晨便可聚集,這是第五利;太原富產鐵煤,如果運輸便利,則開采必然就多,這是第六利;如果海上有戰爭,向京城運糧的依然可暢通無阻,這是第七利。有這七利,分段分年來修筑便可建成。”上書進諫得到了皇帝的圣旨批復同意,于是有了把張之洞調往湖北的任命。
1889年,張之洞調任湖廣總督后,便主持興建湖北漢陽鐵廠、大冶鐵礦、湖北織布局等大型企業。其中最著名的,便是湖北漢陽鐵廠。在那時,漢陽鐵廠是一個牽動著國家命運的鋼鐵引擎。鑄鐵廠、打鐵廠、機器廠、造鋼軌廠和煉熟鐵廠等林林總總的廠房,與包容其間的3000名工人和40名外國技師一起,形成了一個亞洲最大的鋼鐵之城。
“昔頓乾坤,締造先從江漢始”,身為湖廣總督的張之洞在這里傾注了一生的主要精力。一位國外觀察家對當時漢陽鐵廠的描述是:“煙囪凸起,矗立云霄;化鐵爐之雄杰,輾軌機之森嚴,汽聲隆隆,錘聲丁丁,觸于眼簾、轟于耳鼓者,是為二十世紀中國之雄廠耶!”
從武漢到重慶的鋼鐵長征
漢陽鐵廠鋼水翻騰了50年,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后,抗日戰爭全面爆發,由于東北、華北等地鋼鐵廠相繼陷落,出海口也被日軍封鎖,進口困難,鋼材、生鐵奇缺,國民政府準備西遷重慶。1938年2月7日,蔣介石下達手令:“漢陽鐵廠應擇要遷移,并限三月底遷移完畢為要。”

3月1日鋼遷會成立,漢陽鐵廠的拆遷從一開始就遭遇到很多困難。由于漢陽鐵廠已停工十多年,大部分機器爐座都已經陳舊甚至被腐蝕,零件缺損問題尤其突出。更為嚴峻的現實是:漢陽鐵廠的機械設備都是進口的,安裝時都是外國工程師一手完成的,少數參與此項工作的中國人也已經找不到了。南京陷落后,日軍逼近九江。1938年4~7月間,拆遷中的漢陽鐵廠遭到日軍轟炸,工人死傷慘重,煉鐵爐、煉鋼爐、動力機件不同程度受損。工作人員冒著被日機轟炸的危險,隨炸隨修,日夜不停,一直堅持到10月21日武漢撤守前夕,鋼遷會共從漢陽鐵廠拆遷機器、材料約3萬噸,其中包括200噸高爐一座、30噸平爐兩座。
鋼遷會經多方考察,決定利用重慶及周邊地區豐厚的煤鐵儲量與便利的水上運輸,將新廠址設立于距離重慶上游約20公里的大渡口地區,以求戰時兵工鋼鐵材料的自給自足。但日軍仍盯著鋼廠不放,1938年2月至1943年8月,日本對戰時陪都重慶進行了長達5年半的戰略轟炸,新建的鋼廠成為日軍轟炸的重要目標。有一段時間,敵機連續好幾天對大渡口輪番轟炸,從早到晚空襲不斷。但因為巧妙偽裝,煉鐵、煉鋼的高爐和平爐,卻神奇地從未熄火停產。當時工人一邊安裝設備,一邊生產,一邊還得躲避日機轟炸。

左右頁圖:火車,作為工業的引擎,是重鋼百年歷史的見證。These train is the witnessing of the one hundred years history of Chongqing iron works.

這座鋼廠(重鋼前身)建成后鼎盛時期有員工15699人,是抗戰時期后方最大的鋼鐵聯合企業,最多時占全國鋼鐵產量的90%,被贊譽為“國之楨干”、“現代工業此其始基”。
一場嶄新的涅槃之旅
新中國成立后,張之洞的這份“骨血“在重慶愈發壯大,由漢陽鐵廠演變而來的重鋼在中國的鋼鐵版圖上越來越重要,擁有了“北有鞍鋼,南有重鋼”的贊譽。引以自豪的是,新中國的第一根鋼軌便是在重鋼軋出,鋪就在新中國的第一條鐵路— —成渝鐵路上。
到了上世紀60年代至70年代,重鋼成為“全國十大鋼廠”,大渡口因重鋼而建區,被稱為“十里鋼城”。重鋼也從此被視作重慶工業的一面旗幟,一個符號,一個寄托。對于生活在大渡口區的人來說,重鋼是那么的大,整個大渡口區,城即是廠,廠即是城,所有的街道、商店、學校甚至一個很不起眼的小門面,都能和鋼廠掛上關系;重鋼是那么紅火,就算是到了夜晚,晝夜不停的爐子也能把整個天際映得紫紅;重鋼總是那么忙碌,一列列的小火車滿載煤炭呼嘯而過;重鋼總是那么時尚,第一個手扶電梯,還有那氣勢恢宏的電影院……


若干年過去了,隨著城市的發展,已扎根大渡口73年的百年重鋼,也走上了首鋼的道路,戀戀不舍的離開了見證它成長的重慶主城區。曾經熱鬧的廠區變得空空落落,周圍的鬧市也隨著廠區和幾萬工人的離去而成為了孤獨的廢都;曾經沸騰火紅的廠房,最后一批或是等待搬遷或是等待廢棄的器械四處凋零;曾經傲氣十足的火車頭扎堆的擠在一起,就像沒有家的浪者相互偎依;曾經豪情萬丈的最后一批工人邊裝載著拆下來的器件邊黯然淚下。
李子林、石槽門、中山堂、丁家埡口這些熱鬧非凡的集市現在都荒無人煙了,駛過的公交車空空蕩蕩,曾經必須靠擠才能上車的時代早已一去不回。從張之洞初創漢陽鐵廠到重鋼搬遷,這個鋼鐵王國120年的艱辛與輝煌都已結束,擺在它面前的,將是一場嶄新的涅槃之旅。
- 城市地理的其它文章
- 東珠多杰帶著和尚玩音樂的居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