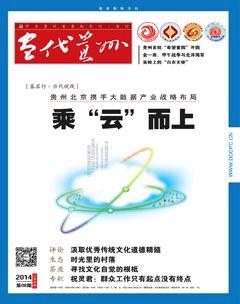土地文明中的倫理信仰
于丹,著名文化學者,北京師范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首都文化創新與文化傳播工程研究院院長、北京師范大學藝術與傳媒學院副院長;著名電視策劃人;國務院參事室特約研究員;古典文化的普及傳播者。
今天的中國處在城鄉一體化的進程中,我們會迅速地擁有都市的高樓大廈,但是中華民族的規矩與最早的倫理信仰,都潛藏在我們的土地之中。
文明的起源有不同源頭,既有高寒草原過來的游牧文明,也有河套上成長起來的農耕文明,還有臨海、海岸或島嶼上生成的商業文明。中華文明既有北方的游牧文明,也有南方圩田的文明,還有茶的文明以及蠶絲的文明,各式各樣的文明都并生于大地。農耕文明不光供給了我們口糧,還供給了一種哲學思想,這種哲學思想就是人以大地作為一切法則的開端。
《禮記》上有這樣一句話:“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于地,取法于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也就是說,大地上承載著萬物的生長。取財于地,人類從大地上取得財物、財寶沒有問題,大地愿意供養它的兒女,但是同時,要知道取法于天,蒼天的法則是制約大地的,要取用合時取用有度,如果毫無節制到坐吃山空,狂妄到趕盡殺絕,大地很快就沒法供養它的持續生長了。
“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農耕文明的因地制宜就是任何一種土地都有適合它的一種生命可以存在,這才是真正的包容。
記得在西方講學的時候,有記者問我:“我們也過節你們也過節,你能簡單說說這個節日有什么區別嗎?”我跟他們開玩笑說:“你看你們的節日絕大多數是從天上下來的,我們的節日絕大多數都是從地里長出來的。”因為西方過圣誕節、感恩節和復活節,這些都是個體的人在向神靈致敬,是人向天空膜拜。而華人的節日與節氣是合一的,在二十四節氣里向大地回歸和致敬。例如,清明是一個節氣,因為它需要種瓜、種豆,農民在這個時候不能耽誤農時;清明又是一個節日,因為它慎終追遠,向自己的祖先和值得尊敬的先賢獻上心中的敬意。
我們應該對土地文明抱著一點信念,因為這里面有祖先沉淀在我們基因里的安全感,這是一份向大地學規矩的謙恭和信任。人向大地回歸,給予大地這份信任,大地一定會還給你承諾。
從哲學上來看,農耕文明是中華哲學真正的發軔。它講相生,講相克,講萬物的和諧。這其中,第一應該順應天時,第二應該因地制宜,第三要天人合一。
順應天時、因地制宜、天人合一這三個詞就是中華哲學,這也是中華文明的天地人三才。順應天時是節序;因地制宜是在不同的條件下找到最好的生長可能;而天人合一是人在天地之中,終于找到了自我的坐標,也找到了一個華人頂天立地的尊嚴。
今天我們向西方學到的經驗很多,學制度改革也不少,有許多人出去留學,帶回來的經驗系統固然都好。但是,如果沒有了農耕文明的思維,那將是“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只有基于對土地的信任,人法地、地法天,之后才能夠找到道法自然,即最后的華人共識。
2011年的歲末,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在自己的連任宣言中用《老子》第八十一章,也就是整部《道德經》的最后一句話,給了這個后工業文明時代一個建議,他說:“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為而不爭。”就是說蒼天最基本的道理,應該是有利于萬物生長而不制造禍害,人間最基本的道理是“為而不爭”,每一個人都發憤圖強有所作為而不勾心斗角與別人紛爭。今天看天道,可能自然災害不少,而人間彼此的紛爭就更多,怎么樣才能做到天道與人道都合乎古訓常理,其實這才是我們真正應該思考的問題。
未來,我們會向國際學習更多,但不能丟棄自己土地里的文明。“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兇”,我們應該抱有“尊天親地”的樸素情懷,有山水之樂,學習仁智品德,才可以靜下心來在自己的節氣和節令中喚醒民族的禮儀。
我們應該從眼前做起,可以讓老者安之,可以讓朋友信之,可以讓少者懷之,在倫理之中完成人生的安頓,找到最代表中華文明以及最民族化的起點。(責任編輯/吳文仙)
于丹,著名文化學者,北京師范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首都文化創新與文化傳播工程研究院院長、北京師范大學藝術與傳媒學院副院長;著名電視策劃人;國務院參事室特約研究員;古典文化的普及傳播者。
今天的中國處在城鄉一體化的進程中,我們會迅速地擁有都市的高樓大廈,但是中華民族的規矩與最早的倫理信仰,都潛藏在我們的土地之中。
文明的起源有不同源頭,既有高寒草原過來的游牧文明,也有河套上成長起來的農耕文明,還有臨海、海岸或島嶼上生成的商業文明。中華文明既有北方的游牧文明,也有南方圩田的文明,還有茶的文明以及蠶絲的文明,各式各樣的文明都并生于大地。農耕文明不光供給了我們口糧,還供給了一種哲學思想,這種哲學思想就是人以大地作為一切法則的開端。
《禮記》上有這樣一句話:“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于地,取法于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也就是說,大地上承載著萬物的生長。取財于地,人類從大地上取得財物、財寶沒有問題,大地愿意供養它的兒女,但是同時,要知道取法于天,蒼天的法則是制約大地的,要取用合時取用有度,如果毫無節制到坐吃山空,狂妄到趕盡殺絕,大地很快就沒法供養它的持續生長了。
“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農耕文明的因地制宜就是任何一種土地都有適合它的一種生命可以存在,這才是真正的包容。
記得在西方講學的時候,有記者問我:“我們也過節你們也過節,你能簡單說說這個節日有什么區別嗎?”我跟他們開玩笑說:“你看你們的節日絕大多數是從天上下來的,我們的節日絕大多數都是從地里長出來的。”因為西方過圣誕節、感恩節和復活節,這些都是個體的人在向神靈致敬,是人向天空膜拜。而華人的節日與節氣是合一的,在二十四節氣里向大地回歸和致敬。例如,清明是一個節氣,因為它需要種瓜、種豆,農民在這個時候不能耽誤農時;清明又是一個節日,因為它慎終追遠,向自己的祖先和值得尊敬的先賢獻上心中的敬意。
我們應該對土地文明抱著一點信念,因為這里面有祖先沉淀在我們基因里的安全感,這是一份向大地學規矩的謙恭和信任。人向大地回歸,給予大地這份信任,大地一定會還給你承諾。
從哲學上來看,農耕文明是中華哲學真正的發軔。它講相生,講相克,講萬物的和諧。這其中,第一應該順應天時,第二應該因地制宜,第三要天人合一。
順應天時、因地制宜、天人合一這三個詞就是中華哲學,這也是中華文明的天地人三才。順應天時是節序;因地制宜是在不同的條件下找到最好的生長可能;而天人合一是人在天地之中,終于找到了自我的坐標,也找到了一個華人頂天立地的尊嚴。
今天我們向西方學到的經驗很多,學制度改革也不少,有許多人出去留學,帶回來的經驗系統固然都好。但是,如果沒有了農耕文明的思維,那將是“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只有基于對土地的信任,人法地、地法天,之后才能夠找到道法自然,即最后的華人共識。
2011年的歲末,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在自己的連任宣言中用《老子》第八十一章,也就是整部《道德經》的最后一句話,給了這個后工業文明時代一個建議,他說:“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為而不爭。”就是說蒼天最基本的道理,應該是有利于萬物生長而不制造禍害,人間最基本的道理是“為而不爭”,每一個人都發憤圖強有所作為而不勾心斗角與別人紛爭。今天看天道,可能自然災害不少,而人間彼此的紛爭就更多,怎么樣才能做到天道與人道都合乎古訓常理,其實這才是我們真正應該思考的問題。
未來,我們會向國際學習更多,但不能丟棄自己土地里的文明。“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兇”,我們應該抱有“尊天親地”的樸素情懷,有山水之樂,學習仁智品德,才可以靜下心來在自己的節氣和節令中喚醒民族的禮儀。
我們應該從眼前做起,可以讓老者安之,可以讓朋友信之,可以讓少者懷之,在倫理之中完成人生的安頓,找到最代表中華文明以及最民族化的起點。(責任編輯/吳文仙)
于丹,著名文化學者,北京師范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首都文化創新與文化傳播工程研究院院長、北京師范大學藝術與傳媒學院副院長;著名電視策劃人;國務院參事室特約研究員;古典文化的普及傳播者。
今天的中國處在城鄉一體化的進程中,我們會迅速地擁有都市的高樓大廈,但是中華民族的規矩與最早的倫理信仰,都潛藏在我們的土地之中。
文明的起源有不同源頭,既有高寒草原過來的游牧文明,也有河套上成長起來的農耕文明,還有臨海、海岸或島嶼上生成的商業文明。中華文明既有北方的游牧文明,也有南方圩田的文明,還有茶的文明以及蠶絲的文明,各式各樣的文明都并生于大地。農耕文明不光供給了我們口糧,還供給了一種哲學思想,這種哲學思想就是人以大地作為一切法則的開端。
《禮記》上有這樣一句話:“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于地,取法于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也就是說,大地上承載著萬物的生長。取財于地,人類從大地上取得財物、財寶沒有問題,大地愿意供養它的兒女,但是同時,要知道取法于天,蒼天的法則是制約大地的,要取用合時取用有度,如果毫無節制到坐吃山空,狂妄到趕盡殺絕,大地很快就沒法供養它的持續生長了。
“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農耕文明的因地制宜就是任何一種土地都有適合它的一種生命可以存在,這才是真正的包容。
記得在西方講學的時候,有記者問我:“我們也過節你們也過節,你能簡單說說這個節日有什么區別嗎?”我跟他們開玩笑說:“你看你們的節日絕大多數是從天上下來的,我們的節日絕大多數都是從地里長出來的。”因為西方過圣誕節、感恩節和復活節,這些都是個體的人在向神靈致敬,是人向天空膜拜。而華人的節日與節氣是合一的,在二十四節氣里向大地回歸和致敬。例如,清明是一個節氣,因為它需要種瓜、種豆,農民在這個時候不能耽誤農時;清明又是一個節日,因為它慎終追遠,向自己的祖先和值得尊敬的先賢獻上心中的敬意。
我們應該對土地文明抱著一點信念,因為這里面有祖先沉淀在我們基因里的安全感,這是一份向大地學規矩的謙恭和信任。人向大地回歸,給予大地這份信任,大地一定會還給你承諾。
從哲學上來看,農耕文明是中華哲學真正的發軔。它講相生,講相克,講萬物的和諧。這其中,第一應該順應天時,第二應該因地制宜,第三要天人合一。
順應天時、因地制宜、天人合一這三個詞就是中華哲學,這也是中華文明的天地人三才。順應天時是節序;因地制宜是在不同的條件下找到最好的生長可能;而天人合一是人在天地之中,終于找到了自我的坐標,也找到了一個華人頂天立地的尊嚴。
今天我們向西方學到的經驗很多,學制度改革也不少,有許多人出去留學,帶回來的經驗系統固然都好。但是,如果沒有了農耕文明的思維,那將是“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只有基于對土地的信任,人法地、地法天,之后才能夠找到道法自然,即最后的華人共識。
2011年的歲末,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在自己的連任宣言中用《老子》第八十一章,也就是整部《道德經》的最后一句話,給了這個后工業文明時代一個建議,他說:“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為而不爭。”就是說蒼天最基本的道理,應該是有利于萬物生長而不制造禍害,人間最基本的道理是“為而不爭”,每一個人都發憤圖強有所作為而不勾心斗角與別人紛爭。今天看天道,可能自然災害不少,而人間彼此的紛爭就更多,怎么樣才能做到天道與人道都合乎古訓常理,其實這才是我們真正應該思考的問題。
未來,我們會向國際學習更多,但不能丟棄自己土地里的文明。“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兇”,我們應該抱有“尊天親地”的樸素情懷,有山水之樂,學習仁智品德,才可以靜下心來在自己的節氣和節令中喚醒民族的禮儀。
我們應該從眼前做起,可以讓老者安之,可以讓朋友信之,可以讓少者懷之,在倫理之中完成人生的安頓,找到最代表中華文明以及最民族化的起點。(責任編輯/吳文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