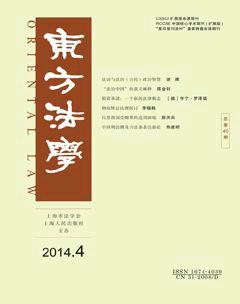虛假供述的第二道防線:口供實質補強規則
內容摘要:虛假供述一旦被采信,極有可能導致錯案。近年來,我國先后通過出臺專門的司法解釋和修改刑訴法,確立了一系列有關口供的證據規則。由于虛假供述形成原因的復雜性和虛假供述的多樣性,它們在整體上防范能力有限。以非法口供排除規則防止虛假供述在我國存在著現實困難和內在困境。同非法口供排除規則相比,以口供補強規則實質化作為突破口不僅具有理論根據、比較優勢,也具有現實根據。為切實防止虛假供述,必須要結合虛假供述的形成機制和真假供述的識別原理,參考其他國家的口供補強規則,分別從補強證據要求、待補強口供要求、補強對象和程度等方面使口供補強規則實質化。經過非法口供排除規則過濾后的任何口供,只有在特殊情節排除了誘供指供和案情泄露的前提下獲得的,并得到了具有證據能力、證明力的被告人供述以外的獨立證據或者新證據的印證,且供述中的犯罪客觀方面的特殊細節與證據所證明的事實基本吻合一致,才能作為證據使用。
關鍵詞:虛假供述排除規則口供實質補強規則
該文系作者主持的是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刑事錯案風險分配研究》(項目編號:12BFX059)和中國法學會2013年度部級法學研究課題《公訴案件無罪判決難問題研究》(項目編號:CLS2013C67)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據統計,我國犯罪嫌疑人在偵訊階段的自白率接近100%。〔1 〕我國每年一審被認定有罪的被告人的數量為100萬人左右。〔2 〕哪怕是千分之一的虛假口供被法院采信,由此導致的錯案數量也是驚人的。近年來,我國媒體披露了一些令人震驚的錯案,就證據制度而言,偵查階段的虛假口供成為法院定案根據,正是首要原因之一。〔3 〕我國目前已披露錯案中的虛假供述,通常與刑訊逼供有關,立法者在修改《刑事訴訟法》時,把防止刑訊逼供放在了重中之重的位置,〔4 〕同時通過非法口供絕對排除規則否定刑訊逼供所得供述的證據能力,以排除侵犯基本人權和可能不真實的口供。有關司法解釋還進一步擴大了非法口供絕對排除規則的適用范圍,并確立了瑕疵口供相對排除規則以及翻供印證規則。
那么虛假供述到底是如何形成的?遏制了刑訊逼供行為,是否就能夠有效地防止虛假供述?我國當前所確立的各種有關口供的證據規則,是否足以防止法院錯誤地采信虛假供述?如果它們還存在不足,我們該如何完善當前的口供證據規則?是否需要進一步擴大非法口供排除規則的范圍?如果擴大非法口供排除規則的可行性不大,又該采取其他什么措施呢?本文將嘗試依次解答上述問題。
一、虛假供述的形成機制
虛假供述是沒有實施犯罪的無辜公民所作出的“有罪供述”。一般來說,故意編造口供自陷于罪是違背人性的,中國當前發生的錯案證實,虛假口供幾乎都是偵查人員采用刑訊逼供等手段逼迫出來的。但是這個直觀的認識可能有失片面,而且可能產生誤導,使司法人員誤認為,在沒有刑訊等暴力手段的時候,所獲得的口供是“真實的”:一個沒有犯罪的人,在沒有被刑訊的情況下,怎么可能會承認給其帶來刑罰的犯罪?事實上,沒有刑訊,照樣可能產生虛假供述。虛假口供的形成,可能是由于偵訊的環境和方式所造成的,也可能是由于犯罪嫌疑人的個體因素所造成的,還可能是由于兩者綜合作用所造成的。
犯罪嫌疑人在接受偵訊時,一開始就承認有罪并不多見。〔5 〕為了打擊犯罪嫌疑人的自信,強化偵查人員的心理優勢,以達到“解除”心理防線的目的,世界上多數國家偵查機關都會設計出密閉、隔離的訊問環境,通過“空間壓迫”制造心理壓力。當普通人被拘禁在安靜及密閉的環境下,或者處在色彩、擺設及光線單調的環境中,因缺乏釋放內在壓力的刺激物,難以集中精神和進行清晰的思考,容易陷入焦慮狀態,并容易受到外部暗示的影響。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被剝奪后,進入一個陌生的密閉空間,對訊問時間的長短、過程及結果充滿不確定感,也會使犯罪嫌疑人壓力重重。甚至偵查人員所穿的衣著,都會令犯罪嫌疑人產生相當的壓力。正是由于上述這些因素,美國最高法院曾在米蘭達一案的判決書中寫道,即使沒有任何人為的壓迫,偵訊環境也具有“內在的壓力”。〔6 〕這種內在的壓力會導致部分嫌疑人處于一種無助、焦慮、挫折的狀態,容易屈從。
如果偵查人員采取威脅、利誘、欺騙等“偵訊謀略”,則可能進一步加大其中的壓力。無辜的犯罪嫌疑人為了擺脫當前的困境,可能會“理智地”選擇擺脫眼前痛苦,先迎合偵查人員的需要,承認犯罪,然后寄希望于沒有壓力的事后程序(如起訴、審判)否認自己的罪行。他們可能“天真地”認為,反正自己沒有實施犯罪,即使現在認罪,法官也不可能采信自己的供述而定罪。無辜的人對自己的供認有可能導致刑罰,并不具有任何“現實感”:不管怎樣,自己沒有做這一切,沒有做的人即使說自己做了,也不能據此處以刑罰。這是無辜犯罪嫌疑人自白時的真實心境。〔7 〕
例如,20世紀30年代以前,美國偵查人員曾經大量地使用刑訊等手段獲取口供。聯邦最高法院在此期間作出數份判決,宣告這種方式所獲得的口供應當絕對排除,迫使警察必須發展一些更為精細、專業的訊問技巧。美國學者萊德等人的著作《刑事偵訊與自白》,是美國警察局培訓警察訊問技巧的經典教材。萊德等人在書中使用的偵訊技術被稱為“萊德技巧”,對獲取口供非常管用。“萊德技巧”要求警察必須學會使用各種游走于法律邊緣的說服技巧,打消嫌疑人的抗拒心理,淡化自白可能帶來的不利后果,促使嫌疑人供述犯罪事實。例如,欺騙嫌疑人(宣稱在兇器上發現他的指紋)、黑臉白臉法(一個施加壓力另一個假裝同情)、維持注意力(將座位靠近嫌疑人,維持與嫌疑人的眼神接觸)、提出帶有誘導性質的問題(“這種事是你第一次這樣做,還是已經做過多次了?”)等等。美國學者研究發現,在沒有刑訊的條件下,運用“萊德技巧”進行訊問,無辜者可能受到這種具有高度影響力和說服力的偵訊技巧的影響,作出虛假自白。〔8 〕其中,最有可能導致虛假供述的訊問方法就是偵查人員有意無意地把犯罪事實透露給犯罪嫌疑人,然后制造壓力迫使犯罪嫌疑人“重述”警察透露的信息。此時,如果偵查人員是無意為之,可能連自己都不知道犯罪嫌疑人的供述是由自己“喂給”他的,而不是真正來自于犯罪嫌疑人的記憶。〔9 〕
不同的犯罪嫌疑人在面對同樣的偵訊環境和偵訊技巧時,反應可能并不一樣,這會受到個人因素的影響。這些個人因素包括人格特征、年齡、智力、精神健康狀況和接受訊問時的生理及心理狀態等。一般來說,所有上述個人因素或某個因素比較“脆弱”的人,更加可能會作出虛假自白。例如,未成年人在接受訊問過程中,比成年人更容易放棄自己所享有的權利,即使在成年人在場的情況下,也更容易作出自白。而有些沒有實施犯罪的人,可能精神上存在障礙,或者為了獲得某種利益,“主動”替別人頂罪,從而作出“自愿”而虛假的供述。
偵查人員普遍存在的片面偵查觀加劇了虛假口供的形成。所謂片面偵查觀,是指當偵查人員在偵查初期形成某人有罪的判斷后,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些能夠證實有罪的判斷上,忽視犯罪嫌疑人的無罪辯解或其他無罪證據,認為辯解是“狡辯”,更加堅定了偵查人員的有罪判斷。〔10 〕長期從事偵查工作的人員往往比較自信,認為自己能夠通過犯罪嫌疑人的語言、神態、動作等特征,判斷出嫌疑人到底是“真辯”還是“假辯”。只要他們根據自己的辦案經驗和先前收集的不充分的證據,認定犯罪嫌疑人是罪犯,犯罪嫌疑人很難說服偵查人員改變心意。一旦偵查人員形成錯誤的偵查假設,往往就會“將錯就錯”,他們所提的問題更側重于證實有罪的問題,也為強制性的偵訊提供了心理支撐,使嫌疑人承受更大的壓力,從而可能導致虛假的自白。〔11 〕
一般來說,偵查人員的片面觀是虛假自白形成的肇因,并且可能會增強偵訊手段的強制性,加上偵訊環境和偵訊技術的綜合影響所制造的強大壓力,無辜的犯罪嫌疑人,會選擇暫時性地順從偵查人員,進而可能作出虛假自白。絕大多數情形下的虛假口供都屬于這種“強迫屈從型”虛假供述。在一小部分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可能出于負罪感,加上記憶方面存在一定障礙,在偵查人員的逼迫和誘導下,可能誤以為自己是真正的罪犯,從而作出“強迫內化型”虛假供述。有時候,犯罪嫌疑人可能出于袒護他人的動機,供認犯罪事實,從而產生“自愿型”虛假供述。〔12 〕
二、防止虛假供述的證據規則的有限性
由于口供的證明力極強,虛假供述一旦被法院作為定案的根據,極有可能釀成錯案。同時,虛假供述的產生往往是訊問環境、訊問方法以及犯罪嫌疑人自身條件等多種因素單一或者綜合作用下的產物。因此,必須要認真地對待虛假供述問題,采取有效措施防止虛假供述被錯誤采信。首要的措施,當然就是通過否定虛假供述的定案資格,以口供證據規則作為防護板,阻止不可靠的供述轉化為定案的根據。根據我國2012年刑訴法及有關司法解釋的規定,目前我國有可能防止虛假供述成為定案根據的證據規則主要有以下四種:一是非法口供絕對排除規則;二是瑕疵口供相對排除規則;三是翻供印證規則;四是口供補強規則。那么它們是否足以防止不可靠的供述轉化為定案的根據呢?
(一)非法口供絕對排除規則
1.以“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為排除條件的絕對排除規則
為了遏制刑訊逼供,防止因采納非法手段獲得的口供而產生錯案,2010年《關于辦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下文簡稱為《非法證據排除規定》)規定采用刑訊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應當予以排除。2012年刑訴法,將其吸收在新法之中。刑訴法確立的非法口供排除規則,通過否定非法方法取得的口供的證據能力,把可能不真實的供述阻擋在心證大門之外,從而保障了事實認定的準確性,降低了無辜公民被錯誤定罪的可能性。
無論是《非法證據排除規定》,還是刑訴法,都把非法口供排除規則的適用范圍限定在采用“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獲得的供述。根據全國人大法工委的解釋,此處“等非法方法”是指“違法程度和對當事人的強迫程度達到與刑訊逼供相當,使其不得不違背自己意愿陳述的方法”。〔13 〕認定是否屬于“等非法方法”的標準包括兩個方面:一是“非法方法”在性質上與刑訊逼供相當;二是“非法方法”在程度上達到使人被迫供述的地步。一般認為,與刑訊逼供在性質上相當的方法是變相刑訊逼供行為,例如長期不讓睡覺、長時間不讓喝水等。當變相刑訊行為達到了迫使人不得不供認犯罪的程度,由此得到的口供應當予以排除。由此可見,我國目前確立的非法口供排除規則的外延是相當狹窄的,其有效射程僅及于刑訊逼供和一部分較為嚴重的變相刑訊行為。對于采用威脅、引誘、欺騙等非法方法取得的供述,并不在非法口供排除規則的排除范圍之內。〔14 〕從虛假供述的形成機制來看,采用威脅、引誘、欺騙等訊問方法也極有可能導致虛假口供。那么由此獲得的供述,到底在何種情形下不可以作為定案的根據,這就只能由法官自由裁量決定,而無規則可言。
不僅如此,非法口供排除規則并不直接否定受到刑訊逼供影響的其他供述的證據能力。自《非法證據排除規定》施行以來,令人欣慰的是,部分法院已經開始運用該規則解決口供的證據能力問題,有的法院將存在刑訊逼供可能性的口供直接予以排除。令人失望的是,關鍵性的口供被排除之后,法院最終還是認定被告人構成犯罪。〔15 〕其原因在于,被告人在偵查階段的供述通常并不止一份,法院排除其中的一份口供,還有多份關鍵性口供可資使用。實務部門把排除對象限定在采用“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獲得的“那一次”供述上。然而,其他供述由于非法取證行為的影響,也極有可能是虛假的。虛假供述的形成機制揭示,偵訊環境和偵訊方法所制造的持續性壓力,是迫使犯罪嫌疑人作出虛假供述的重要原因。而在司法實踐中,犯罪嫌疑人在偵查階段做出多份供述是一個普遍現象。〔16 〕對于在貌似“合法”手段下獲得但事實上可能是受刑訊逼供影響的口供,我們該如何規范,當前的規則也態度不明。
2.其他非法口供絕對排除規則
《關于辦理死刑案件審查判斷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下文簡稱為《死刑案件證據規定》)擴大了非法口供排除規則的適用范圍,增加了三種情形下的口供絕對排除規則:一是訊問筆錄沒有經被告人核對確認并簽名(蓋章)、捺指印的;二是訊問聾啞人,應當提供通曉聾、啞手勢的人員而未提供的;三是訊問不通曉當地通用語言、文字的人員,應當提供翻譯人員而未提供的。這三種情形下的證據排除規則,無疑也有利于防止虛假供述。在被告人已經簽名、捺指印的絕大多數普通案件中,由于缺乏有效規則的約束,司法人員在供述證據采信方面的裁量權無法得到約束,有可能有意無意地采納了不具有可靠性的供述,導致事實認定的錯誤。
(二)瑕疵口供相對排除規則
所謂瑕疵口供,是指獲取口供的偵訊程序存在輕微違法情節,從而使偵查階段供述的證據能力處于待定狀態的口供。根據《死刑案件證據規定》第21條的規定,下列偵訊筆錄屬于瑕疵口供:一是筆錄填寫的訊問時間、訊問人、記錄人、法定代理人等有誤或者存在矛盾的;二是訊問人沒有簽名的;三是首次訊問筆錄沒有記錄告知被訊問人訴訟權利內容的。瑕疵口供只有在不能通過補正或者合理解釋的手段彌補程序上的缺陷時,才會予以排除。因此,它是一個相對排除規則。同非法口供絕對排除規則相比,瑕疵口供相對排除規則不僅賦予了法院采納與否的裁量權,而且還授予了偵查機關進行補救的機會。
該規則對于防止虛假供述被采納定案根據的效果,也是非常有限的。瑕疵口供相對排除規則的適用條件采取的是明確列舉式規定,還有很多既不屬于絕對排除情形也不屬于相對排除情形的違法訊問所得供述的證據資格問題,依然處于“無法可依”的狀態。〔17 〕因此,當面對其他既不在絕對排除也不在相對排除情形下的“非法”或者“瑕疵”口供,到底依據什么標準,防止虛假供述被錯誤采納,沒有具體的規則。
就瑕疵口供本身的補正而言,該規則對于補正的范圍和方式未作限定,可能助長取證人員的弄虛作假行為,如倒推取證日期、虛構訊問人員人數或者見證人、提供關于訊問地點的不真實信息等,補正或者合理解釋后的口供真實性可能并無有效保障。〔18 〕此外,瑕疵證據相對排除規則只是著眼于訊問筆錄程序性瑕疵的補救,而不是其實質真實性的補救。換句話說,補正或解釋的只是供述的“形式”瑕疵,而不是口供“內容”本身。筆錄填寫的訊問時間、訊問人、記錄人、法定代理人是否有誤或者存在矛盾的,訊問人是否簽名,首次訊問筆錄是否記錄告知被訊問人訴訟權利內容的,與口供本身是否是真實的沒有什么必然的聯系。判斷口供是否是真實的,必須要從供述內容是否符合事實本身來判斷,而不是從形式上是否存在瑕疵來判斷。形式上沒有瑕疵的供述完全可能是虛假的。
(三)翻供印證規則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時供時翻,尤其是在庭審中推翻庭前供述,是困擾口供真實性認定的現實難題之一。《死刑案件證據規定》在總結我國司法實踐經驗的基礎上,確立了一個翻供時口供的采信規則。根據《死刑案件證據規定》第22條,對于翻供時口供的采信,可以分為兩種情況:一方面,如果被告人庭前供述一致,庭審中翻供,但被告人不能合理說明翻供理由或者其辯解與全案證據相矛盾,而庭前供述與其他證據能夠相互印證的,可以采信被告人庭前供述;另一方面,如果被告人庭前供述和辯解出現反復,但庭審中供認的,且庭審中的供述與其他證據能夠印證的,可以采信庭審中的供述,而被告人庭前供述和辯解出現反復,庭審中不供認,且無其他證據與庭前供述印證的,不能采信庭前供述。簡而言之,只要被告人的供述能夠與其他證據相互印證的,即使被告人在庭前時供時翻或者庭前供述一致但庭審中翻供的,法庭都可以“采信”庭前供述。如果供述與其他證據不能相互印證的,則不能把供述作為定案的根據。因此,該規則可以被稱為翻供印證規則。
翻供印證規則與前述非法口供排除規則不同的是,它是從供述的內容,而不是獲得供述的程序或者手續來規范供述的證據資格。翻供印證規則假設的前提是,得到其他證據佐證的供述,由于供述的內容與其他證據揭示的信息相互吻合一致,共同指向同一個結論,從而基本上可以排除口供的虛假性。
但是,如果只是考慮口供與其他證據是否印證,不考慮供述形成的環境以及印證證據的性質,可能因形式上的印證而導致采納不可靠的口供。在實踐中,稍有經驗的偵查人員都知道口供印證的重要性,都會想方設法使口供與其他證據表面上看起來一致。如果口供是在偵查人員強迫、威脅、引誘下獲得的,然后再“炮制”其他證據“印證”口供的細節,那么口供即使與其他證據是高度吻合的,也極有可能是虛假的。〔19 〕這將會導致在形式上達到“證據相互印證、形成完整證明體系”的案件完全可能是錯誤的。〔20 〕那么,到底什么樣的證據才能作為印證證據?供述本身應當要具備什么樣的基本要求才能夠作為印證的對象?印證到什么樣的程度,才能讓翻供后的供述具備定案資格?被告人沒有翻供的案件,采信被告人的供述是否也需要其他證據的印證?諸如此類的有關口供印證的核心問題,在翻供印證規則中都無法找到答案。從防止采納虛假供述的目標而言,翻供印證的規范思路是值得肯定的,但是由于它過于粗糙,所以不僅無法有效地控制事實認定者的裁量權,而且還可能帶來誤導性效應:不管供述本身是在什么情境下取得的,也不管印證證據的性質如何,只要供述得到其他證據印證,供述就是可采信的。這非但可能無法防止虛假供述被采納,反而可能使虛假供述獲得了一張名正言順的“通行證”。
(四)口供補強規則
1979年、1996年和2012年刑訴法均有這樣的規定:只有被告人供述,沒有其他證據的,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這是我國立法所確認的口供補強規則。口供補強規則表面上看似對法官自由評價供述證明力的限制,但事實上發揮著與證據能力規則相同的作用,阻止裁判者把沒有證據補強的口供作為定案的根據。
口供補強規則主要具有三個目的:一是防止采納沒有證據補強的不可靠口供;二是激勵偵查機關尋找其他證據;三是糾正裁判者不加批判地接受口供證據的傾向。因此,該規則的主要目的是為了擔保口供的真實性,這與建立在合法性基礎之上的非法口供排除規則目的并不完全一致,后者主要側重于對程序法治的保障。
我國目前的口供補強規則只是一個有關證據數量的規則。它要求除了口供以外,必須要有其他證據證明犯罪事實,可以視為“孤證不能定案”原理的基本要求。但是,它跟翻供印證規則一樣,并沒有告訴司法人員到底應當依據什么樣的標準補強口供,口供才能作為證據使用。在司法實踐中,沒有其他證據,只有被告人供述的案件幾乎是沒有的。〔21 〕偵查人員或多或少都會提供一些證據補強口供的真實性。如果只是簡單地要求口供需要證據補強,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根本不可能發揮過濾不可靠供述的作用。在我國目前的印證證明模式下,偵查人員都知道提供證據印證口供的重要性,可能有意無意地通過“披露”犯罪信息讓犯罪嫌疑人供述“隱蔽性”細節,有時候甚至直接帶領犯罪嫌疑人“指認”犯罪現場,更為嚴重的情形就是直接讓犯罪嫌疑人“背誦”或者“抄寫”警方或者特情已經制作好的“口供”。只要求口供有其他證據予以補強,沒有具體的補強標準,一般補強規則在防止虛假供述方面的作用同翻供印證規則一樣,其規范力度有限。
三、口供實質補強規則的正當性
就防止虛假供述而言,我國當前的口供證據規則可以概括為兩大類型:一類是以合法性作為標準的可采性規則;另一類是以真實性作為標準的可采性規則。非法口供絕對排除規則和瑕疵口供相對排除規則是直接否定特定類型的非法供述的可采性,翻供印證規則和口供補強規則是直接否定某些真實性存疑(沒有印證或者補強)的供述的可采性。但是,它們在防止虛假供述方面的整體能力存在不足。就非法口供排除規則而言,他們的排除范圍極其有限。大量的比較嚴重的違法偵查行為下獲得的供述,并不在非法口供排除規則的射程之內。翻供印證規則或者口供補強規則,并沒有對印證或補強的具體標準設定要求,實踐中難免流于恣意。我國目前所發生的諸多錯案,其中的口供至少在形式上與其他證據都是相互印證的。因此,目前有兩條道路可選:一是擴大非法口供排除規則的范圍;二是為口供采納設定一個最低限度的補強或者印證要求。
(一)擴大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難度和內在局限性
進一步擴大非法口供排除規則的范圍在當前可行性不大。非法口供排除規則的立法歷程,可以充分證明這一點。1979年、1996年刑訴法均明確規定,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刑訴法并沒有對違反上述方法所獲得的口供證據能力問題作出規定。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61條和1999年《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第265條彌補了該缺陷,均明確規定:采用刑訊逼供或者威脅、引誘、欺騙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被告人供述,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從司法解釋頒布后的實施情況來看,“對于非法取得的證據,在司法實踐中卻幾乎沒有排除過”。〔22 〕有鑒于此,2010年“兩個證據規定”,以“兩高三部”聯合解釋的形式重申“采用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供述,不得作為定案的根據。2012年刑訴法予以確認。
對比前后的非法口供排除規則,可以明顯看出兩者之間的區別:后者把非法口供排除的范圍嚴格限定在“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供述,排除范圍非但沒有維持或者擴張,反而縮小。對于采用“威脅、引誘、欺騙等非法方法”獲得的供述到底是否排除,采取了模糊處理的態度。從全國人大法工委有關刑訴法修改的條文說明和立法理由中,筆者沒有找到這種帶有“退步”性質規定的依據何在,是因為威脅、引誘、欺騙沒有侵犯到人權嗎?還是因為威脅、引誘、欺騙不大可能產生虛假的供述呢? 〔23 〕不過,可以從“兩個證據規定”的主要參與者有關理由說明中找到答案,他們認為:“在司法實踐中,‘威脅、‘引誘、‘欺騙的含義特別是標準不好界定,很多從氣勢上、心理上壓倒、摧垮犯罪嫌疑人心理防線的訊問語言、行為和策略很難與之區分開來,如果這些訊問方法都被認為非法,將導致大量口供被排除,給偵查工作帶來較大沖擊。因此,對此問題應當根據具體案件作出具體處理。” 〔24 〕
由此可見,規則制定者的主要理由是一旦將非法口供排除規則的范圍界定過寬,將導致“大量口供被排除”,會沖擊偵查工作。但是,他們擔心的肯定不是大量“虛假口供”被排除,而是擔心大量“真實口供”被排除。虛假口供被排除,不管有多么“大量”,任何司法制度可能都會接受。“真實口供”僅因取證違法被排除,則取決于價值權衡。權衡標準就是一個國家在特定歷史時期對程序法治和懲罰犯罪的平衡點的選擇。為了確保程序法治的實現,法律應當最大限度地排除非法取得的證據;為了懲罰犯罪的實現,法律可能會通過其他手段制裁違法偵查的人員,但不會排除非法取得的真實證據。就目前中國選擇的模式而言,立法者和司法解釋制定者主要擔心的是那些他們認為極有可能導致證據不真實的違法偵查行為,如“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而對于其他非法手段獲得的供述,則擔心一概排除會導致“真實口供”連同“虛假口供”被排除,妨礙懲罰犯罪目標的實現。由于政法傳統、民眾觀念、司法文化、社會轉型等多種因素的綜合影響,在短期內,這種重視證據真實性而不是合法性的權衡模式不可能有多大的改進空間。
事實上,即使無須權衡的絕對排除規則,在司法實踐中也難逃法官的權衡考量。在2010年“兩個證據規定”頒布之前,針對辯方提出的排除非法口供的申請,法官經常以真實性為由否定辯方的申請。
在“兩個證據規定”頒布之后,根據筆者觀察,非法口供排除規則存在啟動難、排除難和難以排盡的現實問題。所謂啟動難,是指法官原則上不會接受辯方的非法證據排除申請,不啟動非法證據調查程序;所謂排除難,是指法官即使啟動程序,往往也會以證據具有合法性為由不予排除;所謂難以排盡,是指即使排除了口供,通常也只是排除其中的某一份或者某幾份供述,而不是將所有受到非法偵查行為影響的供述予以排除。〔25 〕法院的主要擔憂是排除了全部供述,將會導致無法定罪,可能會放縱事實上有罪的被告人。因此,口供真實性考量依然潛伏于無須權衡的非法口供絕對排除規則之下。因此,即使擴大當前非法口供排除規則的適用范圍,可能還是無法消除司法實踐中以“真實性”取代“合法性”的潛規則。
退一萬步講,即使立法中確立了廣泛的非法口供排除規則,它們在防止虛假供述方面仍然存在明顯的漏洞。例如,美國可能是當今世界上非法口供排除規則范圍最廣的國家之一。首先,任何不具有自愿性的供述,都必須要排除。其次,為了防范法官在評價自愿性時裁量權過大,美國最高法院還發明了米蘭達規則,通過“一刀切”的方式排除任何侵犯米蘭達規則的供述,即沒有告知沉默權的、被告人沒有明確放棄沉默權的、被告人要求保持沉默的等等。最后,其他多種違法行為下取得的口供也會被強制排除,例如違法逮捕后獲得的口供,遲延送至治安法官后獲得的供述,等等。〔26 〕即使如此,從美國近20多年來披露出來的錯案來看,虛假供述問題依然是擺在司法者面前的一道難題。在2000年,依靠DNA證據再審宣告無罪的62名無辜者中,15名作出了虛假供述,占24%。在2007年一份統計中,200名被再審宣告無罪的無辜者中,其中31名被錯誤定罪是由于虛假供述造成的,占16%。〔27 〕造成這種結果的原因是,供述的合法性與真實性并沒有直接聯系,通過前文虛假供述的產生機制來看,即使是合法的供述,也完全有可能是虛假的供述。
(二)口供補強規則實質化的理由
如果轉換思路,從證明力的角度來防止虛假口供,效果可能更好。筆者認為,為了防止虛假口供可能被錯誤采信,同時盡量減少錯誤地排除可能真實的口供,可在現有證據能力規則之上,為口供的可靠性設置一個最低限度的證據標準。簡而言之,任何口供,如果其可靠性沒有得到其他證據的實質性補強,不得采信,藉此限制自由心證的濫用,可以說是“以夷制夷”。〔28 〕也就是說,使當前立法和司法解釋所確立的口供補強規則或者印證規則實質化,規范法官在供述證明力方面的自由評價權力。如此一來,既可阻擋明顯不具有可信性的口供,同時也可緩解非法口供排除規則過于擴張后的消極后果,不至于浪費太多真實的口供,因為即使違法獲得的口供,如果不屬于當前非法口供排除規則的適用對象,也滿足了相應的可靠性標準,就無須直接排除。相對于擴大非法口供排除規則而言,該規則在防范虛假供述方面不僅具有理論基礎和現實依據,而且具有明顯的比較優勢。
1.理論依據
在日常交流過程中,人們對他人所陳述信息的評價,通常是不會質疑其真實性的。其背后的原理是,人類在生活交往中,一般會自發地受到誠實性道德準則的約束,不會去欺騙對方,只有當存在欺騙的動機時,才會故意說假話。由于人們在絕大多數情況下都是根據該原理行事,所以人們也同樣相信其他人也會如此行事。因此,通常在與他人交流時,在對方沒有欺騙的動機存在時,都會默認對方給出的信息是真實的。默認真實的傾向性既是人類有效交流的需要,也是人類思維的惰性所致。同信任相比,傾向于信任交流中的對方是普遍存在的現象,不相信他人所陳述的信息需要更為積極的能動思維。當一方能夠合理地預測到對方具有欺騙的動機時,就可能從信任轉變為懷疑。關于交流內容可信任性的經典研究發現,由于人類具有趨利避害的本能,對于那些損害自己利益的陳述者所陳述的事實,由于缺乏欺騙的動機,往往被評價為更為可信。〔29 〕在一般情形下,一個理性的犯罪嫌疑人沒有明顯的動機作出虛假供述,因為供述意味著承認犯罪,不僅可能無法得到什么利益,反而可能因“撒謊”而失去自由等利益。因此,在對供述進行真實性判斷時,供認犯罪通常會被評價為可信的,因為此時被告人缺乏欺騙他人的動機。當在被告人否認犯罪或者翻供時,由于存在一個明顯的逃避責任追究的動機存在,就會對此保持懷疑態度。輕信供述的真實性是人類的一般心理傾向,而不相信被告人的辯解、翻供也是人類的一般心理傾向。
法官在采信口供時不僅無法避免普通人所具有的上述傾向性,而且還可能因起訴方式加劇。〔30 〕根據2012年刑訴法的有關規定,我國公訴方式恢復到1979年刑訴法的案卷移送制度,即檢察院提起公訴時,應當把全部案卷材料和證據一并移送給法院進行審查。不管是從法律上而言,還是從公訴人的實際利益上而言,公訴案卷材料“在形式上”至少能夠證明被告人的罪行成立。在我國,進行庭前審查的法官與案件的承辦法官并不分離,法官在面對被告人之前,可能已經詳細審閱了案件的所有證據材料,審前產生被告人有罪的心證可能是無法避免的。一旦法官形成了被告人有罪的信念或假設后,就可能會產生“證實性偏差”。所謂“證實性偏差”,是指個體在判斷自己的信念或假設并進行決策時,往往認為支持性的論據更具說服力,并有意或無意地尋找與已有信念或假設一致的信息和解釋,忽視可能與之不一致的信息和解釋,并會把不一致的信息解釋為沒有根據的或者不相關的。〔31 〕因此,在證實性偏差的心理影響下,法官往往無法保持一個開放的心態開始庭審,無法對被告人的供述、辯解進行批判性的審查,由此也可能導致法官輕信被告人的供述。〔32 〕
法官通過經年累月的審判實踐,可能積累了很多察言觀色的技巧。當被告人出現在法庭上,被告人的言行舉止往往會成為他們判斷供述真實性的重要依據。但是,單純依據供述本身和供述者的肢體語言對供述的真實性進行分析,其可靠性也是極低的。我國古代就曾有“五聲聽獄訟”的經驗總結,“通過對嫌犯在庭審中的表情和肢體反應特征直觀整體的把握,來認定案情”。〔33 〕但是,實證研究證實,不管是職業警察還是普通公民,識別供述真實性的能力同隨意拋擲硬幣的幾率相差無幾。美國學者曾以警察和大學生作為實驗對象,研究他們識別真假供述的幾率和差異。研究結果表明,整體的判斷準確率與猜對硬幣正反面的比率相當。其他研究成果也得出類似的結論。〔34 〕即使是經驗豐富的法律職業人員,面對一個虛假供述,也很難依靠供述本身和供述者言行舉止識別出虛假供述。
由于裁判者在口供真實性的判斷上存在輕信供述真實性、不重視無罪辯解和虛假供述識別能力低的特點,所以完全把口供可靠性的判斷交給法官自由認定,極有可能導致不可信的供述被誤采為定案的根據。我們有必要在口供的采納上設置一個不同于自愿性的可靠性標準,從而從證明力的角度設置一個證據準入資格規則。
2.比較優勢
前已述及,為了進一步控制裁判者的裁量權,防止虛假供述,就證據采納制度而言,至少有兩種選擇:一是進一步擴大非法口供排除規則的適用范圍,把威脅、引誘、欺騙等所有違反刑訴法偵訊法定程序的供述,統統予以排除;二是進一步完善當前的口供補強規則,使其真正成為審查判斷口供真實性的一個指南針和不可靠供述的過濾器。
從防止采納虛假供述的角度而言,第一種方案無疑更具有徹底性。但是,正如立法者和司法機關所擔心的,其成本過高。〔35 〕是否遵守法定程序與口供是否是真實的并不是一回事。換句話說,遵守了法定程序可能會導致虛假的供述,而不遵守法定程序有可能會產生真實的供述。如果把所有違反刑訴法偵訊程序的供述統統排除,大量的甚至能夠得到證據實質補強的真實供述也連同虛假供述一并被排除。由此導致的結果是,大量事實上有罪的被告人將因此受益,逍遙法外。發現真相不能不計代價,保障權利同樣也不能不計代價。事實上,最能夠防止虛假供述的證據制度是排除所有的供述,而不僅僅是排除違反法定程序的供述。可能沒有哪一個國家為了保障被告人免受冤獄,會采取如此激進的措施。
要求對口供進行實質補強,也不是一個沒有代價的制度。它同樣也可能導致一部分沒有得到實質補強的口供被排除,由此可能導致真正有罪的人被宣告無罪。因為“在個別的情況下,由于時間過得很久,由于客觀環境、事物的變化等,或者由于最初的偵查路線、偵查方法的錯誤等,以致對被告人的自白找不到證實犯罪事實的有力旁證材料……甚至在少數極為個別的情況下,對被告人的自白找不到任何旁證材料”。〔36 〕此時,口供之所以無法得到實質補強,是客觀原因導致的,而不是因為口供本身不真實所導致的。但是,沒有證據或者證據不夠充分,本身就不能認定任何人構成犯罪。因此,與其說由于客觀原因導致口供無法補強而無法追究刑事責任,是由于口供補強規則所導致的,倒不如說是由于現代刑事訴訟證據裁判原則所導致的。換句話說,如果認真地對待證據確實、充分的證明標準,因口供沒有得到實質補強而被放縱了的“罪犯”,本質上就是無法認定犯罪事實成立的“罪犯”。這與擴大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后導致法院宣告一些“明知”有罪的被告人無罪,顯然不是一回事。從我國法律文化、司法精神和現實國情而言,可能更為容忍無法補強口供后所導致的無罪結果,而不是排除違法但真實的口供后所導致的無罪結果。
3.現實依據
依照《刑事訴訟法》第48條第3款:“證據必須經過查證屬實,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因此,證據具有定案根據的前提之一就是它的真實性。口供沒有得到實質補強,就是口供真實性存在疑點的表征,以其作為證據,不符合《刑事訴訟法》第48條第3款的規定。因此,實質補強規則并不是對立法的突破,它只不過是我國立法有關證據采信基本原則的具體貫徹。
實質補強規則不僅與立法的基本原則是一致的,而且也與司法機關的理解是一致的。由于“兩個證據規定”把排除非法口供范圍限定在“刑訊逼供等手段”,2012年《刑事訴訟法》同樣如此,針對“威脅、引誘、欺騙”等手段所得證據該如何處理的問題,最高人民法院在其有關新刑訴法的法官培訓教材中專門就此提出了指導性意見:“關于通過采取威脅、引誘、欺騙等方法獲得的言詞證據應如何處理的問題……此次刑事訴訟法修改沒有涉及該問題。我們在實踐中可以這樣把握:如果采取威脅、引誘、欺騙等方法獲得言詞證據可能影響證據的真實性,那么該證據就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 〔37 〕
可見,最高人民法院試圖在偵查現實需要和維護實體公正之間尋求平衡,不是一律禁止所有通過非法方法獲得的口供,而只是禁止采納“可能影響證據的真實性”的口供。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并沒有就口供真實性審查提出一個具體明確的規則,事實上是讓全國各地法官根據案件的“具體情況具體分析”。此外,目前法官在運用非法口供排除規則上把口供的真實性作為規則背后的“潛規則”。前文已經分析,針對口供,法官在進行真實性判斷的時候,存在許多心理、認知和制度上的不足,如果任由法官自由認定口供的真實性,極有可能導致采納虛假供述,因此有必要從“真實性”角度建立口供實質補強規則,從而為判斷供述可靠性提供一個較為明確具體的法律標準。
在我國,由于受到各種因素的綜合影響,法官在審理案件時已經養成了“印證”辦案模式。印證的核心在于,“必須獲得更多的具有內含信息同一性的證據來對其進行支持。如證言必須有基本內容相同的口供支持,或者其他證言支持,或者物證、書證以及其他證據支持”。〔38 〕由此可見,印證的本質就是對各種證據的補強。口供實質補強規則就是要求提供證據印證供述。對于已經嫻熟于印證辦案模式的中國法官而言,口供實質補強規則不是一個讓他們感到陌生的新事物,反倒是他們日常辦案模式的基本要求。只不過相對于依靠經驗、能力和道德自覺的印證規則,口供實質補強規則是一個既定的法律規則,可以克服事實認定的隨意性,保障認定標準的統一性,從而使“裁量印證”轉變為“法定印證”。
因此,確立實質補強規則是完全符合我國當前刑訴法基本原則和“司法解釋”精神的,也與我國司法審判長期以來形成的“印證”辦案模式是符合的。
四、口供實質補強規則的比較法考察
在美國,由于歷史上并未經歷歐洲大陸的法定證據制度,對規制證明力問題并不反感,且由“法律外行”組成的陪審團負責事實認定,擔心他們無法客觀地評價證據,所以有關口供的可采性問題歷來是他們關注的核心問題。要求對口供予以補強才能具備證據能力的規則,最早可以追溯到英國17世紀的普通法規則,但是其發揚光大則是美國法官的杰作。在19世紀末,沒有獨立證據補強口供的真實性,口供就不具有可采性的口供補強規則,被美國幾乎所有的州以某種形式予以采納。〔39 〕該規則后來被日本吸收,并明確規定于憲法之中。〔40 〕中國的法律由于受到日本法的影響,加上對歷史上發生的逼供信錯案的憂慮,也在刑訴法中確立了口供補強規則,但是沒有實質內容。因此,有必要在設定中國的口供補強規則具體內容之前,對美國和日本的口供補強規則進行考察。
(一)內容比較
由于審判組織、文化傳統等因素的影響,日本的口供補強規則與美國的規則存在明顯差異。在美國,口供補強規則主要是一個證據可采性規則,即沒有補強到一定程度的庭審外自白,不得作為證據使用。在日本,口供補強規則主要是一個證據充分性規則,即口供被補強到何種程度,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前者主要是通過補強規則來否定特定類型口供的證明力,可以稱為消極補強規則,后者主要是通過補強規則來規范法官以口供為基礎的有罪認定,可以稱為積極補強規則。
其一,關于待補強口供的范圍。
美國實行對抗制,其核心特征是當事人享有充分的程序主導權和實體處分權。最能體現該特征的制度是有罪答辯制度。所謂有罪答辯制,即根據被告人在法庭上的自愿認罪行為作出有罪判定,不再就證據進行法庭調查。被告人的有罪答辯在程序上終止審判,在實體上等同于有罪認定。因此,美國被告人在法庭上的自白無須進行補強。美國的補強規則只適用于不認罪的案件中,被告人在法庭外所作出的自白。〔41 〕在日本,由于擔心有罪答辯制度會導致控辯雙方進行審前“辯訴交易”,而這種交易是“日本的國民精神在根本上所不能相容的”,所以沒有引進美國的有罪答辯制度。〔42 〕被告人在法庭上的自白只是一種有待調查的證據,并不具有終止訴訟和直接定罪的功能。日本的口供補強規則不僅適用于法庭外的自白,也適用于法庭內的自白。此外,美日兩國均要求待補強的口供本身不屬于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對象。也就是說,沒有被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排除掉的供述才有補強的資格。
其二,關于補強對象。
美國有關口供補強的對象有經典模式和現代模式之分。鑒于英國、美國在17世紀末和18世紀初,出現了多起“被害人復活”案件,極大地動搖了刑事司法的公信力。因此,美國補強規則誕生的目的,主要是為了防止被告人供認一個事實上沒有發生的犯罪。為了實現該目的,補強規則要求法庭外自白中的“罪體”要素必須要得到獨立證據的補強,自白才具備可采性。〔43 〕“罪體”要素屬于犯罪構成要件中刨除主體要件和主觀要件的剩余部分。英美法系的“罪體”通常包括以下兩個方面:一是損失或者損害結果的發生,例如發現了一具尸體;二是損失或者損害是由于犯罪行為所引起的,排除偶然因素等其他非犯罪原因,例如經過尸檢,確認是他殺,排除自殺或者意外事件等。其中,被告人和罪犯的同一性不屬于補強的對象,控方只需要證明罪體要素(損害結果以及犯罪行為引起),表明有犯罪確實發生即可。〔44 〕這是美國口供補強規則的經典模式。當前很多州依然采用該模式。該模式幾乎被日本完全照搬。日本有關口供補強的對象,也限制在“罪體”范圍內。有關犯罪的主觀要件和被告人與罪犯的同一性,無須提供補強證據。〔45 〕
在美國聯邦法院系統以及一部分州(如猶他州、新澤西州)則采用另外一種模式。美國最高法院1954年奧普案的判決是其中的典范。相對于經典模式,由于出現較晚,可以視為一種現代模式。該模式要求控方必須要提供證據證明口供本身的可信性,控方“必須提出實質性的獨立證據,證明供述的可信性”,〔46 〕法庭外供述才具有可采性。法官充當守門人角色,在進行可信性認定時,法官要“綜合全部情節”進行判斷。〔47 〕
其三,關于補強證據資格。
在采用罪體標準的美國各州,補強證據的唯一要求就是它必須是除了供述以外的其他獨立證據。在采用可信性標準的法院,只要有其他獨立的證據證明供述具備可信性即可。由于可信性標準并不要求必須對罪體進行證明,所以補強證據范圍不限于那些能夠證明犯罪事實發生的證據。具體來說,主要有兩種形式:一是通過綜合審查供述形成程序的證據進行判斷,可以稱之為“綜合權衡模式”;二是通過審查其他能夠印證供述中只有罪犯才知曉的“特殊知識”的證據進行判斷,可以稱之為“特殊知識模式”。在第一種模式下,可以用來評估法庭外陳述可信性的證據包括“有關供述自發性的證據;是否以欺騙、詭計、威脅或許諾獲得供述;被告人的身體和心理條件,包括年齡,教育和經歷;以及在作出陳述時是否有律師在場”等等。〔48 〕在后一種模式下,可以用來評估供述可信性的,主要是那些能夠印證供述“特殊細節”的證據。
其四,關于補強程度。
因美國的口供補強規則是一個有關庭審外供述的可采性規則,并不是對供述真實性的最終審查,所以其補強程度并不要求達到排除合理懷疑的程度,只要以優勢證據證明罪體事實存在或者供述具有可信性即可。需要指出的是,在以罪犯才可能知道的“特殊知識”來判斷供述的可信性時,其補強程度只要達到證據所證明的事實與特殊知識具有一致性即可。三個方面的因素可以說明被告人具有罪犯才可能知道的“特殊知識”:第一,所提供的信息“幫助警察發現了警察不知曉的證據;第二,提供了“尚未公開的極其不尋常的犯罪情節”的信息;第三,提供了“犯罪現場的日常細節的準確描述,不是輕易能夠猜到的,也沒有公開報道過”,因為“日常細節不大可能是警察誘導的結果”。〔49 〕法官根據供述中的“特殊知識”和證據所證明的犯罪事實之間的“符合程度”來判斷可信性。
日本的口供補強規則不是一個可采性規則,而是一個積極的入罪標準,即口供被其他證據補強到何種程度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因此,其補強程度比美國要更為嚴格。在日本,關于口供補強的程度,“核心問題就是補強證據與口供的互相結合到達排除合理疑問的確信程度,或是到達能夠更加增強這種確信的程度。” 〔50 〕也就是說,補強證據至少需要結合口供能夠達到定罪的證明標準時,才算是達到了補強要求。
(二)價值評析
在美國,口供補強規則主要是一個可采性規則。本質上,它與傳聞證據規則、品格證據規則、原始證據規則等普通法的“內在排除規則” 〔51 〕沒有差異,均是為了防止陪審團錯誤地評價證據或者賦予其超過自己應有的證明力而設計的預防性規則。當然,如果法官把關不嚴,導致沒有得到實質補強的供述轉化為陪審團事實認定的依據,上級法院有可能會以法律適用錯誤為由撤銷判決。日本與美國補強規則的最大差別在于,前者把補強規則視為一個補強到何種程度即可定罪的規則,而不是可采性規則。因此,日本要求的補強程度與定罪標準無異,高于美國的標準。在美國,只要有證據證明罪體事實或者口供本身的大致可信性,就算是達到了補強要求。如果要求補強到排除合理懷疑的程度,無疑使法官事實上在履行陪審團的職能,被視為“篡奪”了陪審團的定罪權,同時也使一名被告人在同一審判程序下接受兩次是否有罪的評價。
就防止虛假供述而言,美國的消極補強規則優于日本的積極補強規則。日本的積極補強規則雖然可以極大地限制裁判者采信口供方面的裁量權,但由于它混同于證明標準,無法將口供自身的可信性問題分離出來。事實上,在日本模式下,只有補強證據和口供相結合,無法排除合理懷疑地證明犯罪事實,口供才可能喪失證明力。但是,當任何證據組合沒有達到證明標準時,都無法定罪,其證明力在理論上都等于零。因此,日本的口供補強規則,實際上把單個證據的證明力審查問題混同于定罪證明標準問題,從而使補強規則特有的防止虛假供述的功能無法得到發揮。美國的消極補強規則本身就是一個有關口供的證據能力規則,其目標就是防止虛假供述,至于達到了補強要求的供述最終是否可以采信以及是否認定有罪,則不是該規則所要解決的問題,它是陪審團在審理結束后綜合全案證據進行判斷的問題。
就補強對象而言,存在罪體標準和可信性標準兩種類型。日本完全吸收了美國的罪體標準。日本學界也有人主張可信性標準,但主導性判例還是以罪體標準為主。〔52 〕筆者認為,就防止虛假供述而言,可信性標準要優于罪體標準。罪體標準確實可以防止被告人承認一起根本就沒有發生過的犯罪,但是對于防止無辜被告人承認了一起確實發生的犯罪,它的防范力度極其有限。因為它只是要求證明犯罪確實存在,并不要求證明有可能是被告人所為。正如美國判例所言:“在認定一個人犯了從來沒有發生過的罪和認定一個人構成由其他人實施的犯罪之間似乎沒有多大區別。” 〔53 〕在司法實踐中,虛假供述通常發生在供認了確實發生的犯罪,而不是沒有發生的犯罪。罪體標準的重心不是放在口供可信性的證明,而是犯罪客觀要素的證明。同時,在司法實踐中,像諸如猥褻兒童等犯罪,可能根本沒有任何客觀的損害或者損失存在,要求證明罪體非常困難。因此,美國的檢察官對其也不滿意。〔54 〕可信性標準則把焦點直接集中于供述自身的可靠性問題,不管罪體要素是否得到補強,只要供述的可靠性得到了法定的補強要求即可,這可以解決罪體標準某些情形下保護力度不足和某些情形下要求過于嚴格的雙重弊端。
就可信性標準下的補強證據而言,綜合權衡模式并不對補強證據提出具體要求,只要能夠綜合起來證明供述的可信性即可,而特殊知識模式要求補強證據必須是能夠證明供述中的關鍵情節的證據。筆者認為,特殊知識模式更加符合當前偵查學和自白心理學有關真假口供的判斷原理。根據刑事偵查學和自白心理學的有關理論,如果供認者在供認前并沒有通過其他途徑獲知案件事實,也沒有受到偵查人員的指供誘供,那么有罪者的供述就能夠透露只有罪犯才可能知道的“特殊知識”,能夠引導偵查人員發現他們尚未收集到的新證據或者無法找到的證據,能夠為難以得到解釋的犯罪事實提供合理解釋,所陳述的內容能夠得到不依賴口供所收集的獨立證據的印證。相反,除非是偶然猜到的,無辜者的供述不可能提供準確的犯罪細節,也無法引導警察發現新證據或者無法找到的證據,也不能解釋犯罪過程中非同尋常的細節,所陳述的內容也難以得到獨立證據的印證。無辜者的虛假供述可能充斥著猜測、錯誤,并且與案件的客觀證據要么不一致,要么無法佐證。〔55 〕美國的特殊知識模式符合供述真假判斷的基本原理,成為許多州供述可信性判斷的標準,并得到學界的認可。〔56 〕
五、我國口供實質補強規則的構建
根據前文比較考察的結果,并結合供述真假識別原理,為了防止虛假供述被錯誤采信,中國口供補強規則的實質化可以把美國的特殊知識模式作為主要參考對象,并分別從待補強口供的范圍、補強對象、補強證據、補強程度等方面設定具體要求。在待補強口供的范圍方面,日本的做法無疑更符合中國實際,因為中國也沒有建立有罪答辯制度。在補強對象方面,應當著眼于供述的可信性,也就是供述中的關鍵細節。在補強證據方面,要求必須是口供以外的其他有證據能力的證據。在補強程度方面,要求供述中的關鍵細節應當與其他證據證明的事實基本一致。
(一)補強證據的基本要求
補強證據是用來擔保供述真實性的證據。補強證據本身的品質直接影響到供述是否真正得到印證。為此,補強證據必須要具備資質方面的基本要求,它必須是具有證據能力、證明力的被告人供述以外的獨立證據或者新證據。
首先,補強證據必須是獨立證據或者新證據。
所謂得到獨立證據的補強,即口供應當包含尚未公開的能夠得到獨立證據證實的信息。犯罪發生后,總是會在世界上遺留下某種客觀痕跡或者主觀痕跡。偵查人員通過取證活動,可以收集到一部分犯罪發生時遺留下來的證據。通過對證據的分析,偵查人員可以獲知案件的部分事實甚至絕大部分事實。依照刑訴法的規定,偵查機關在立案之前,必須要通過獨立的調查活動確認犯罪事實確已發生(相當于“罪體證明”),才能展開偵查訊問活動。因此,在訊問之前,偵查人員已經掌握了部分犯罪事實。如果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中所提供的信息能夠得到事前收集到的證據的證實,那么供述的可靠性就較高。
所謂得到新證據的補強,即口供應當能夠引導偵查人員獲取尚未收集到或者尚未知曉的新證據,且能夠印證供述的內容。對于真正的罪犯而言,如果他供述犯罪,可能會透露出一些尚未被偵查人員了解的信息。如果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幫助偵查人員找到了殺人兇器、血衣、贓物等證據,尤其是當供述幫助偵查人員發現了隱蔽性很強的證據,那么這就等于是犯罪“特殊知識”的高度暴露。由此可以揭示,除非供述者是真正的罪犯,否則不可能知曉這么隱蔽的證據。〔57 〕如果犯罪嫌疑人的供述無法引導偵查人員尋找到有價值的新證據,這將是供述者不知道犯罪事實的表征,是供認者對犯罪事實“無知的暴露”,進而表明供述可能是虛假的。〔58 〕當然,有時候犯罪分子為了逃避追究,有可能會毀尸滅跡,導致與犯罪直接相關的重要證據滅失,但是即使在此情形下,其毀滅罪證的行為依然可能會遺留新的證據。真正的罪犯當然知曉自己毀滅證據的行為,同樣可能引導偵查人員發現有價值的證據。
如果供述的內容既有獨立證據的補強,也有新證據的補強,當然最好。但是,由于時過境遷、風雨侵蝕、取證方法不當等原因,可能無法同時收集到獨立證據和新證據,所以即使供述沒有得到獨立證據和新證據的同時補強,只要得到其中一種補強,也可以視為供述的內容得到了其他證據的補強。畢竟不管是獨立證據,還是新證據,通常都是非罪犯不可能知道的“特殊知識”,可以擔保供述的可靠性。
其次,補強證據必須是被告人供述以外的其他證據。
從供述的對象而言,口供可以分為向專門機關的供述和向第三人的供述。依照我國當前的證據理論和實務操作,把前者視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后者視為“證人證言”。但是,轉述他人犯罪事實的“證人證言”,本質上不過是另一種版本的“口供”,如果允許以其作為補強證據,就等于是允許以被告人的口供來印證自己的口供。因此,不管把向第三人的供述歸為何種法定證據種類,其事實上屬于被告人供述的“傳來證據”的性質是無法否認的。因此,向第三人的供述不具有補強證據資格。
最后,補強證據本身必須具有證據能力和證明力。
美國的補強規則并不要求補強證據具備證明力,這主要是因為可采性認定和證據證明力認定的分離所致。包括口供在內的所有證據,其最終是否有證明力以及有多大證明力,屬于陪審團的判斷權限。因此,法官無須也無法要求補強證據具備證明力。但中國的證據資格審查和證據最終證明力的判斷均由同一個審判組織來負責,因此裁判者有權力也有職責確保補強證據本身具有證明力。此外,如果以不具有證明力的虛假證據來補強口供,往往會導致錯誤的判斷。因此,筆者認為,補強證據必須同時具備證據能力和證明力。不具有證據能力的證據,例如通過刑訊逼供等非法手段獲得的同案犯供述,通過暴力、威脅等非法手段獲得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不能證明物證、書證來源的物證、書證、拒不出庭作證的鑒定人的鑒定意見等,均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當然也不能作為補強證據。即使具有了證據能力,經過法庭調查后認定不具有相關性或者真實性的,也不能作為補強證據。
(二)待補強口供的基本要求
對于口供的審查,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它的合法性,二是它的真實性。合法性審查在先,真實性審查在后。只有在排除口供系由刑訊逼供等非法手段獲得的條件下,才啟動口供真實性審查。我國目前已經初步建立了有關口供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體系,任何落在非法口供排除規則排除范圍之內的供述,不再具有證據能力。不具有證據能力的口供當然也就沒有被補強的資格。因此,待補強口供首先必須是經過非法口供排除規則過濾后的供述。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口供實質補強規則是虛假供述的“第二道防線”。
根據供述的階段,可以把口供分為庭審口供和庭前口供。一般認為,在公開的法庭上,由于沒有外在的壓力,如果被告人在理解供述的后果后,主動供認犯罪事實,應當視為真實的供述。因此,需要補強的口供主要是庭前口供。無論是庭審口供還是庭前口供,采信被告人的口供都必須要得到獨立證據或者新證據的補強。因為我國并沒有建立英美法系的有罪答辯制度,被告人自愿認罪的行為不具有類似民事訴訟自認的效果,不可以直接認定被告人構成犯罪。我國被告人的供述只是一種證據類型,并不具有終止訴訟的程序效果。再加上我國法院具有發現事實真相的義務,不受當事人意思的拘束,應當在職權范圍內澄清案件真相,所以庭審口供與庭前口供都需要得到證據補強,才能作為定案根據。
法官在審查供述是否得到證據補強時,必須要同時審查供述信息的來源,只有在排除了偵查人員誘供指供和案情泄露的情形下,口供才具有被證據補強的資格。為什么一個沒有實施犯罪的人能夠供認出具體犯罪事實?普通人一般認為,肯定是偵查人員采取刑訊逼供所致。事實上,刑訊逼供最多只能讓無辜的犯罪嫌疑人放棄辯解,承認犯罪,而不可能讓無辜的犯罪嫌疑人供述出犯罪的細節。因為不知道犯罪事實的無辜嫌疑人只能依靠猜想、推測“供述”犯罪事實,所以他們所“供述”的事實通常無法得到證據的印證。真正讓無辜犯罪嫌疑人供述出犯罪細節的,不是逼供,而是誘供指供。偵查人員通過披露他們已經掌握的犯罪事實或者展示有關的犯罪證據,然后誘導嫌疑人“順桿爬”,無辜犯罪嫌疑人才能供述出符合規格的供述。“在偵查人員針對一名嫌疑人提出指控之前,或許已經知道了許多只有罪犯才知道的犯罪事實——使用什么類型的武器,罪犯的慣技等等。如果粗枝大葉的訊問人員在訊問時把這個信息傳送給嫌疑人,嫌疑人隨后就能夠做出一個虛假的但卻能夠得到嚴格意義上補強的口供。” 〔59 〕顯然,此時供述的信息事實上不是源自于犯罪嫌疑人自己的記憶,而是源自于偵查人員的誘導性信息。從這個意義上而言,誘供指供比逼供更為可怕,逼供只能讓人認罪,放棄抵抗,而誘供指供則能讓無辜的犯罪嫌疑人供述出與證據表面上印證的口供,從而使案件在表面上“無懈可擊”。此外,還需要審查案情在偵訊之前是否已經泄露。當案件信息已經泄露,凡是了解所泄露信息的人都可能知曉部分非罪犯不可能知道的“特殊知識”。在此情況下,有可能導致冒名頂替式的自愿性虛假供述,也可能導致強迫依從型虛假供述。〔60 〕因此,不管是獨立證據的補強,還是新證據的補強,只有當供述中得到補強的信息真正源自于犯罪嫌疑人的“特殊知識”,才具有印證的價值。如果信息源自于誘供指供或者信息已經泄露給有關人員,那么即使口供得到補強,也不能據此認定口供的真實性已經得到了證明。
(三)補強的對象和程度
被告人的供述有可能詳細地陳述犯罪的動機、意圖、準備、手段、過程和結果等諸多方面的信息。如果要求供述中的全部內容都必須要得到證據的補強,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顯然標準過高,而且也混淆了補強證據規則和證明標準的關系。口供實質補強規則主要為了防止采納那些明顯不具有真實性的口供,如果要求補強證據必須能夠證實供述中的每一個細節,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很多供述可能都無法達到上述要求。
此外,即使是基本內容真實的供述,也可能在某些關鍵情節上與其他證據所證明的事實不符。導致這種現象的原因甚多:有可能是由于擔心遭受沉重的道德指責,某個奸淫幼女的罪犯只是承認奸淫,但拒絕透露更多的細節;可能是由于實施犯罪的時候處于醉酒的狀態,無法完全清楚地記住案發時的情景;可能是由于犯罪時過度緊張,注意力過于集中到某些方面,而忽視其他的細節;可能是謀殺者為了報復死者及其親屬,拒絕透露尸體的藏匿位置;可能是其他人員發現了被藏匿的盜竊物品并將其偷走;可能是罪犯期望從監獄釋放后揮霍那些他藏匿的盜竊物品而故意提供錯誤情節;等等。因此,要求供述中的所有細節均需得到其他證據的證實,才能作為證據使用,將會導致許多真實的供述被排除。
被告人承認指控的犯罪,但是他無法提供關鍵性的細節,或者所提供細節無法得到獨立證據、新證據的印證,可能存在合理的解釋。但是,如果一份供述中沒有提供任何關鍵性的細節,或者所有細節都與證據不符。此時,通常應當對他的可靠性和自愿性保持懷疑。只承認犯罪,無細節或者細節印證,是被告人從內心不準備接受刑事責任的征兆。在此情形下,要么被告人確實不知道犯罪事實,要么被告人的供述不是出自于他的自由意志,此時不加批判地接受供述存在著巨大的風險。〔61 〕
因此,對犯罪細節的補強是防范這種風險的最佳裝置之一。當然,由于供述中可能存在許多細節,要求全部細節均得到證實,也是非常困難的。作為一個排除性的規則,設定如此嚴格的要求,無異于廢棄口供。“細節特征吻合的意義主要不在于數量,而在于該細節的特殊性程度”,〔62 〕只要證據能夠補強供述中的犯罪客觀方面的某個或某些特殊細節,就可以據此認定口供的真實性得到了擔保。例如,殺人的兇器是故意殺人案件中印證供述中犯罪工具的重要補強證據,但是由于兇器被銷毀等原因,可能無法再找到相應的證據。那么不能單單因為殺人工具沒有證據印證,就徹底否定供述的證據資格。如果尸體檢驗報告關于被害人特殊死亡原因的描述與被告人供述的殺人方法是一致的,那么也可以視為供述的真實性得到了補強。
就補強程度而言,筆者認為,只要補強證據和供述中的某個或某些關鍵性細節,基本吻合一致,就視為達到了補強要求。前已述及,對于真正的罪犯而言,由于他知曉犯罪的前因后果和具體過程,所以真實的供述應當是與其他證據證明的事實吻合的。但是,由于受到記憶、表達和情感等多種因素的影響,供述的內容與其他證據完全吻合一致、嚴絲合縫,幾乎是不可能的。相反,如果犯罪嫌疑人的供述與證人證言等言詞證據在語言表達甚至標點符號上都是一致的,那么反而證明兩者之一可能是虛假的,因為任何兩個人幾乎都不可能在沒有誘導的情況下說出完全一樣的話。因此供認者的描述與被害人的陳述或者證人證言之間存在不完全一致的地方,并不能否定供述的真實性,但是在基本情節上供述的內容應當需要與其他證據證明的事實保持基本吻合一致。否則,就極有可能是虛假的供述。
經過非法口供排除規則過濾后的任何口供,只有在特殊情節排除了誘供指供和案情泄露的前提下獲得的,并得到了具有證據能力、證明力的被告人供述以外的獨立證據或者新證據的印證,且供述中的犯罪客觀方面的特殊細節與證據所證明的事實基本吻合一致,才能作為證據使用。這是口供實質補強規則的核心內容。當然,經過了非法口供排除規則的過濾和實質補強規則的驗證之后,供述最終是否能夠采信以及能否據此認定被告人構成犯罪,還必須結合全案的證據進行綜合判斷,只有依據理性、邏輯、良心得出排除任何合理懷疑的有罪結論,才能最終認定被告人有罪。這是消極補強規則同積極補強規則的核心差別。
〔1〕根據我國學者的實證研究,在三個區縣的調研結果為犯罪嫌疑人的自白率為95.1到100%。參見劉方權:《認真對待偵查訊問——基于實證的考察》,《中國刑事法雜志》2007年第5期。麥康威爾對我國刑事司法的實證研究結果,也能夠證實這個結果,他統計的自白率為95%。See Mike McConville, Criminal Justice in China: An Empirical Study, Edward Elgar, 2011, p.72.
〔2〕最高法院工作報告顯示:2011年各級法院審結一審刑事案件84萬件,判處罪犯105.1萬人;2010年各級法院審結一審刑事案件779641件,判處罪犯1006420人;2009年各級法院審結一審刑事案件76.7萬件,判處罪犯99.7萬人。
〔3〕參見陳永生:《我國刑事誤判問題透視——以20起震驚全國的刑事冤案為樣本的分析》,《中國法學》2007年第3期;何家弘、何然:《刑事錯案中的證據問題——實證研究與經濟分析》,《政法論壇》2008年第2期;李建明:《死刑案件錯誤裁判問題研究——以殺人案件為視角的分析》,《法商研究》2005年第1期。
〔4〕2012年刑訴法所確立的防止刑訊逼供的主要舉措為:明確要求拘留、逮捕后必須立即將犯罪嫌疑人送看守所羈押,拘留后送所羈押不得超過24小時;對被羈押的犯罪嫌疑人,只能在看守所內進行訊問;對于可能判處死刑、無期徒刑的案件,應當進行全程錄音或者錄像。
〔5〕真正有罪的嫌疑人可能會萬般狡辯、推卸責任,而“無辜者至高的利益和迫切的愿望何在?驅散環繞在其身上的疑云,并作出每一個解釋以還原事實的原貌”。 See Michael A. Menlowe, Bentham Self-Incrimination and The Law of Evidence, 104 LAW Q. REV. 286 (1988), p.104.
〔6〕由羈押性訊問所產生的內在強制力是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確立米蘭達規則的基本理由之一,其目的是為了消除羈押場所中內在的壓力,使犯罪嫌疑人能夠自由地決定是否行使沉默權。參見孫長永:《沉默權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68—169頁。
〔7〕[日]浜田壽美男:《自白的心理學》,片成南譯,中國輕工業出版社2006年版,第80頁。
〔8〕Kassin, S. M., Drizin, S. A., Grisso, T., Gudjonsson, G. H., Leo, R.A., & Redlich, A. D., Police-Induced Confessions: Risk Factors and Recommendations, Law and Human Behavior, 2010, vol.34, pp.3—38.
〔9〕See Brandon L. Garrett, The Substance of False Confessions, 62 STAN. L. REV. 1051 (2010).
〔10〕See Saul M. Kassin, Christine C. Goldstein and Kenneth Savitsky, Behavioral Confirmation in the Interrogation Room: On the Dangers of Presuming Guilt, Law and Human Behavior, 2003, Vol. 27, No. 2.
〔11〕Richard A. Leo, Why Interrogation Contamination Occurs(2013), Ohio State Journal of Criminal Law, Forthcoming; Univ. of San Francisco Law Research Paper, Available at SSRN: http://ssrn.com/abstract=2235152.
〔12〕參見[英]Gisli H. Gudjonsson:《審訊和供述心理學手冊》,樂國安、李安等譯,中國輕工業出版社2008年版,第185頁。
〔13〕參見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刑法室:《關于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決定:條文說明、立法理由及相關規定》,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56頁。
〔14〕參見張建偉:《自白任意性規則的法律價值》,《法學研究》2012年第6期。
〔15〕參見李昌盛:《違法偵查行為的程序性制裁效果研究——以非法口供排除規則為中心》,《現代法學》2012年第3期。
〔16〕有學者曾對1984年、1994年和2004年三個年份刑事案件證據種類結構進行過統計分析,結果表明:1984年每案口供證據平均為8.11份,1994年為4.47份,2004年為6.5份。參見左衛民等:《中國刑事訴訟運行機制實證研究:以審前程序為重心》,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232頁。
〔17〕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的解釋》第82條基本上照搬了《死刑證據規定》第21條的規定,沒有進一步擴大瑕疵證據相對排除規則的適用情形。
〔18〕熊秋紅:《刑事證據制度發展中的階段性進步——刑事證據兩個規定評析》,《證據科學》2010年第5期。
〔19〕參見林勁松:《刑事審判書面印證的負效應》,《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6期。
〔20〕佘祥林案件就是其中的典型。有關該案的具體內容,參見唐衛彬、黎昌政:《就這樣,佘祥林把妻子“殺”了11年》,《新華每日電訊》2005年4月8日。
〔21〕根據成都市法院系統針對隨機抽選的250起案件中口供證據的分析,“完全沒有其他證據而只以口供定罪的案件(不包括共同犯罪中只有各被告人口供)在調查中沒有發現”。參見成都市中級法院研究室、武侯區法院刑事審判庭:被告人口供運用的調研報告——以審判程序為視,載成都法院網http://cdfy.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04/06/id/550827.shtml,2013年9月21日。
〔22〕參見張建偉:《自白任意性規則的法律價值》,《法學研究》2012年第6期。
〔23〕參見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刑法室:《關于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決定:條文說明、立法理由及相關規定》,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55—57頁。
〔24〕張軍主編:《刑事證據規則理解與適用》,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297頁。
〔25〕參見前引〔15〕,李昌盛文。
〔26〕Larry Laudan, Truth, Error, and Criminal Law: An Essay in Legal Epistemolog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172—178.
〔27〕See Richard A. Leo, Police Interrogation and American Justic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239.
〔28〕林鈺雄:《嚴格證明與刑事證據》,臺灣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版,第124頁。
〔29〕Timothy R. Levine, Rachel K. Kim & J. Pete Blair, (In)accuracy at Detecting True and False Confessions and Denials: An Initial Test of a Projected Motive Model of Veracity Judgments, 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36 (2010), pp.86—88.
〔30〕據筆者對重慶、四川、貴州、海南、內蒙古、廣東等地的調研,很多地方的檢察院在數年前就已經恢復了案卷移送制度。
〔31〕參見吳修良等:《判斷與決策中的證實性偏差》,《心理科學進展》2012年第7期。
〔32〕例如,在浙江省張輝、張高平錯案中,偵查階段對死者做的DNA檢驗報告顯示,在被害人的8個指甲末端檢出混合的DNA譜帶,由死者與一名男性的DNA譜帶混合形成,“排除由死者和犯罪嫌疑人張輝或張高平的DNA譜帶混合形成”。但在一審、二審中,杭州市中級法院認為,“因手指為相對開放部位,不排除被害人因生前與他人接觸而在手指甲內留下DNA的可能性”,浙江省高級法院認為,“本案中的DNA鑒定結論與本案犯罪事實并無關聯”。參見陳東升、王春:《記者調查“死刑改判案”前因后果》,《法制日報》2013年3月27日。這顯然是法官在證實性心理的基礎上對證據的“沒有根據的”解釋。DNA顯然是一個重要的無罪證據,而不是沒有關聯,雖然它們不能證明被告人沒有實施犯罪,但是足以證明本案有可能是其他人所為,認定二張構成犯罪,結論不具有唯一性。
〔33〕李麒:《中國傳統刑事訴訟文化的雙重性格》,《比較法研究》2013年第2期。
〔34〕See Christian A. Meissner and Saul M. Kassin, You're guilty, so Just Confession! Cognitive and Behavioral Confirmation Biases in the Interrogation Room, in G. D. Lassiter(ed.), Interrogations, Confessions and Entrapment, Springer, 2006, pp.86—106.
〔35〕美國有關口供的排除規則不僅數量眾多,而且極其嚴格。其中,米蘭達規則就是一項。根據米蘭達規則,只要在羈押訊問的情境下,沒有進行米蘭達告知,或者告知后犯罪嫌疑人沒有明確表示放棄沉默權或者律師幫助權的,由此獲得的供述都要予以排除。保羅·卡塞爾曾對米蘭達案對定罪率的影響進行了廣泛的實證研究。其中一個結論是:“每年由于米蘭達規則沒有解決的犯罪數量在暴力犯罪中介于56000件到136000件之間,在財產犯罪中介于72000件到299000件之間。”See Paul Cassell, Miranda's Social Costs: An Empirical Reassessment, 90 Nw. U. L. Rev. 387 (1996). 雖然我國尚未賦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權,但是如果排除規則的適用范圍過大,必將導致定罪率的下降。這可能是我國立法機關及司法機關不愿意進一步擴大排除規則適用范圍的主要原因。
〔36〕劉慶林:《試論被告人自白證據價值》,《法學》1957年第5期。
〔37〕張軍主編:《新刑事訴訟法法官培訓教材》,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72頁。
〔38〕龍宗智:《印證與自由心證——我國刑事訴訟證明模式》,《法學研究》2004年第2期。
〔39〕See David A. Moran, In Defense of the Corpus Delicti Rule, Ohio State Law Journal, 2003, vol.64, p.817.
〔40〕[日]松尾浩也:《刑事訴訟法》(下卷),張凌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37頁。
〔41〕Evidence-Extrajudicial Confession Inadmissible Without Corroborate Evidence to Establish Corpus Delicti, St. Louis v. Watters, 289 S.W.2d444 (Mo. App. 1956), 1956 Wash. U. L. Q. 483 (1956).
〔42〕[日]土本武司:《日本刑事訴訟法要義》,董璠輿、宋英輝譯,臺灣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336頁。
〔43〕See David A. Moran, In Defense of the Corpus Delicti Rule, Ohio State Law Journal, 2003, vol.64, p.817.
〔44〕See David A. Moran, In Defense of the Corpus Delicti Rule, Ohio State Law Journal, 2003, vol.64, p.817.
〔45〕前引〔40〕,松尾浩也書,第38頁;前引〔42〕,土本武司書,第340—342頁。
〔46〕Opper v. United States, 348 U.S. 84 (1954), at 93.
〔47〕State v. Mauchley, 67 P.3d 477 (Utah 2003), at 490.
〔48〕State v. Mauchley, 67 P.3d 477 (Utah 2003), at 488.
〔49〕State v. Mauchley, 67 P.3d 477 (Utah 2003).
〔50〕前引〔40〕,松尾浩也書,第39頁。
〔51〕所謂“內在排除規則”,即“基于證據的證明力可能會被過高評價或者損害性會超出其證明價值——即可能導致事實認定者不公平地偏向于某一特定結果——的理論而確立的證據排除規則”。參見[美]米爾建·R·達馬斯卡:《漂移的證據法》,李學軍等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19頁。
〔52〕[日]田口守一:《刑事訴訟法》,劉迪等譯,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54頁。
〔53〕State v. Mauchley, 67 P.3d 477 (Utah 2003).
〔54〕See Richard A. Leo, Police interrogation and American justic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285.
〔55〕See Fred E. Inbau, John E. Reid, Joseph P. Buckley & Brian C. Jayne, Criminal Interrogation and Confessions, Jones and Bartlett Publishers, 2003, p.432; See Richard A. Leo, Steven A. Drizin, Peter J. Neufeld, Bradley R. Hall & Amy Vatner, Bring Reliability Back in: False Confessions and Legal Safeguard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2006 WIS. L. REV. 479, pp.520—522; Richard A. Leo, Police interrogation and American justic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287—289.
〔56〕See Richard A. Leo, Police interrogation and American justic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285—286.
〔57〕在司法實踐中,司法人員有時候直接依據“新證據補強”規則認定犯罪事實,甚至核準死刑,足見該規則在擔保供述真實性方面的巨大作用。可參見方文軍:《供證關系與事實認定探微》,《法律適用》2010年第12期。
〔58〕前引〔7〕,浜田壽美男書,第32—34頁。
〔59〕Larry Laudan, Truth, Error, and Criminal Law: An Essay in Legal Epistemolog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180.
〔60〕浙江吳大全錯案就是典型案例。具體內容,參見陳磊:《吳大全 中國版的“肖申克救贖”》,《南方人物周刊》2014年第41期。
〔61〕Rinat Kitai-Sangero, Can Dostoyevsky's Crime and Punishment Help Us Distinguish Between True and False Confessions? Ohio State Journal of Criminal Law, 2011, vol.19, pp.252.
〔62〕李建明:《刑事證據相互印證的合理性與合理限度》,《法學研究》200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