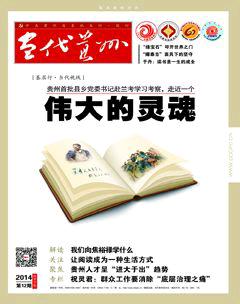甲午戰爭與北洋海軍(中)
金一南,本刊顧問,國防大學戰略教研部副主任(副軍級)、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國家安全戰略、國際沖突與危機處理,曾赴美國國防大學和英國皇家軍事科學院學習,2001年3月代表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赴美國國防大學講學。
危機面前的北洋海軍能否一戰?流行的說法是,自1888年后未添船購炮,北洋海軍難以一戰。難道真如清臣文廷式指責的那樣“北洋海軍糜費千萬卻不能一戰”?
先從軟件方面看。首先, 北洋海軍建立之初參考西方各海軍強國,制定了一套周密的規程。其中囊括船制、官制、餉制、儀制、軍規、校閱、武備等方面,組織規程完備,對各級官兵都有具體詳盡嚴格的要求。其次,北洋艦隊前期訓練相當刻苦,監督甚嚴,“刻不自暇自逸,嘗在廁中猶命打旗傳令”;“日夜操練,士卒欲求離艦甚難,是瑯精神所及,人無敢差錯者”。此等嚴格的要求和訓練,在文化素質上也使北洋官兵達到了較高水準。
再從硬件上說。定遠、鎮遠兩艘鐵甲艦,直到大戰爆發前,是當時世界比較先進的鐵甲堡式鐵甲艦,各裝十二英寸大炮四門,裝甲厚度達十四寸。黃海大戰中兩艦“中數百彈,又被松島之十三寸大彈擊中數次,而曾無一彈之鉆入,死者亦不見其多”,皆證明它們是威力強大的海戰利器。日本以此二艦為最大威脅,嘆其為“東洋巨擘”,直到戰時也未獲得達到這樣威力的軍艦。
黃海大戰前的北洋海軍,從表面看軟件硬件都具有相當實力。清廷正是出于此種自信,才在豐島海戰之后毅然對日宣戰。
日本精心策劃了這場戰爭。但礙于北洋海軍,它也沒有必勝的把握。日本為勝利和失敗都做好了準備。所以如此,是感覺到自己海軍力量不足。
首先,日本海軍的投入少于滿清海軍。其次,聯合艦隊組建倉促。其三,艦只混雜,有的戰斗力甚弱。
大戰之前的中日海軍,總體看中方的優勢還稍大一些。但當戰場不再是操演場時,平日訓練的差異立即顯現。
面對逼近的敵艦,北洋艦隊首先在布陣上陷入混亂。提督丁汝昌的“分段縱列、掎角魚貫之陣”,到總兵劉步蟾傳令后,變為“一字雁行陣”;隨后針對日方陣列我方又發生齟齬,交戰時的實際戰斗隊形成了“單行兩翼雁行陣”;時間不長,“待日艦繞至背后時清軍陣列始亂,此后即不復能整矣”。這種混亂致使今天很多人還在考證,北洋艦隊到底用的什么陣形。
其次,還未進入有效射距,“定遠”艦首先發炮,不但未擊中目標,反而震塌主炮上的飛橋,丁汝昌從橋上摔下嚴重受傷,首炮就使北洋艦隊失去了總指揮。黃海大海戰持續四個多小時,北洋艦隊“旗艦僅于開仗時升一旗令,此后遂無號令”,一直在失去統一指揮的狀態下作戰。
第三是作戰效能低下,擊之不中,中之不沉。李鴻章平日夸耀北洋海軍“攻守多方,備極奇奧”、“發十六炮,中至十五”,在真槍實彈的戰場上煙消云散。有資料統計,黃海海戰日艦平均中彈11.17發,而北洋各艦平均中彈107.71發。對方火炮命中率高出我方9倍以上。
北洋艦隊官兵作戰異常英勇。其寧死不退、誓以軍艦共存亡之氣概,讓外籍雇員都留下深刻印象。但對軍人來說,勝利沒有替代品。戰場決定勝利,戰場不能孕育勝利。很多東西僅憑戰場上的豪壯不能獲得。最輝煌的勝利,只能孕育在最瑣碎枯燥、最清淡無味的承平里。
多種資料證明,北洋海軍在一片承平的環境中,軍風嚴重毒化。《北洋海軍章程》、清廷兵部的《處分則例》等形同虛設。
至于艦船不作訓練而用于它途,已不是個別現象。“南洋‘元凱、‘超武兵船,僅供大員往來差使,并不巡緝海面”;北洋則以軍艦走私販運,搭載旅客,為各衙門賺取銀兩。艦隊腐敗風氣蔓延,訓練中弄虛作假,欺上瞞下。
軍風腐敗的結果,戰時必然要付出高昂代價。力圖隱瞞這一代價,就要謊報軍情。直至全軍覆滅那一天,謊報軍情未曾中止。
有的謊報軍情,使作戰計劃都發生改變。1895年2月, 左一魚雷艇管帶王平駕艇帶頭出逃,至煙臺后先謊稱丁汝昌令其率軍沖出,再謊稱威海已失。陸路援兵得訊,撤消了對威海的增援。陸路撤援,成為威海防衛戰失敗的直接原因。
越是艱難處境,越考驗軍風、軍紀。北洋海軍在威海圍困戰后期,軍紀蕩然無存。
首先是部分人員不告而別。其次是有組織的大規模逃逸。最后發展到集體投降。
軍風至此,軍紀至此,不由不亡。(責任編輯/吳文仙)
金一南,本刊顧問,國防大學戰略教研部副主任(副軍級)、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國家安全戰略、國際沖突與危機處理,曾赴美國國防大學和英國皇家軍事科學院學習,2001年3月代表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赴美國國防大學講學。
危機面前的北洋海軍能否一戰?流行的說法是,自1888年后未添船購炮,北洋海軍難以一戰。難道真如清臣文廷式指責的那樣“北洋海軍糜費千萬卻不能一戰”?
先從軟件方面看。首先, 北洋海軍建立之初參考西方各海軍強國,制定了一套周密的規程。其中囊括船制、官制、餉制、儀制、軍規、校閱、武備等方面,組織規程完備,對各級官兵都有具體詳盡嚴格的要求。其次,北洋艦隊前期訓練相當刻苦,監督甚嚴,“刻不自暇自逸,嘗在廁中猶命打旗傳令”;“日夜操練,士卒欲求離艦甚難,是瑯精神所及,人無敢差錯者”。此等嚴格的要求和訓練,在文化素質上也使北洋官兵達到了較高水準。
再從硬件上說。定遠、鎮遠兩艘鐵甲艦,直到大戰爆發前,是當時世界比較先進的鐵甲堡式鐵甲艦,各裝十二英寸大炮四門,裝甲厚度達十四寸。黃海大戰中兩艦“中數百彈,又被松島之十三寸大彈擊中數次,而曾無一彈之鉆入,死者亦不見其多”,皆證明它們是威力強大的海戰利器。日本以此二艦為最大威脅,嘆其為“東洋巨擘”,直到戰時也未獲得達到這樣威力的軍艦。
黃海大戰前的北洋海軍,從表面看軟件硬件都具有相當實力。清廷正是出于此種自信,才在豐島海戰之后毅然對日宣戰。
日本精心策劃了這場戰爭。但礙于北洋海軍,它也沒有必勝的把握。日本為勝利和失敗都做好了準備。所以如此,是感覺到自己海軍力量不足。
首先,日本海軍的投入少于滿清海軍。其次,聯合艦隊組建倉促。其三,艦只混雜,有的戰斗力甚弱。
大戰之前的中日海軍,總體看中方的優勢還稍大一些。但當戰場不再是操演場時,平日訓練的差異立即顯現。
面對逼近的敵艦,北洋艦隊首先在布陣上陷入混亂。提督丁汝昌的“分段縱列、掎角魚貫之陣”,到總兵劉步蟾傳令后,變為“一字雁行陣”;隨后針對日方陣列我方又發生齟齬,交戰時的實際戰斗隊形成了“單行兩翼雁行陣”;時間不長,“待日艦繞至背后時清軍陣列始亂,此后即不復能整矣”。這種混亂致使今天很多人還在考證,北洋艦隊到底用的什么陣形。
其次,還未進入有效射距,“定遠”艦首先發炮,不但未擊中目標,反而震塌主炮上的飛橋,丁汝昌從橋上摔下嚴重受傷,首炮就使北洋艦隊失去了總指揮。黃海大海戰持續四個多小時,北洋艦隊“旗艦僅于開仗時升一旗令,此后遂無號令”,一直在失去統一指揮的狀態下作戰。
第三是作戰效能低下,擊之不中,中之不沉。李鴻章平日夸耀北洋海軍“攻守多方,備極奇奧”、“發十六炮,中至十五”,在真槍實彈的戰場上煙消云散。有資料統計,黃海海戰日艦平均中彈11.17發,而北洋各艦平均中彈107.71發。對方火炮命中率高出我方9倍以上。
北洋艦隊官兵作戰異常英勇。其寧死不退、誓以軍艦共存亡之氣概,讓外籍雇員都留下深刻印象。但對軍人來說,勝利沒有替代品。戰場決定勝利,戰場不能孕育勝利。很多東西僅憑戰場上的豪壯不能獲得。最輝煌的勝利,只能孕育在最瑣碎枯燥、最清淡無味的承平里。
多種資料證明,北洋海軍在一片承平的環境中,軍風嚴重毒化。《北洋海軍章程》、清廷兵部的《處分則例》等形同虛設。
至于艦船不作訓練而用于它途,已不是個別現象。“南洋‘元凱、‘超武兵船,僅供大員往來差使,并不巡緝海面”;北洋則以軍艦走私販運,搭載旅客,為各衙門賺取銀兩。艦隊腐敗風氣蔓延,訓練中弄虛作假,欺上瞞下。
軍風腐敗的結果,戰時必然要付出高昂代價。力圖隱瞞這一代價,就要謊報軍情。直至全軍覆滅那一天,謊報軍情未曾中止。
有的謊報軍情,使作戰計劃都發生改變。1895年2月, 左一魚雷艇管帶王平駕艇帶頭出逃,至煙臺后先謊稱丁汝昌令其率軍沖出,再謊稱威海已失。陸路援兵得訊,撤消了對威海的增援。陸路撤援,成為威海防衛戰失敗的直接原因。
越是艱難處境,越考驗軍風、軍紀。北洋海軍在威海圍困戰后期,軍紀蕩然無存。
首先是部分人員不告而別。其次是有組織的大規模逃逸。最后發展到集體投降。
軍風至此,軍紀至此,不由不亡。(責任編輯/吳文仙)
金一南,本刊顧問,國防大學戰略教研部副主任(副軍級)、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國家安全戰略、國際沖突與危機處理,曾赴美國國防大學和英國皇家軍事科學院學習,2001年3月代表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赴美國國防大學講學。
危機面前的北洋海軍能否一戰?流行的說法是,自1888年后未添船購炮,北洋海軍難以一戰。難道真如清臣文廷式指責的那樣“北洋海軍糜費千萬卻不能一戰”?
先從軟件方面看。首先, 北洋海軍建立之初參考西方各海軍強國,制定了一套周密的規程。其中囊括船制、官制、餉制、儀制、軍規、校閱、武備等方面,組織規程完備,對各級官兵都有具體詳盡嚴格的要求。其次,北洋艦隊前期訓練相當刻苦,監督甚嚴,“刻不自暇自逸,嘗在廁中猶命打旗傳令”;“日夜操練,士卒欲求離艦甚難,是瑯精神所及,人無敢差錯者”。此等嚴格的要求和訓練,在文化素質上也使北洋官兵達到了較高水準。
再從硬件上說。定遠、鎮遠兩艘鐵甲艦,直到大戰爆發前,是當時世界比較先進的鐵甲堡式鐵甲艦,各裝十二英寸大炮四門,裝甲厚度達十四寸。黃海大戰中兩艦“中數百彈,又被松島之十三寸大彈擊中數次,而曾無一彈之鉆入,死者亦不見其多”,皆證明它們是威力強大的海戰利器。日本以此二艦為最大威脅,嘆其為“東洋巨擘”,直到戰時也未獲得達到這樣威力的軍艦。
黃海大戰前的北洋海軍,從表面看軟件硬件都具有相當實力。清廷正是出于此種自信,才在豐島海戰之后毅然對日宣戰。
日本精心策劃了這場戰爭。但礙于北洋海軍,它也沒有必勝的把握。日本為勝利和失敗都做好了準備。所以如此,是感覺到自己海軍力量不足。
首先,日本海軍的投入少于滿清海軍。其次,聯合艦隊組建倉促。其三,艦只混雜,有的戰斗力甚弱。
大戰之前的中日海軍,總體看中方的優勢還稍大一些。但當戰場不再是操演場時,平日訓練的差異立即顯現。
面對逼近的敵艦,北洋艦隊首先在布陣上陷入混亂。提督丁汝昌的“分段縱列、掎角魚貫之陣”,到總兵劉步蟾傳令后,變為“一字雁行陣”;隨后針對日方陣列我方又發生齟齬,交戰時的實際戰斗隊形成了“單行兩翼雁行陣”;時間不長,“待日艦繞至背后時清軍陣列始亂,此后即不復能整矣”。這種混亂致使今天很多人還在考證,北洋艦隊到底用的什么陣形。
其次,還未進入有效射距,“定遠”艦首先發炮,不但未擊中目標,反而震塌主炮上的飛橋,丁汝昌從橋上摔下嚴重受傷,首炮就使北洋艦隊失去了總指揮。黃海大海戰持續四個多小時,北洋艦隊“旗艦僅于開仗時升一旗令,此后遂無號令”,一直在失去統一指揮的狀態下作戰。
第三是作戰效能低下,擊之不中,中之不沉。李鴻章平日夸耀北洋海軍“攻守多方,備極奇奧”、“發十六炮,中至十五”,在真槍實彈的戰場上煙消云散。有資料統計,黃海海戰日艦平均中彈11.17發,而北洋各艦平均中彈107.71發。對方火炮命中率高出我方9倍以上。
北洋艦隊官兵作戰異常英勇。其寧死不退、誓以軍艦共存亡之氣概,讓外籍雇員都留下深刻印象。但對軍人來說,勝利沒有替代品。戰場決定勝利,戰場不能孕育勝利。很多東西僅憑戰場上的豪壯不能獲得。最輝煌的勝利,只能孕育在最瑣碎枯燥、最清淡無味的承平里。
多種資料證明,北洋海軍在一片承平的環境中,軍風嚴重毒化。《北洋海軍章程》、清廷兵部的《處分則例》等形同虛設。
至于艦船不作訓練而用于它途,已不是個別現象。“南洋‘元凱、‘超武兵船,僅供大員往來差使,并不巡緝海面”;北洋則以軍艦走私販運,搭載旅客,為各衙門賺取銀兩。艦隊腐敗風氣蔓延,訓練中弄虛作假,欺上瞞下。
軍風腐敗的結果,戰時必然要付出高昂代價。力圖隱瞞這一代價,就要謊報軍情。直至全軍覆滅那一天,謊報軍情未曾中止。
有的謊報軍情,使作戰計劃都發生改變。1895年2月, 左一魚雷艇管帶王平駕艇帶頭出逃,至煙臺后先謊稱丁汝昌令其率軍沖出,再謊稱威海已失。陸路援兵得訊,撤消了對威海的增援。陸路撤援,成為威海防衛戰失敗的直接原因。
越是艱難處境,越考驗軍風、軍紀。北洋海軍在威海圍困戰后期,軍紀蕩然無存。
首先是部分人員不告而別。其次是有組織的大規模逃逸。最后發展到集體投降。
軍風至此,軍紀至此,不由不亡。(責任編輯/吳文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