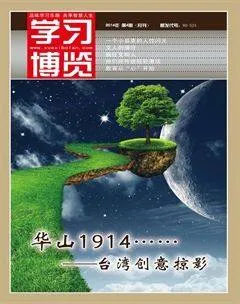華山1914……
臺灣,一塊文化創意蓬勃涌動的島嶼。
在這塊島嶼上,中華傳統文化﹑臺灣原住民文化﹑殖民時期遺留的歐洲和日本文化,以及戰后風行的歐美文化互相交匯和融合,在文化上形成多元并存的格局,為創意提供了極具異質性的文化基因。同時,隨著民主化進程的推進,自由開放氛圍的營造,政府管制的放松,人們得以百無禁忌地創新,甚至“敢想就會贏”。這塊島嶼,遂成為文化創意的沃土、華人世界創意人才的大本營。
尤值一提的是,在臺灣文化創意的成功案例中,很多都是既吸收了中華傳統文化的養分,又結合了最新的時尚元素和國際化的審美趣味。當文化的要素被巧妙地凝結到精致的日用器物之上或周圍環境之中,就有一種直指人心的力量,潛移默化地滋養精神,潤澤生活。
未來若干年,“中國制造”勢必轉向“中國創造”。人們豐衣足食之后,亦當求個心安理得。早行一步的“臺灣創意”,對我們或許不無啟迪。
華山1914:“酷自在創意聚落”
這里有周杰倫和劉謙合開的音樂魔術創意料理“Déjà vu”,店名取法文“似曾相識”之意,每晚均有魔術表演在此舉行;這里有庾澄慶開的“Legacy”,作為臺北音樂文化發聲基地,門前總是排著長長的人龍;這里有被規劃成跨界美學空間的獨立書店“好樣本事”,享有著“全世界最美的20家書店”之美譽;這里被稱為臺灣“出鏡最多的文創園區”,許多電影均在此取景。2006年,簡單生活節在這里掀起樸實生活的流行;2009年,漢字文化節在這里讓中華文化顯得如此親切;2010年,眾所矚目的臺灣設計師周在這里型塑未來的夢想;2012年,電影大師侯孝賢的光點電影院在這里發光……
這里,就是“華山1914”。
進入“華山1914”的大門,這里的建筑物都會立刻將視線緊緊攫住:傳統工法燒制的紅磚、被時光熬洗過的木門、窗戶、瓦片、隱沒在草地上的酒瓶。步入園區室內,只見挑高的空間、鑄鐵的欄桿、挖空圓洞的天花板,每一寸都有濃濃的歷史感……
在臺北所有的文創園區中,“華山1914”雖然面積不是最大,但卻是發展最早、營運最為成熟,同時也是人氣最旺的一處。臺灣著名私房菜“食養山房”的創辦人林炳輝則認為,華山1914“是臺北市難得的凈土,可以吸引忙碌的現代人來此沉淀、靜思、冥想”。
“華山”之名,源自此地在日據時期的地名“樺山町80番地”。“樺山”取自日本首任臺灣總督“樺山資紀”,在抗戰勝利后被改為“華山”。“1914”乃是這塊土地開始釀酒的年代,最先是兩個日本人修建的“芳釀社”,后來此地建造了臺灣最大的酒廠。1987年,酒廠搬遷,那些日據時期的制酒產業建筑群,自此荒廢十余年。1997年,一些藝術家意外發現此地,深感酒廠保有過去臺北產業與生活的空間記憶,非常適合成為一個與城市生活相結合的多元藝文展演空間。在各界人士的努力下,到1998年8月29日,“華山藝文特區”正式掛牌,成為公共空間。幾經變遷,2007年,在全面整修及公開招標后,全新的“華山文化創意產業園區”正式運營,被官方定位為推動臺灣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旗艦基地。
在公開招標中,ROT(Rehabilitate重建、Operation營運、Transfer轉移)部分由“臺灣文創發展基金會”經營。基金會董事長王榮文為華山定下獨有的基調:“酷自在創意聚落”。在華山,“文創”被界定為“就像一顆果實,文化是果核,創意是果肉”。“華山從酒廠出發,以文創轉身,而無論是酒廠或文創,都是‘緣于醞釀,成于分享”。
王榮文說,金庸筆下的華山,是江湖英雄比武論劍的擂臺;臺灣的華山,將是文創產業高手競飆創意的舞臺。他將“華山”描述為“世貿中心”“孵夢基地”“未來櫥窗”和“休憩勝地”。
在華山,人們不僅能看到最新銳的創意,也能看到最古老的傳統文化。這里有“約茶不夜”,一個臺灣茶文化的收藏聚落;也有“老叢茶園”,一個臺灣茶文化的孵育溫床,每年一度的“笑傲江壺展”已成茶藝界的盛事。位于大門旁的“1914 Connection”,是臺灣第一家當代設計師禮品專賣店,店內擺放地方原鄉時尚商品,涌動著臺灣文創的豐沛能量。還有一個叫“花草雨林”的地方,由李家維教授運用熱帶雨林的珍貴物種活體,營造前所未見的空間氛圍,展示出許多臺灣特有的物種,突顯出自然與人文的和諧永生……
在華山,還有很多稍不留神就會被錯過的風景:華山戶外劇場上,被民眾當作隨性歇腿的椅子是雕塑家楊柏林的青銅名作《島嶼系列》;在廣場旁的白千層樹陰下,由階梯、廣場與通道共同構成的“千層野臺”是建筑名家邱文杰設計的作品;順著階梯上到二樓,是“風潮音樂旗艦店”,它是臺灣規模最大的獨立唱片公司,常常有小型音樂會在此舉行。
如今,“酷”且“自在”的華山1914已經如王榮文預期般成為一個“跨領域創意玩咖群聚、生活的創意樞紐”。“未來的華山,終將成為一本大書、一個舞臺、一個風景、一所學校,讓每個人找到最適合的角色,盡情書寫、表演、體驗和學習”,這是王榮文的心愿。
臺北故宮:創意來自開放
以虛構的雍正皇帝后宮后妃爭寵為背景,電視劇《后宮·甄嬛傳》中一句“朕知道了”臺詞紅遍海峽兩岸。臺北故宮博物院在2013年7月推出同款的創意紙膠帶,膠帶上印有康熙皇帝朱批真跡“朕知道了”四個字,三卷一盒要價新臺幣200元,當天就被搶購一空,后來還幾度脫銷,日銷售量曾創臺北故宮文化創意商品新高,并在網上引發熱烈討論。
設想一下,這霸氣的“墨寶”粘貼在紙張或禮盒之上時,那封存之物立刻就有了歲月的色澤,又會因皇上的“一筆參與”而身價倍增。這些皇帝朱批紙膠帶“穩準狠”地抓住了年輕人的心理,既有文化歷史感,又能在實用的基礎上幽人一默。
“朕知道了”膠帶熱賣之際,有媒體翻出舊賬指出,買賣皇帝的朱批不算什么,臺北故宮可是連皇帝的臉面都敢賣。比如他們賣的一款便條紙叫“宗心為你”,是把館藏畫作里的唐玄宗頭像設計成卡通可愛版人物,三撇小胡子、兩個紅臉蛋,一下子把皇家氣象變為現代動漫。而用撅著小嘴的唐朝仕女卡通人像制作的另一款產品則叫做“想入妃妃”——這樣別致獨創的設計,即使是對唐朝文化不感興趣的人也會被吸引。
其實,相對于紅極一時的“朕知道了”,翠玉白菜系列才是故宮文創產品的常青樹。翠玉白菜的原件,是清代藝人巧妙地運用一塊一半灰白、一半翠綠的灰玉雕成,把綠色的部位雕成菜葉,白色的雕成菜幫,菜葉自然反卷,筋脈分明,綠葉上還停留著兩只寓意多子多孫的螽斯和蝗蟲。翠玉白菜受到游客的格外垂青,甚至成為臺北故宮的形象代表。圍繞翠玉白菜,相關文創衍生品達200多種,除了較為常見的仿制品擺件、鑰匙扣等,還有翠玉白菜造型的晶瑩剔透的U盤、可愛的“白菜頭”鉛筆、裝了一肚子特制臺灣蜜餞的“白菜罐”,乃至翠玉白菜傘,等等。2012年,該系列的文創產品的銷售額達到新臺幣1.4億元。
臺北故宮匯集了南京國立中央博物院、清代北京故宮、沈陽故宮和承德避暑山莊、中國青銅器之鄉寶雞等處舊藏之精華。65萬件收藏,不論是圖像、造型,還是工藝、故事,都是可供創作的元素。衍生文創商品大致分為三類,一種是精致優美的復制書畫、仿制器物,二是出版品及數碼出版品。而最受歡迎的,莫過于物美價廉、古典和現代元素完美結合的小玩意,包括掛飾、文具、生活用品等。這些小玩意完全打破了“老古董”可望不可及的刻板印象,走可愛、優雅,甚至夸張路線。例如,胖胖的清朝官員公仔造型的鹽罐,畫有《清明上河圖》的餐墊、行李吊牌,印有《蘭亭序》的iPhone手機外殼、購物袋,以明代宣德窯瓷器上的青花轉枝番蓮紋為主題設計的柔軟的羊毛鞋、羊毛皮筆記本,等等。
曾幾何時,臺北故宮也是“高高在上”,以至被民眾稱為“太廟”,只賣些簡單的文物復制品而已。2000年以來,臺北故宮文創產業才逐漸起步。2008年,周功鑫接掌臺北故宮博物院院長,力推“形塑典藏新活力,創造故宮新價值”的口號,利用藏品的豐富度與多樣性,研發可跟生活結合的實用物,藉此提升民眾的藝術素養與生活品味。
臺北故宮擁有大量的文創商品,卻沒有專門的文創團隊。創意從何而來呢?答曰:開放合作。方式主要有三種:首先是圖像授權,就是將故宮藏品圖像授權給有知名度和值得信賴的商家。其次是雙品牌,與知名品牌合作,在文創商品上標明臺北故宮與合作方的名字。第三,也是最有效的合作方式,就是開放征集設計方案。一是通過舉辦臺北故宮文物“衍生商品設計競賽”,向全社會公開征集優秀的文創提案。例如,頗受臺灣本地顧客青睞的“翠玉白菜傘”,就是由一位17歲的在校女生設計的,是2010年競賽的獲獎作品。二是商家自己提案,再由臺北故宮“文創開發商品審查委員會”審查。“審查委員會”由業界、專家和博物院有關人員組成,臺北故宮博物院內外人士各半。為此,臺北故宮還組成了一個40人的院外人力資源庫。這40個人都是各類文物方面的專家。依照文創商品所涉及的文物,從中挑選人員參加“審查委員會”。
目前,臺北故宮與90余家臺灣本土及國際知名廠商合作,已推出近2400種文創商品。2012年,臺北故宮禮品店收入達7.2億元新臺幣,甚至略高于門票收入。
雖然文創商品獲利頗豐,臺北故宮文創行銷處處長徐孝德卻表示:“我們不會為了賺錢而隨波逐流。”在“朕知道了”因《甄嬛傳》而爆紅之際,圍繞該劇衍生的“臣妾做不到啊!”“賤人就是矯情”等紙膠帶在市場上雖然也賣得紅火,但進不了臺北故宮的商店,因為臺北故宮所有文創商品都要跟典藏文物相關。徐孝德說,臺北故宮推動文化創意產業,其實是教育功能的延伸,“游客欣賞臺北故宮,感動之余買回文化商品,給人生留下紀念”。禮品的說明書會說明歷史背景、背后故事,“無形中,中華文化就會滲透到全球”。
法藍瓷:讓東方風味走紅世界
瓷藝發端于中國,有過“四大名窯”的輝煌,但近幾十年來卻顯得有些落寞。縱覽世界陶瓷市場,歐洲名窯可謂后來居上。中國出口的陶瓷,多為價格便宜的中低檔產品,徘徊在高端消費市場之外。
面對此境,陳立恒說,中國人要把失去的光輝搶回來。他認為,中國陶瓷之所以淪為地攤貨,技術不是問題,主要輸在設計和創意上。但只要有好的學習對象,臺灣的創意一點都不輸給外國。2001年,他在其家族企業臺灣海暢實業旗下,創建“法藍瓷”品牌——這個有點歐化的品牌名,來自陳立恒的德文名Franz。
推出不久,“法藍瓷”品牌初試啼聲,以一套蝶舞系列,一舉拿下2002年紐約禮品展“年度最佳收藏品獎”。在這個系列中,設計師何振武從敦煌飛天壁畫中的天女彩帶得到靈感,轉化為羽化后的蝴蝶彩翼,在杯盤上翩翩起舞。“蝶舞”系列最成功之處在于中國人看到瓶身上的這對彩翼,會聯想到敦煌的飛天;但同樣的彩翼,西方人看到后,就像看到希臘神話中維納斯雕像上的雙翼。“法藍瓷在設計上的優勢,就是東方人看起來像東方,西方人看起來像西方。”短短一句話,道盡了法藍瓷的設計精髓。
此后,在創意之路上,法蘭瓷越走越嫻熟。
比如,在西方文化里,瓢蟲是幸運的象征。法蘭瓷借此設計制作了一套名為“飄然忘憂”的產品,全套產品由瓷瓶、茶壺、椒鹽罐、燭臺等構成,嬌俏可愛的小瓢蟲與雛菊相配,淡雅而有情趣,推向市場后很受消費者歡迎。
“福海騰達”的設計構想,則來自于皇帝龍袍上的圖騰,其中蝙蝠代表福氣、海水江牙則代表山河版圖,把帝王貴氣在一張餐桌上展露無遺。將郎世寧的工筆畫和康熙皇帝的龍袍在日常生活中的瓷器上面復活,這種“古舊時尚”成為法藍瓷的新創意源頭。陳立恒認為,東方風味要在全世界走紅,品牌就必須深刻理解和借助中國的文化資產。
近年來,法藍瓷業績增長大好,全球跨界合作也是其重要法寶。在美國市場,法藍瓷一個令人意想不到的渠道就是迪斯尼樂園。大小朋友都對《愛麗絲夢游仙境》的主題茶壺、彼得·潘與小鹿班比造型的瓷杯瓷盤贊不絕口。在歐洲,法藍瓷則出入時尚圈。近三年為Lanvin打造的多款美女瓷偶,在巴黎時裝周造成大轟動。
“要用活在當下的心情去打造傳統產業。”陳立恒說。在他看來,瓷器并不是只放在櫥窗里供收藏的觀賞品,也可以用于日常生活之中。法藍瓷的設計中,似乎無不可以入瓷。陳立恒設計制作了陶瓷椅背、陶瓷吧臺、陶瓷壁爐墻壁,他的下一個目標甚至是陶瓷手機。
面對未來,陳立恒說要打造“世界新名窯”,占據世界陶瓷藝術的制高點。他自信,即便人類滅絕,外星人來到地球挖出法藍瓷時,也會“非常驚訝”。他還清楚地記得,有一次,一個德國朋友由衷對他說:“感謝你們中國人,發明了瓷器,當我們德國人還在用木盤子、鐵盤子盛東西吃時,是你們帶來了中國的瓷器,讓我們變得溫文爾雅。”
琉璃工房:“創作有益人心的作品”
2001年,第73屆奧斯卡獎。
臺上,華裔導演李安執導的中國電影《臥虎藏龍》,一舉奪得四項奧斯卡獎桂冠。臺下,中國藝術家張毅、楊惠姍夫婦創作的一組題為《將進酒——古風六品》的琉璃藝術品,破天荒進入了奧斯卡嘉賓的禮品籃,成為這屆頒獎儀式的一大熱門話題。這是一組由六個不同色彩、細部處理各異的酒杯組成的系列作品,分別名為《遨天》《清和》《舞羽》《嘯風》《品樂》《閑情》。酒杯古樸卻不失典雅的造型,脫胎于中國古代酒器之一的“斛”。而材質,則也是在兩千多年前的中國就已經出現過并且風光一時的琉璃。而這些藝術品的設計者,亦曾是電影界的風云人物,讓人不禁感嘆世事之奇妙輪回。
二十多年前的張毅和楊惠姍,一個是金馬獎最佳導演,一個是金馬獎影后,在臺灣電影界名重一時。1987年,他們合作一部電影時,第一次接觸到琉璃藝術品的道具。兩人幾乎同時感悟到,這通體透明光影永恒的琉璃,應該是承載他們終生情感最好的載體。
就在那一年,他們在臺灣淡水創辦琉璃工房。對琉璃工藝幾乎一竅不通的影壇夫妻,在創業初期一味學習西方,經歷多次失敗,曾負債高達7500萬新臺幣。后來,得益于一位日本專家的提點,他們決定將琉璃工房的風格指向中國傳統文化,從傳統文化中挖掘靈感。在這一思路下,他們相繼創作出“敦煌——人間八千億萬佛”“天地之間”“松竹月影”“生生不息”“大圓融歡喜”等系列作品。強烈的傳統中國語言融合了現代思想,加以琉璃脫臘鑄造技術的高度掌握,為國際琉璃藝術界提供新的視野,引發強烈反響。
如何讓琉璃走入現代生活?這也是張毅和楊惠珊一直在思考的問題。楊惠珊開發出以琉璃為主要材質的首飾品牌——“觀念佩飾”,推出的每一系列首飾都有一個特別的主題,如“不會因為你而改變我的樣子”系列,表達對擁有自主性格、特立獨行的美國知名女畫家歐基芙的敬意;“打開心里的窗戶,讓陽光進來”系列,以海倫·凱勒的故事激勵女性追尋生命的陽光。“如果有一些作品,能將女性在人生歷程中深刻的情懷表達出來,一定很美好。我期許觀念佩飾帶給女性朋友更多的是一種心靈的力量。” 楊惠珊說。
從2001年開始,琉璃工房將琉璃與其他材質如陶瓷、木頭等結合,開發創意家居產品。“我們不斷從材質出發,探索琉璃在現代生活中設計的種種可能,超越琉璃在裝飾性與工藝性上的表現,將文化生活融入衣食住行中。”張毅說。“透明思考”餐廳就是楊慧珊和張毅的探索成果。這家餐廳從屋頂、墻飾、地板,到客人所使用的餐具等都與琉璃有關。
面對傳統文化的斷層,張毅和楊惠姍思考著如何將屬于中國人的情感和故事,用琉璃工藝語言表現出來。他們認為:“每一件琉璃工房的作品,不僅僅是工藝美術品,它更是一個載體,承載著情感。”“基本上,我們不判斷市場的商業動向。我們希望從心靈上,從精神上,情感上,做市場的支持。我們經常提醒自己,設計如果只是設計,沒有深入的意義,充其量那只是‘造型。” 他們要“永遠不斷地創作有益人心的作品”,“努力地在美感需求下,架構一個安詳的社會”。
食養山房:“以貼近自然為本意”
年輕時,學制圖的林炳輝是一名小建筑商人,在工地忙進忙出,為的是償還宜蘭老家的債務。環境壓力讓他喘不過氣來。生意不順,公司停業,他來到新店山中,租一間鐵皮屋,且住著喘息喘息。
一次偶然機緣,在國小任校長的朋友請林炳輝為二十多位教職員做一餐飯。從來沒進過廚房的他,以“招待朋友”的心情接下邀約,反應卻出乎意料地好。愈來愈多的朋友“請他作餐”,鐵皮屋也被朋友們裝點成古意盎然的食飲空間。“食養山房”的雛形,就這么有意無意地形成了。
1996年,食養山房在臺北縣烏來成立。2005年12月,因為人氣太好,烏來店結束營業,搬到陽明山松園舊址。2009年,再度因為人氣太好,松園店結束營業,搬到更為偏遠的新北市汐止深山之中。
“生意一好,我就覺得工作無趣味了,就是為了賺錢,沒有人生的樂趣,所以就關了第一期、第二期的食養山房。” 林炳輝說。經營多年后,他不再想要庭院,想要所謂“美的空間”,而只想要一塊“干凈”的地方。這片被遺忘在荒野之中的山谷,他一看就很喜歡。
林炳輝最大限度地保持了山谷的自然風貌,無論是空間還是風格,一切以貼近自然為本意。他不鋪石頭道路,不除草,只順著河流勉強建造了一條人行步道而已。最主要的餐廳建筑群,只是利用農民舊有的石頭房子略加改造,就像這里的植物一樣,是慢慢長出來的。他在屋外面加寬了長廊,整個就餐空間多了一倍。將屋頂利用起來,做成了二樓的就餐區域。建筑材料延續當地的風格,石頭、鋼鐵、竹子,素到缺乏特征。舊石墻也只做了消毒。他添加的裝飾就是舊家具和燭臺,外加陶瓶里插的鮮花。一有客人,燭臺立刻點燃:“別小看蠟燭光,它是最好的裝飾品之一。”
雖然山房離臺北市區有數小時車程,各地藝文人士、高官貴族卻爭相前往,還需提前幾周預約。山房并無菜單,賓客只需在預約時選擇葷素套餐,剩下的就一切“聽候發落”。店家會根據當季、當天的食材決定菜單。從烹調的方式、食物顏色、造型的搭配到器皿的選擇,處處獨具匠心。有一道壓軸菜叫“蓮花羹”,在蓮子、藕和蘑菇燉成的濃湯端上來的瞬間,把一朵夏天采摘的干蓮花放進去,蓮花靜靜地一瓣瓣綻放,直至完全盛放在湯水間,驚艷堪比曇花一現。一頓飯下來,著實吃了“一朵花開的時間”。
如今,林炳輝已不太操心具體事務。“食養”積攢了一批忠實的追隨者:一開始是大學生來打工,慢慢喜歡上這里的生活,每日喝茶、誦經,食物清淡,位置又在“隔斷紅塵三十里”的山中,他們覺得這不僅是一份工作,而是一種生活方式,或者說是一種修行。
在這個“成功就是找到一種成功的方式并且不斷復制”的年代,林炳輝似乎并沒有那么大的“野心”。他只以真正來自生活體驗的創意,安靜地沉淀累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