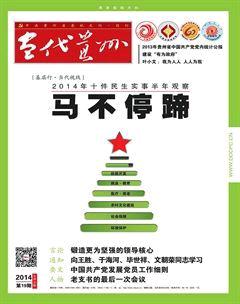勃列日涅夫是扼殺改革的“衛(wèi)道者”
赫魯曉夫被“宮廷政變”廢黜,柯西金因遭強勢利益集團擠兌被迫辭職,戈爾巴喬夫從“改革”到“改制”,蘇聯(lián)歷史上這三個重要改革者的結局,都與一個人有關,就是勃列日涅夫。如果說他在改革上無所作為,但在扼殺改革上卻是頗有“建樹”的:他參與搞陰謀,顛覆了一個敢想敢干的赫魯曉夫;通過打擊排擠,壓垮了一個溫文爾雅的柯西金;他把國家拖到一團糟的地步,使接手者不改革不行,改革也不行,逼出了一個章法大亂的戈爾巴喬夫。結果沒過幾年,蘇聯(lián)這個“大廈”就坍塌了。但與其把勃列日涅夫看作一個人、一個政治領袖,不如更準確地說,把他看作具有超強頑固性的蘇聯(lián)傳統(tǒng)體制的化身,一個既得利益集團的代表,更為合適。因為在這些人眼里,任何改革都是沒有必要的。在現(xiàn)有體制結構下,他們已經(jīng)實現(xiàn)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改革只會使他們失去已到手的東西,而不會給他們帶來更多利益。因此,所有與改革有關的主張,他們都予以封殺。蘇聯(lián)政治生活日益走向保守的特點,在勃列日涅夫身上淋漓盡致地反映出來。
勃列日涅夫與斯大林、赫魯曉夫、戈爾巴喬夫一樣,都是純正的無產(chǎn)階級出身。勃列日涅夫曾長期從事基層工作,搞過農(nóng)業(yè)和工業(yè),從區(qū)土地處主任開始,一個臺階一個臺階地上升到更高的職務。個人履歷可以說無可挑剔,在“山頭”眾多的蘇共領導集團中,是個容易被各方面都當作“自己人”來接受的人。他從不喜歡出頭,看問題和辦事都中規(guī)中矩,并選擇站在領導集團大多數(shù)一邊。他深知,在蘇聯(lián)現(xiàn)行體制下,有沒有像列寧那樣領導全黨正確前進的遠見卓識,在權力交替階段并不重要。而咄咄逼人、鋒芒畢露,更是一種“政治不成熟”的表現(xiàn)。
勃列日涅夫深知,盡管很多蘇共領導人都口口聲聲講要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但都清楚,保證黨的領導層的擁護和支持,比什么都重要。赫魯曉夫被趕下臺的主要原因,就是實施干部任期制與輪換制度改革,得罪了一大片。勃列日涅夫上臺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廢除了蘇共中央和地方黨委會每次改選必須更換1/3成員的規(guī)定,同時也就順理成章地鞏固了自己的領導職務終身制。
勃列日涅夫對人溫和,不粗暴,注意外表禮貌,使大家覺得和善可親,容易博得周圍和下面人的好感。他對下面干部一般都不提嚴格要求,有的干部在一個地方因犯錯誤被撤職,但很快就能異地復出。中央部門的高級干部犯了錯誤,就派他出任大使,到國外避一陣風頭再調(diào)回來重新重用。有時為了安排某個人,甚至專門新設一個同級別的部門,等等。勃列日涅夫這種“菩薩心腸”,使得赫魯曉夫時期每天惶恐不安的干部感激不盡。大家交口稱贊、都擁護他長期擔任最高領導人。
勃列日涅夫穩(wěn)定干部的政策, 從積極方面講,有利于干部制定長期計劃,踏實做事,而不是總想著如何升遷;從消極方面看,能進不能出,能上不能下,能官不能民,也導致不少干部沒有危機感,整天無所事事、養(yǎng)尊處優(yōu)。而年老力衰的干部長期占據(jù)領導崗位,不能正常工作也不讓位,使許多精力充沛、年富力強、德才兼?zhèn)洹㈤_拓進取的中青年干部卻因沒有崗位空缺失去用武之地,必然導致干部隊伍失去生機和活力。
當然,勃列日涅夫一上臺就強調(diào)要穩(wěn)定干部隊伍,主要為籠絡住那些已經(jīng)晉身領導層的成員。站穩(wěn)腳跟后,他也開始用“自己的人”逐步取代原來的“統(tǒng)戰(zhàn)對象”。
勃列日涅夫行事謹慎,是個各方面都很平庸、功勞不多但過錯也較少的人。他當政后最突出的執(zhí)政風格,就是墨守成規(guī),不急不忙,三思而后行。他認為“與其做無用功,不如維持現(xiàn)狀”。于是求穩(wěn)怕變,就成為勃列日涅夫執(zhí)政時代的基本特征。
從勃列日涅夫1964年取代赫魯曉夫上臺執(zhí)政,到l982年在臺上病逝,執(zhí)政時間占整個蘇聯(lián)歷史的近1/4,僅次于執(zhí)政30年的斯大林。從表面上看,國家保持了前所未有的穩(wěn)定,但也正是在這18年中,積累了大量的政治、經(jīng)濟和社會問題,使蘇聯(lián)走向停滯。盡管進行根本性改革已刻不容緩,改革的客觀條件也更為成熟,但凡是想改革傳統(tǒng)體制、給蘇共和蘇聯(lián)注入新的活力的人,都被勃列日涅夫這個傳統(tǒng)體制的“衛(wèi)道者”打敗了。結果在一片歌舞升平中,曾經(jīng)取得過輝煌成就的蘇聯(lián),從發(fā)展的頂峰跌落下來。因此有人說,勃列日涅夫才是蘇共真正的掘墓人。(責任編輯/吳文仙)
赫魯曉夫被“宮廷政變”廢黜,柯西金因遭強勢利益集團擠兌被迫辭職,戈爾巴喬夫從“改革”到“改制”,蘇聯(lián)歷史上這三個重要改革者的結局,都與一個人有關,就是勃列日涅夫。如果說他在改革上無所作為,但在扼殺改革上卻是頗有“建樹”的:他參與搞陰謀,顛覆了一個敢想敢干的赫魯曉夫;通過打擊排擠,壓垮了一個溫文爾雅的柯西金;他把國家拖到一團糟的地步,使接手者不改革不行,改革也不行,逼出了一個章法大亂的戈爾巴喬夫。結果沒過幾年,蘇聯(lián)這個“大廈”就坍塌了。但與其把勃列日涅夫看作一個人、一個政治領袖,不如更準確地說,把他看作具有超強頑固性的蘇聯(lián)傳統(tǒng)體制的化身,一個既得利益集團的代表,更為合適。因為在這些人眼里,任何改革都是沒有必要的。在現(xiàn)有體制結構下,他們已經(jīng)實現(xiàn)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改革只會使他們失去已到手的東西,而不會給他們帶來更多利益。因此,所有與改革有關的主張,他們都予以封殺。蘇聯(lián)政治生活日益走向保守的特點,在勃列日涅夫身上淋漓盡致地反映出來。
勃列日涅夫與斯大林、赫魯曉夫、戈爾巴喬夫一樣,都是純正的無產(chǎn)階級出身。勃列日涅夫曾長期從事基層工作,搞過農(nóng)業(yè)和工業(yè),從區(qū)土地處主任開始,一個臺階一個臺階地上升到更高的職務。個人履歷可以說無可挑剔,在“山頭”眾多的蘇共領導集團中,是個容易被各方面都當作“自己人”來接受的人。他從不喜歡出頭,看問題和辦事都中規(guī)中矩,并選擇站在領導集團大多數(shù)一邊。他深知,在蘇聯(lián)現(xiàn)行體制下,有沒有像列寧那樣領導全黨正確前進的遠見卓識,在權力交替階段并不重要。而咄咄逼人、鋒芒畢露,更是一種“政治不成熟”的表現(xiàn)。
勃列日涅夫深知,盡管很多蘇共領導人都口口聲聲講要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但都清楚,保證黨的領導層的擁護和支持,比什么都重要。赫魯曉夫被趕下臺的主要原因,就是實施干部任期制與輪換制度改革,得罪了一大片。勃列日涅夫上臺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廢除了蘇共中央和地方黨委會每次改選必須更換1/3成員的規(guī)定,同時也就順理成章地鞏固了自己的領導職務終身制。
勃列日涅夫對人溫和,不粗暴,注意外表禮貌,使大家覺得和善可親,容易博得周圍和下面人的好感。他對下面干部一般都不提嚴格要求,有的干部在一個地方因犯錯誤被撤職,但很快就能異地復出。中央部門的高級干部犯了錯誤,就派他出任大使,到國外避一陣風頭再調(diào)回來重新重用。有時為了安排某個人,甚至專門新設一個同級別的部門,等等。勃列日涅夫這種“菩薩心腸”,使得赫魯曉夫時期每天惶恐不安的干部感激不盡。大家交口稱贊、都擁護他長期擔任最高領導人。
勃列日涅夫穩(wěn)定干部的政策, 從積極方面講,有利于干部制定長期計劃,踏實做事,而不是總想著如何升遷;從消極方面看,能進不能出,能上不能下,能官不能民,也導致不少干部沒有危機感,整天無所事事、養(yǎng)尊處優(yōu)。而年老力衰的干部長期占據(jù)領導崗位,不能正常工作也不讓位,使許多精力充沛、年富力強、德才兼?zhèn)洹㈤_拓進取的中青年干部卻因沒有崗位空缺失去用武之地,必然導致干部隊伍失去生機和活力。
當然,勃列日涅夫一上臺就強調(diào)要穩(wěn)定干部隊伍,主要為籠絡住那些已經(jīng)晉身領導層的成員。站穩(wěn)腳跟后,他也開始用“自己的人”逐步取代原來的“統(tǒng)戰(zhàn)對象”。
勃列日涅夫行事謹慎,是個各方面都很平庸、功勞不多但過錯也較少的人。他當政后最突出的執(zhí)政風格,就是墨守成規(guī),不急不忙,三思而后行。他認為“與其做無用功,不如維持現(xiàn)狀”。于是求穩(wěn)怕變,就成為勃列日涅夫執(zhí)政時代的基本特征。
從勃列日涅夫1964年取代赫魯曉夫上臺執(zhí)政,到l982年在臺上病逝,執(zhí)政時間占整個蘇聯(lián)歷史的近1/4,僅次于執(zhí)政30年的斯大林。從表面上看,國家保持了前所未有的穩(wěn)定,但也正是在這18年中,積累了大量的政治、經(jīng)濟和社會問題,使蘇聯(lián)走向停滯。盡管進行根本性改革已刻不容緩,改革的客觀條件也更為成熟,但凡是想改革傳統(tǒng)體制、給蘇共和蘇聯(lián)注入新的活力的人,都被勃列日涅夫這個傳統(tǒng)體制的“衛(wèi)道者”打敗了。結果在一片歌舞升平中,曾經(jīng)取得過輝煌成就的蘇聯(lián),從發(fā)展的頂峰跌落下來。因此有人說,勃列日涅夫才是蘇共真正的掘墓人。(責任編輯/吳文仙)
赫魯曉夫被“宮廷政變”廢黜,柯西金因遭強勢利益集團擠兌被迫辭職,戈爾巴喬夫從“改革”到“改制”,蘇聯(lián)歷史上這三個重要改革者的結局,都與一個人有關,就是勃列日涅夫。如果說他在改革上無所作為,但在扼殺改革上卻是頗有“建樹”的:他參與搞陰謀,顛覆了一個敢想敢干的赫魯曉夫;通過打擊排擠,壓垮了一個溫文爾雅的柯西金;他把國家拖到一團糟的地步,使接手者不改革不行,改革也不行,逼出了一個章法大亂的戈爾巴喬夫。結果沒過幾年,蘇聯(lián)這個“大廈”就坍塌了。但與其把勃列日涅夫看作一個人、一個政治領袖,不如更準確地說,把他看作具有超強頑固性的蘇聯(lián)傳統(tǒng)體制的化身,一個既得利益集團的代表,更為合適。因為在這些人眼里,任何改革都是沒有必要的。在現(xiàn)有體制結構下,他們已經(jīng)實現(xiàn)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改革只會使他們失去已到手的東西,而不會給他們帶來更多利益。因此,所有與改革有關的主張,他們都予以封殺。蘇聯(lián)政治生活日益走向保守的特點,在勃列日涅夫身上淋漓盡致地反映出來。
勃列日涅夫與斯大林、赫魯曉夫、戈爾巴喬夫一樣,都是純正的無產(chǎn)階級出身。勃列日涅夫曾長期從事基層工作,搞過農(nóng)業(yè)和工業(yè),從區(qū)土地處主任開始,一個臺階一個臺階地上升到更高的職務。個人履歷可以說無可挑剔,在“山頭”眾多的蘇共領導集團中,是個容易被各方面都當作“自己人”來接受的人。他從不喜歡出頭,看問題和辦事都中規(guī)中矩,并選擇站在領導集團大多數(shù)一邊。他深知,在蘇聯(lián)現(xiàn)行體制下,有沒有像列寧那樣領導全黨正確前進的遠見卓識,在權力交替階段并不重要。而咄咄逼人、鋒芒畢露,更是一種“政治不成熟”的表現(xiàn)。
勃列日涅夫深知,盡管很多蘇共領導人都口口聲聲講要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但都清楚,保證黨的領導層的擁護和支持,比什么都重要。赫魯曉夫被趕下臺的主要原因,就是實施干部任期制與輪換制度改革,得罪了一大片。勃列日涅夫上臺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廢除了蘇共中央和地方黨委會每次改選必須更換1/3成員的規(guī)定,同時也就順理成章地鞏固了自己的領導職務終身制。
勃列日涅夫對人溫和,不粗暴,注意外表禮貌,使大家覺得和善可親,容易博得周圍和下面人的好感。他對下面干部一般都不提嚴格要求,有的干部在一個地方因犯錯誤被撤職,但很快就能異地復出。中央部門的高級干部犯了錯誤,就派他出任大使,到國外避一陣風頭再調(diào)回來重新重用。有時為了安排某個人,甚至專門新設一個同級別的部門,等等。勃列日涅夫這種“菩薩心腸”,使得赫魯曉夫時期每天惶恐不安的干部感激不盡。大家交口稱贊、都擁護他長期擔任最高領導人。
勃列日涅夫穩(wěn)定干部的政策, 從積極方面講,有利于干部制定長期計劃,踏實做事,而不是總想著如何升遷;從消極方面看,能進不能出,能上不能下,能官不能民,也導致不少干部沒有危機感,整天無所事事、養(yǎng)尊處優(yōu)。而年老力衰的干部長期占據(jù)領導崗位,不能正常工作也不讓位,使許多精力充沛、年富力強、德才兼?zhèn)洹㈤_拓進取的中青年干部卻因沒有崗位空缺失去用武之地,必然導致干部隊伍失去生機和活力。
當然,勃列日涅夫一上臺就強調(diào)要穩(wěn)定干部隊伍,主要為籠絡住那些已經(jīng)晉身領導層的成員。站穩(wěn)腳跟后,他也開始用“自己的人”逐步取代原來的“統(tǒng)戰(zhàn)對象”。
勃列日涅夫行事謹慎,是個各方面都很平庸、功勞不多但過錯也較少的人。他當政后最突出的執(zhí)政風格,就是墨守成規(guī),不急不忙,三思而后行。他認為“與其做無用功,不如維持現(xiàn)狀”。于是求穩(wěn)怕變,就成為勃列日涅夫執(zhí)政時代的基本特征。
從勃列日涅夫1964年取代赫魯曉夫上臺執(zhí)政,到l982年在臺上病逝,執(zhí)政時間占整個蘇聯(lián)歷史的近1/4,僅次于執(zhí)政30年的斯大林。從表面上看,國家保持了前所未有的穩(wěn)定,但也正是在這18年中,積累了大量的政治、經(jīng)濟和社會問題,使蘇聯(lián)走向停滯。盡管進行根本性改革已刻不容緩,改革的客觀條件也更為成熟,但凡是想改革傳統(tǒng)體制、給蘇共和蘇聯(lián)注入新的活力的人,都被勃列日涅夫這個傳統(tǒng)體制的“衛(wèi)道者”打敗了。結果在一片歌舞升平中,曾經(jīng)取得過輝煌成就的蘇聯(lián),從發(fā)展的頂峰跌落下來。因此有人說,勃列日涅夫才是蘇共真正的掘墓人。(責任編輯/吳文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