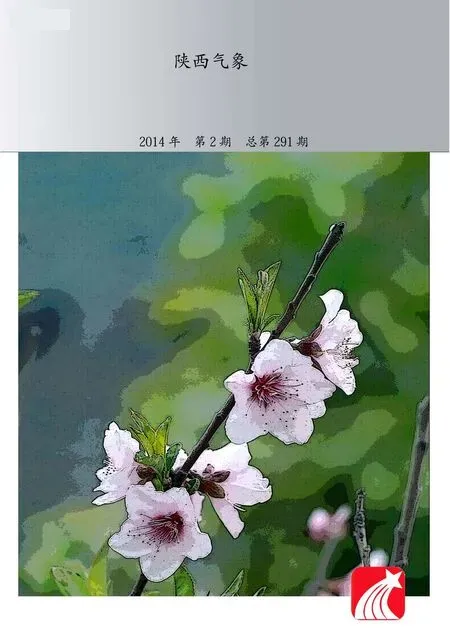青藏高原東北側地區暴雨特征分析
侯建忠,權衛民,潘留杰,劉海軍
(1.陜西省氣象臺,西安 710014;2.延安市氣象局,陜西延安 716000;3.陜西省氣象局, 西安 710014)
青藏高原東北側地區暴雨特征分析
侯建忠1,權衛民2,潘留杰1,劉海軍3
(1.陜西省氣象臺,西安 710014;2.延安市氣象局,陜西延安 716000;3.陜西省氣象局, 西安 710014)
利用統計方法,對比分析青藏高原東北側甘肅、陜西、寧夏和青海四省區1961—2008年的暴雨時空分布特征及地形影響。結果表明:本地區暴雨年頻次變化存在3 a和6 a兩個顯著周期;暴雨的空間分布具有“三高兩低”的特征,地理分布受地形影響明顯,多暴雨區域均發生在迎風坡及河川喇叭口輻合地帶;年度內的第一場較大范圍的區域性暴雨較早出現時對該年度暴雨偏多有一定指示意義,即當年內首場暴雨落區偏北或偏西時,預示著該年度暴雨的落區會出現相對偏北或偏西分布;相關結論和規律能為人們趨利避害、防洪減災提供一定借鑒。
青藏高原東北側;暴雨;時空分布特征
西北地區是我國降水量最少的地方,降水量的特點是東南多西北少,降水量自東南向西北迅速減少。而位于青藏高原東北側的甘肅、陜西、青海和寧夏等地區,暴雨的發生率較高,短時暴雨的極值更是接近國內極值[1-2],給當地的國民經濟和人民生命財產造成了巨大的災害和損失;另一方面暴雨對緩解西北地區農業干旱、水庫蓄水和水力發電又極為有利,暴雨多的年份,特別是區域性暴雨偏多時,往往降雨也多,農業收成好[3]。因此對該地區的暴雨氣候特征進行分析研究,為人們趨利避害、防洪減災以及預報此類天氣提供氣候背景。
1 暴雨標準和資料說明
按照中國氣象局全國暴雨日降雨量標準,當某區域內有一站日降水量大于等于50 mm或有一站大于等于100 mm時,分別定義為該區域的一個暴雨日或有一個大暴雨日(單位為次)。由于是分析青藏高原東北側地區的暴雨特征,對測站的選取作了一定的取舍,其中陜西、寧夏包括境內所有測站,甘肅、青海則分別選擇武威以東的所有測站和青海湖以東地區的所有測站,共涉及到該地區212個測站,基本涵蓋了青藏高原東北側的所有地區,具有廣泛的代表性。分別對1961—2008年共48 a間各省和青藏高原東北側地區逐日的降水量資料(本文以20—20時統計,下同)進行分析,以利于其結果進一步的比較和使用。
2 暴雨的年際特征
資料分析顯示,在過去的48 a中,青藏高原東北側的地區出現暴雨1 324次,年均27.6次。其中陜西年均26次、甘肅年均7次、寧夏年均3次、青海年均不足1次。發生次數最多的年份是1964年為42次,最少的是1986年僅有16次;其年際間變化差異很大,最多年份與最少年份暴雨相差約3倍。
20世紀80年代初期為青藏高原東北側暴雨的高峰期,21世紀初至2007年則為次峰期;20世紀90年代中期和60年代中期則為第三和第四峰期(圖1),與一些研究結論[4]基本一致。青藏高原東北側地區暴雨的站次變化(圖略)比其暴雨年頻次變化更加明顯和更具有規律性,暴雨的年頻次和站頻次變化在年代、年際變化上與陜西十分相似,與甘肅有一定的趨同性(圖1),但寧夏暴雨的年頻次變化有時為相反狀態,如本世紀初至2008年基本為一個低值區(圖1),這可能是其地域偏北的緣故。對青藏高原東北側及各省份暴雨的年頻次和站頻次變化利用Schuster周期圖[5]進行周期分析,結果發現青藏高原東北側及各省區暴雨的年頻次和站頻次變化共同存在約為3 a和6 a兩個周期,不同的省份還分別存在約8 a、9 a和20 a幾個不同的周期。其F檢驗值均通過信度0.01的顯著性檢驗。事實上青藏高原東北側暴雨周期與陜西年降水周期基本吻合[6]。

圖1 1961—2008年青藏高原東北側及各省區暴雨年頻次變化
3 暴雨的月、旬分布特征
3.1 月分布特征
統計顯示:青藏高原東北側的暴雨在2—11月均可出現(見表1),存在著一定的階段性,暴雨主要集中在7、8月,分別約占全年的33%、30%,各個區域間既有聯系又有區別。偏西偏北區域出現暴雨的時間跨度相對集中和縮短,這種特征隨著地理位置向西或向北表現更加明顯。青海和寧夏地區尤為突出,7、8月的暴雨分別占全年的是32%、65%和39%、44%,且以8月為年內最大值。對比陜西與該地區的暴雨月分布可以發現,陜西與該區域的暴雨分布非常相似,表明陜西暴雨在該區域內的權重偏強,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其他地區的特征。這一點從該區域的暴雨極值事件更能說明情況,如該區最早暴雨日期為2004年2月20日(藍田51.0 mm、洋縣54.0 mm),最遲為1994年11月13日(漢中、安康市的8個測站),均出現在陜西,陜西最大暴雨日降水紀錄出現在2003年8月29日(寧陜304.5 mm),最多年份為1983年共179站,最大區域性暴雨過程為1998年7月7日的43站暴雨。而青海東部地區最早為1987年6月20日(河南59.6 mm),最晚為1985年10月18日(托托河站50.2 mm),最大暴雨日降水紀錄出現在1963年7月23日尖扎站75.5 mm。寧夏最早暴雨為1967年5月16日(涇源62.6mm),最晚為1996年9月28日(涇源54.0 mm),最大暴雨日降水紀錄出現在1973年8月9日石嘴山測站為132.9 mm,最多年份為2002年共14站,最大區域性暴雨過程為2002年6月8日的10站暴雨。甘肅最早暴雨日為2003年4月1日(慶陽50.5 mm),最遲為2002年10月18日(武山57.7 mm),最大暴雨日降水紀錄出現在1966年7月26日慶陽測站為190.2 mm,最多年份為1970年共41站,最大區域性暴雨過程為1970年6月8日的18站暴雨。表明幾個省份各有其特點,而且最遲暴雨時間多在10月中下旬,但最早暴雨出現時間相差約4個月左右。
對該區域不同年份內較早發生暴雨的時間、落區、范圍及強度對比發現,當年內第一場較大范圍的暴雨較常年出現偏早時或接近常年時間時,該地區當年暴雨則相應較多,如:1960年、1964年、1965年、1978年、1983年、1998年均在5月底出現了區域性暴雨,其相應年份暴雨日均較多,同時當年的年降水量均屬正常偏多。當年內第一場暴雨較常年出現偏早或接近常年,暴雨落區偏北或偏西時,則預示著該年度暴雨的落區將較常年偏北或偏西。如:1961年、1970年、1973年、1990年、1991年、1996年、1981年、2002年、2003年和2005年,其年內的第一場暴雨均出現在秦嶺以北的關中地區或甘肅境內,相應年份甘肅、寧夏或陜西關中地區均為暴雨偏多年份,甚至是洪澇較重年份,表明該年度雨帶(即暴雨)偏北或偏西。這可能與高原季風及東亞季風活動有關[7-8]。這一結果對長期預報及氣候預測具有一定參考價值。

表1 青藏高原東北側暴雨月、旬分布特征 次
3.2 旬分布特征
在旬分布上,青藏高原東北側的暴雨有多峰值特點。7月下旬為暴雨出現的第一高峰期,也是全年的最大峰值。最大峰值存在地區差異(見表1),其中陜西、甘肅均出現在7月下旬,青海為8月上旬,寧夏則為7月下旬和8月上旬。次峰值較為分散,除陜西7月上旬的特征相對明顯外,甘肅的7月中旬和8月上旬、中旬的頻次較為接近,寧夏的7月中旬和8月中旬頻次較接近。青海有所后推,在7月下旬和8月中旬、下旬的頻次幾乎相當。從天氣影響系統來講,該地區的降水主要受副熱帶高壓位置影響,而7月副熱帶高壓北側的雨帶正好北移至西北地區東部,且7月中旬至8月中旬副熱帶高壓的位置南北變化不大,其移動大體多為略有西伸或東退,這就形成了青藏高原東北側的地區7月下旬到8月中旬的多暴雨時段。
4 暴雨的日變化特征
青藏高原東北側地區的暴雨具有明顯的日變化。從統計結果來看,大部分過程為午后到傍晚前后開始有降水,在夜間形成暴雨或降雨量較大,次日上午到中午雨勢減弱。降水往往在3~6 h、甚至1~2 h以內就達到區域性暴雨和大暴雨的強度[9]。如1991年7月28日陜北、關中的一次突發性暴雨,西安站日雨量達111.0 mm,創下建站以來新記錄,降水則主要發生在04時左右,10時左右降水基本結束;2007年7月24日下午到夜間甘肅涇川不到4 h降水達148.0 mm(其中30 min雨量為83.5 mm),為涇川縣1957年有氣象觀測記錄以來的最大值。均顯示出暴雨夜間特征非常明顯。
若分別以08時和20時為日界統計暴雨過程,發現在青藏高原東北側地域內的陜西大部和甘肅東南部地區暴雨,20時明顯多于08時,年均偏多3次左右,且20時暴雨過程的雨量和范圍也比08時大。在不同區域內也存在差異,如寧夏地區08時暴雨略多于20時,且08時雨量也大于20時,主要是由于寧夏地區處在干旱與半干干地區,其水汽條件較陜西和甘肅東南部偏少,水汽輸送的持續性較差所造成。其降水多以對流性形式出現,在降水機制上類似冰雹天氣,降水多集中在午后至傍晚,且降水持續時間相對較短。以該地區2000—2008年的暴雨過程為例,9年間20時的暴雨過程僅有2001年多于08時,其余年份無論是暴雨過程和暴雨站次均少于08時或與其持平。再如2006年7月14日銀川出現暴雨08時雨量為104.8 mm,20時雨量則為83.8 mm。
5 空間分布、空間及時間尺度特征
5.1 空間分布
青藏高原東北側的暴雨總體趨勢是由東向西、自南向北逐步減少,且雨強趨于減小,暴雨地理分布大致表現為“三高兩低”的特征。“三高”即以秦嶺以南的鎮巴、紫陽、寧強為第一東西向的高發帶;關中北部的韓城、白水和西部地區的寶雞附近及甘肅東部地區正寧、慶陽[11]為第二東西向的高發帶;陜北北端的神木、府谷一線為第三高值區。另外在關中的中東部和秦嶺山脈北坡附近的戶縣、藍田等也有一個相對高值中心存在。而暴雨低發區域(兩低),一為在關中東部的大荔、高陵一帶,一為陜北長城沿線、寧夏中北部及甘肅天水、靜寧以西地區(圖2a)。

圖2 青藏高原東北側暴雨空間分布(單位:次)
5.2 空間及時間尺度
在青藏高原東北側的區域內暴雨均可出現,多數暴雨自北向南、自西向東先后出現。其中區域性暴雨多以陜南和關中連片出現暴雨、甘肅東部與關中西部或與陜北南部連片出現暴雨,影響范圍多達10~20縣(市),這類暴雨約占區域性暴雨總數的30%。寧夏與陜北及寧夏與甘肅東部也常連片出現暴雨,但暴雨的范圍較小,一般少于10縣(市)。而陜西、甘肅和寧夏同時出現大范圍的暴雨僅有兩次,分別是1977年7月5日和2002年6月8—9日的大暴雨過程,兩次過程均給陜西帶來重大損失和人員傷亡[10-11]。
不可忽視的是,青藏高原東北側偏北地區出現大暴雨的可能性不比偏南地區小,甚至超過南部。如甘肅最大暴雨日降水紀錄出現在慶陽站(1966年7月26日達190.2 mm),并未出現在甘肅隴南的徽縣或康縣。位于陜北的子長站2002年7月4—5日連續兩天降水量超過100 mm,其中7月4日達195.0 mm,遠超過關中地區許多測站的日降水最大紀錄。可見偏北地區的降水強度也非常大,但影響范圍多為1~3縣(市),具有明顯的局部特性。位于北部地區的暴雨有明顯的夜暴雨特征,強度大、降水時間集中,往往3~6 h降水量就可超過100 mm。這多是由副高第三次季節性北跳、西伸北抬和來自副熱帶高壓底部的偏東氣流與來自孟加拉灣的偏南氣流同時作用和地形影響的結果[12]。
從時間尺度來講,青藏高原東北側暴雨基本為單日暴雨,在48 a中,持續兩天的較大范圍暴雨約占總數的10%,且以陜西的陜南居多。總體而言暴雨的時間尺度大多較短,影響系統和強降水同步出現的概率較多,多以局地和局部地區突發性暴雨形式出現,且具有先西后東的次序。在暴雨的預報方面應以短期預報和短時預警預報為重點。
6 地形作用
通過將暴雨資料與青藏高原東北側的地形(圖2b)對比分析,發現暴雨空間分布與地形關系密切。夏半年由于青藏高原東北側的水汽輸送多為偏南或偏東南氣流,形成了秦嶺以南的高值區域,暴雨最大中心的鎮巴位于東西走向的米倉山脈迎風坡,其地形作用十分明顯。位于關中北部、寶雞附近及甘肅東部地區的暴雨高發區,主要是由于地形對翻越秦嶺氣流的強迫抬升[13]以及偏東南氣流的共同作用造成的[14],因為關中地區(即關中盆地)是典型的喇叭口收縮抬升型地形,又分別有黃河、洛河、涇河及渭河等河谷存在,這種大的喇叭口地形與小的河谷喇叭口疊加輻合作用有利于暴雨的產生。關中北部、甘肅東部的暴雨多發區則均為處在相應的河谷附近或河流上游地區與地形(如六盤山、子午嶺的阻擋)共同形成的輻合地區。另外夏季陜西地區受冷空氣活動影響,當較強冷空氣直接南下或華北冷空氣東路侵入陜西時,在秦嶺北坡爬坡和屏障作用下,使得秦嶺北坡的藍田、潼關也成為一個暴雨相對多發區。位于陜北的府谷、神木的暴雨高發區,同樣均是處在黃河沿岸的支流河谷地區,受喇叭口地形輻合和地形抬升影響使得陜北東部暴雨明顯多于其西部地區。
7 結論
(1)青藏高原東北側暴雨年均值為27.6次,20世紀80年代初期為青藏高原東北側暴雨的高峰期,21世紀初至2007年則為次峰期;暴雨的年頻次和站頻次變化在年代、年際變化上與陜西十分相似,與甘肅有一定的趨同性,且共同存在著約為3 a和6 a兩個周期,不同的省份還分別存在約為8 a、9 a和20 a幾個不同的周期,并通過信度檢驗。
(2)青藏高原東北側暴雨的月分布較分散,2—11月均可出現,以7月為主,8月次之,地域上存在差別,青海和寧夏地區則以8月為年內最大值,且有南部多北部少的特征。
(3)暴雨的地理分布受地形影響很明顯,多暴雨區域均在迎風坡及河川喇叭口輻合地帶。
(4)青藏高原東北側的區域性暴雨多為陜南和關中連片出現暴雨、甘肅東部與關中西部和陜北南部連片出現暴雨,寧夏與陜北和寧夏與甘肅東部也常連片出現暴雨,但暴雨范圍較小。陜西、甘肅和寧夏同時出現大范圍的暴雨概率較小。無論是區域性暴雨和大暴雨很少持續兩天以上。但甘肅東部、陜北暴雨的強度有時遠超過南部隴南和關中地區,說明有一定的地方特性。
(5)當年度內第一場較大范圍的區域性暴雨較早出現時,預示該年度暴雨偏多。當年內首場暴雨出現落區偏北或偏西時,預示著該年度暴雨的落區相對偏北或偏西,其結論對長期預報及氣候預測具有一定參考價值。
(6)青藏高原東北側暴雨空間分布具有“三高兩低”的特征。三個高值中心分別位于陜南的鎮巴、紫陽一帶,寶雞、韓城及甘肅東部的正寧一線,陜北北端的神木、府谷一帶。
[1] 白肇燁,徐國昌,夏建平,等.中國西北天氣[M].北京:氣象出版社, 1991:202-254.
[2] 任余龍,壽紹文,李耀輝.西北區東部一次大暴雨過程的濕位渦診斷與數值模擬[J].高原氣象, 2007,26(2):344-352.
[3] 王位泰,張天峰,姚玉璧,等.黃土高原夏半年降水氣候變化特征及對作物產量的影響[J].干旱地區農業研究, 2008,26(1):154-159.
[4] 郭慕萍、王志偉,秦愛民,等.54年來西北地區降水量的變化[J].干旱區研究, 2009,26(1):120-123.
[5] 丁裕國,江志紅.氣象數據時間序列信號處理[M].北京:氣象出版社, 1998:38-44.
[6] 張列銳,呂虹,侯建忠.利用歷史降水量特征做長期預報的嘗試[J].陜西氣象,1999(1):9-11.
[7] 趙漢光,張先恭.東亞季風和我國夏季雨帶的關系[J].氣象,1996,22(4):8-12.
[8] 西北暴雨編寫組.西北暴雨[M].北京:氣象出版社,1992:109-130.
[9] 張列銳,侯建忠,王川,等.陜西大暴雨時空分布特征及減災對策[J].災害學 ,1999,14(2):38-42.
[10] 陜西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陜西省志:氣象卷[M].北京: 氣象出版社, 2001:231-232.
[11] 陜西救災年鑒編委會.陜西救災年鑒2000—2002 [M].西安: 陜西科學技術出版社,2005:177-185.
[12] 賀勤,邱東平,劉正奇,等. 鄂爾多斯盆地夜暴雨多[J].氣象,1997,23(7):46-50.
[13] 杜繼穩,侯明全,梁生俊,等.陜西省短期天氣預報技術手冊[M].北京:氣象出版社, 2007:96-106.
[14] 孫健康、武麥鳳,謝在發,等.青藏高原東部一次大暴雨過程分析[J].干旱區研究, 2007,24(4):516-519.
2013-11-27
侯建忠(1960—),男,陜西澄城人,學士,正研級高工,從事天氣氣候預測及研究。
公益性行業(氣象)科研專項(GYHY201306006);陜西省氣象局重點科研項目(2013Z-1)
侯建忠,權衛民,潘留杰,等.青藏高原東北側地區暴雨特征分析[J].陜西氣象,2014(2):1-5.
1006-4354(2014)02-0001-05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