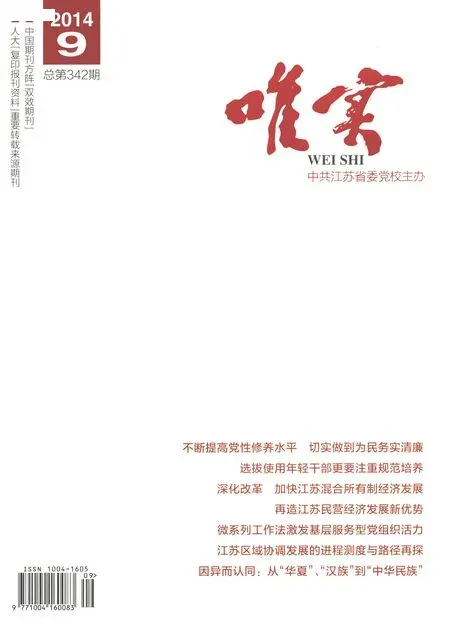因異而認同:從“華夏”、“漢族”到“中華民族”
胡阿祥
“我”是誰?“我”從哪里來?在中國悠久綿長的歷史中,這一直屬于“文化”范疇的問題,道理很簡單,中國古代并無現代意義上的生命科學。進而言之,以代代相傳的、構成生命的遺傳基因Y染色體的檢測為手段,對于類似問題所作出的全新回答,其實并不能真正“改寫”既往的、立足于“文化”認知的那些答案。
舉個我本人的例子。經過復旦大學現代人類學教育部重點實驗室的檢測,2013年4月8日,我知道了我的Y染色體為N-M231+。按照生命科學的解釋,N-M231是“較晚期到達東亞的人群”。“阿爾泰語系、芬蘭人等中高頻分布,在中國廣泛分布,漢人中通常10% 以下,部分少數民族中較高頻”,又“+號表示有突變”。然而這些“科學”答案,只是豐富了我對“我”是誰、“我”從哪里來的認識,而沒有改變我對胡姓源出舜裔胡公滿、中古時代胡姓以安定與新蔡為著望、近世以來我屬寧波柴橋胡等的“文化”認知,雖然這些“文化”認知并無“科學”數據的證明。
作為“個人”的“我”是這樣,推而廣之,作為“華夏”、“漢族”以及“中華民族”的“我們”,又何嘗不是如此呢?
一
起碼在中國歷史上,今天所謂的“民族”,終究是個因異而認同的“文化”概念,而非血統檢測的“科學”概念。在中國歷史上,那些相同點多、相異點少的人群,往往會在相同點少、相異點多的外部人群的壓力下,產生彼此的互認,進而認同;壓力越大,危機越深,這種互認與認同的范圍就越大,圈入的人群也就越多,如此,便形成了具體的民族意識以至民族事實。當然,“民族”一詞,在古漢語里并沒有構成,而用“人”、“種人”、“族類”、“部落”、“種落”等詞表示,用“民族”來表示穩定的共同體,是100余年前從日文中引進的;但是,這并不妨礙我們討論中國歷史上的“民族”問題。
在中國歷史上,地理與文化雙重意義上的主體民族的形成有兩次,一次是作為漢族前身的華夏,一次是漢族。
“華夏”的形成,離不開春秋時代外部蠻夷戎狄的壓力與內部諸夏成員的互認,所謂“四夷交侵,中國微矣”(《詩·小雅·六月》毛《序》),“南夷與北狄交,中國不絕若線”(《春秋公羊傳》僖公四年)。在這樣的情勢下,相對于四夷來說,那些周天子分封的、與周天子的利害大體一致的諸夏國家,祭起了“尊王攘夷”的大旗。“尊王”,就是尊奉周天子為主,“攘夷”,就是排斥蠻、夷、戎、狄。這樣,“華夏”就帶上了民族的意味乃至凝成了民族的名稱。“華夏”民族,就是區別于蠻夷戎狄的、文化燦爛、如同花一樣美麗的“諸夏”,所以區別于并駕乎四夷之上。及至戰國時代,華夏民族形成并壯大,平滅六國以后的秦朝,便是以華夏民族為主體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權制的國家。
再言“漢族”的形成,同樣聯系著非漢民族。先是十六國北朝時期,入主中原的所謂“五胡”匈奴、鮮卑、羯、氐、羌,以“漢”、“漢子”、“漢家”、“漢婦人”、“漢小兒”、“狗漢”、“賊漢”等貶稱,稱呼曾經的兩漢、三國、西晉之“天朝子民”,而在遭到這樣辱罵的語境下,受到歧視的被罵者就有了一種彼此認同的意識,是為漢族的形成階段;漢族意識的再次強化與漢族群體的進一步擴大,是契丹、女真、蒙古等族相繼進入中原,建立起遼、金、大元政權時期,其時,“漢人”、“漢兒”一類仍帶貶義的稱謂再次大量出現,“漢”也成為身份、地位低下的一種象征;再往后,則是滿洲民族進入中原建立大清王朝,漢人作為被統治民族,仍然處于弱勢的地位。而到了1912年中華民國建立,提倡“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為一人”,“合漢、滿、蒙、回、藏諸地為一國”(《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宣言書》),至此,“漢族”作為漢人共同體的族稱,正式出現在了史冊上。
自認先進的“華夏”,是在周邊的蠻夷戎狄的外部壓力下,出現華夏意識、成為華夏民族的,華夏具有一種優越感;而“漢族”是在非漢民族的統治之下、與其雜居狀態之中,被動地自認的,在很長的時間里,“漢”在非漢民族統治者的稱呼里,帶有貶義。
然而必須強調的是,諸如華夏、蠻、夷、戎、狄,漢、匈奴、鮮卑、羯、氐、羌、契丹、女真、蒙古、滿洲,作為民族名稱雖然區別明顯,具體的內涵卻是復雜的、模糊的;也就是說,起碼在中國歷史上,并不存在血統純粹的民族,而這聯系著民族劃分的標準問題。
在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主體民族華夏與漢族的傳統文化中,往往以“文化”而不是以“血緣”來區分民族。如在春秋戰國時期,雖然也有“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左傳·成公四年》)的說法,但逐漸發展出一種標準,即區分華夏與蠻夷戎狄的關鍵,不是血緣關系而是文化選擇。唐人韓愈《原道》:“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于中國則中國之。”章炳麟《中華民國解》(《民報》第15號,1907年7月5日):“《春秋》之義,無論同姓之魯、衛,異姓之齊、宋,非種之楚、越,中國可以退為夷狄,夷狄可以進為中國,專以禮教為標準,而無有親疏之別。”譚其驤師《近代湖南人中之蠻族血統》(《史學年報》第2卷第5期,1939年)也指出:“漢民族自古以來,只以文化之異同辨夷夏,不以血統之差別歧視他族。凡他族之與華夏雜居者,但須習我衣冠,沐我文教,即不復以異族視之,久而其人遂亦不自知其為異族矣。”也就是說,華夏(漢)如果接受了蠻夷戎狄(胡)的風俗習慣,就成了蠻夷戎狄(胡),反之亦然;華夏(漢)、蠻夷戎狄(胡)之分,不在族類,不在地域,而在文化。什么文化呢?《禮記·王制》說道:
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東方曰夷,被發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發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國、夷、蠻、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
由此,華夏(漢)與蠻夷戎狄(胡)的區別,是蠻夷戎狄(胡)“飲食衣服,不與華同”(《左傳·襄公十四年》),華夏“以詩書禮樂法度為政”,而“戎夷無此”(《史記·秦本紀》)。其實讀讀所謂“正史”的蠻夷戎狄傳、土司傳甚至外國傳,記載的主要內容也就是“飲食衣服”與“詩書禮樂法度”。而理解了這樣的“文化”標準,再去探討有關中國歷史上各別民族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等問題,也就有了清晰的梳理線索。endprint
二
比如,正是因為華夏(漢)與蠻夷戎狄(胡)之分,關鍵在于文化,而文化總是在不斷變遷、發展與進步的,加上“中國世界”相對獨立的地理特點、周邊民族向內地民族輻輳的文化趨勢等因素的影響,遂造成了漢族發展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民族的結果。柳詒征《中國文化史》(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8年版)“緒論”指出:
數千年來,其所吸收同化之異族,無慮百數。春秋戰國時所謂蠻、夷、戎、狄者無論矣,秦、漢以降,若匈奴,若鮮卑,若羌,若奚,若胡,若突厥,若沙陀,若契丹,若女真,若蒙古,若靺鞨,若高麗,若渤海,若安南,時時有同化于漢族,易其姓名,習其文教,通其婚媾者。外此如月氏、安息、天竺、回紇、唐兀、康里、阿速、欽察、雍古、弗林諸國之人,自漢、魏以至元、明,逐漸混于漢族者,復不知凡幾。
如此的民族融合,顯示了漢族同化異族的能力極其偉大,隨之,漢族的血統,在世界各民族中也最為復雜。當然,我們也承認歷史上有變夏為夷、變漢為胡者,但畢竟零散地外遷邊疆地區、并且真正融入非華夏族與非漢族者只是少數;就人數本身論,還是遷入內地農耕地區、融入漢族海洋者占了絕大多數。這樣的融入又是多方面的,諸如身份的變胡為漢,經濟生活的變游牧、狩獵為男耕女織,思想文化上的重天地君親師,政治制度方面的實行中央集權專制統治,這些,都是不以個人與民族的意志為轉移的,雖然或快或慢,或主動或被動,但卻不可逆轉的過程。
再如,若以華夏(漢)之地理語境或者文化語境中的蠻、夷、戎、狄,作為中國歷史上南、東、西、北之非華夏族、非漢族的統稱,那么,蠻、夷、戎、狄指稱的對象與地域也是變化不定的,其總的趨勢是蠻、夷、戎、狄指稱的對象越來越少,指稱的地域越來越遠。具體來說,由于漢族以及非漢民族中原王朝勢力的推展、內地農耕社會東部接海,所以逐漸地,“東夷”主要指稱海外的政權與部族,如朝鮮半島國家、日本列島國家;“北狄”一直存在著,雖然所指對象多變,但大體在長城以外,并且往往被傳統儒家視為化外之民與化外之地;“西戎”相對不太復雜,近處的“西戎”如河西走廊、四川西部及其周圍部族,在史書中尚見記載與關注,但由于“中國”疆域的偶像大禹出自西戎的傳說,所以強調得相對較少,而遠處如青藏、西域的“西戎”,與中原內地的聯系、交往、影響本來就較少較弱;至于包含了“群蠻”、“百越”、“千苗”的“南蠻”,其自身種屬的復雜與自認的不足,加上中原王朝對其認識程度的有限,使得“南蠻”的面貌尤為模糊不清,乃至往往難辨淵源,這就誠如譚其驤師《近代湖南人中之蠻族血統》立足于比較的立場所指出的事實:
北方之異族為客,多以武力入主中原,故其來蹤去跡,較為顯而易見;南方之異族為主,多為漢族政權所統治,故其混合同化之跡,隱晦難尋……史籍上關于此類事實之記載,在北為習見不鮮,在南為絕無僅有。即以私家譜牒而言,北族也往往肯自認出于夷狄,其內遷之由來,通婚之經過,歷歷可按。南方之蠻族,則當其始進于文明,自無譜牒一類之記載,迨夫知書習禮,門第既盛,方有事于譜牒,則或已數典而忘祖,或欲諱其所從出,不得已乃以遠祖托名于往代偉人,臆造其徙移經過。易世而后,其訛誤遂至于莫可追究,民族混合之跡,蕩焉無遺。又如以姓氏推定族系由來一法,在北方亦為人所常用,在南方則扦格難行。蓋北方民族之姓氏與漢姓截然有別,讀史者見拓跋、長孫、尉遲、宇文,即可知其為鮮卑;見耶律,即可知其為契丹;見完顏、石抹,即可知其為女真;此諸姓不特顯揚于北魏、遼、金當世,并能著跡于國亡百年之后,故鮮卑諸族血統之常存于中土,亦昭然若揭焉。而南方民族則不然。南方民族之語言與漢語同為單音系統,以是其姓氏亦屬單音,以單音之姓氏,譯為漢字,結果除極少數外,自與漢姓完全無異。漢族有張、王、劉、李、趙,蠻族亦有張、王、劉、李、趙,人但知其為張、王、劉、李、趙,設非語言習俗有異,烏可得而知其是否漢族耶!
而站在今天的立場上,無論這些“張、王、劉、李、趙”以及拓跋、長孫、尉遲、宇文、耶律、完顏、石抹是“漢族”還是“非漢民族”,又都不妨礙其為“中華民族”。
三
現在,“中華民族”已經是我們耳熟能詳的概念了。我們常說的“中華民族大家庭”,包括56個民族成員;“五十六個民族,五十六朵花”,成了流行的歌詞。其實,“中華民族”這個概念,仍然有著從模糊走向清晰的歷史過程。
據我在《偉哉斯名——“中國”古今稱謂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書中的考證,在中國古代,合“中國”與“華夏”二詞而成的“中華”,起源于魏晉時期,首先使用在天文上,是與太陽、太陰配合的、居中的天門名稱;然后擴而大之,地理概念上的“中華”,本指中原、內地或全國,文化概念上的“中華”,本指傳統農耕地區的文化,民族概念上的“中華”,則本指漢族。及至100余年前“民族”一詞從日文中引進后,不久就復合出了“中華民族”一詞,只是緣于古代的傳統觀念,最初“中華民族”一般仍指中國的主體民族即漢族,但是很快含義就有了拓展。1913年初,在歸綏(今呼和浩特)召開的西蒙古王公會議通電聲明:“數百年來,漢蒙久成一家”,“我蒙同系中華民族,自宜一體出力,維持民國。”可見是非漢民族代表人物共同決議,宣告中國非漢民族同屬中華民族的一部分。而與“華夏”、“漢”的形成相仿佛,“中華民族”的出現,也是此前的百余年來資本帝國主義列強侵略、壓迫甚至分化企圖的產物,正是空前的國家與民族危機,使得在同一個中央政府治理下的諸多民族,同呼吸、共命運的意識被強化了起來,終于集聚成了“中華民族”;而發展至今,正如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所說:“中華民族這個詞用來指現在中國疆域里具有民族認同的十一億人民。它所包括的五十多個民族單位是多元,中華民族是一體。”(費孝通等著《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89年版)
然而“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對照現在通行中國大陸的上引斯大林的“民族”定義,顯然又非一般人類學、民族學甚至社會學里的民族概念,畢竟,56個民族,語言有異,56朵花,花色不同。如此,我們可以認為,“中華民族”仍處在由民族意識到民族實體的形成過程中,在多數的場合,“中華民族”是民族群或者說是民族的集合體,而在少數的場合,“中華民族”則是政治概念或者政治宣傳。
我們現在習稱的“56個民族”絕大部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從要求認證的幾百個“民族”中,通過識別并經中央政府確認的民族;而事實上直到目前,有些劃歸某一民族的族體,還在提出重新識別為單一民族的要求,比如許多的四川康巴人,不認為自己屬于藏族,海南省北部50余萬講臨高話的人,要求認證為臨高族。但是由于“56個民族”的說法已成習慣(1965年確認了55個民族,1979年又確認了云南的基諾族),以及其他的諸多考慮,一時之間,這個數字恐怕難以增減。至于56個民族中的“高山族”,其實包括了臺灣地區的諸多族群,如阿美、泰雅、排灣、布農、卑南、魯凱、曹、雅美、賽夏等,他們自稱“原住民”,不叫“高山族”,而且這些族群的習俗并不相同,語言更是互不相通,如此,作為中國一部分的臺灣地區,其族屬也還屬遺留未決問題。又以“少數民族”論,僅僅因為諸多民族相對于漢族而言人口較少,就稱其為“少數民族”,我個人的感覺,這樣的稱呼多少欠妥。我個人平常的行文習慣,是“漢族”與“非漢民族”。
《中國社會科學報》2010年8月24日的“特別策劃”為“全球視野下的國家認同”,中、美、日三國的諸多學者,以中、美、俄、法、德、日的歷史與現實為關注對象,得出了大體傾向一致的觀點,那就是在當今世界的形勢下,國家認同要高于也緊迫于民族認同。如馬戎《“中華民族”是一家》提出:
以“中華民族”為核心認同建立一個全體中國人的“民族國家”,強化中華民族的“民族意識”,逐步淡化各“民族”的“民族”意識,只有這樣才能加強各“民族”之間的相互認同。
又韓震在《全球化時代的國家認同》中,表示“非常贊成蘭州軍區原司令員李乾元上將的看法”:
要用國家觀念淡化民族界限……是國家而不是族群讓公民感受尊嚴和尊重,從而提高國家的凝聚力;個人因國家而不是因族群而感到榮耀自豪,從而增強公民的向心力。
我們或許可以認為,“中華民族”也正在外部的經濟、文化甚至政治、軍事的又一輪壓力下,走在形成真正的、民族實體的途中,“中華民族”的內涵與外延,也正在逐漸等同于國家公民意義上的“中國人”。
(作者系南京大學歷史學系副主任、教授,南京六朝博物館館長,南京六朝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責任編輯:彭安玉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