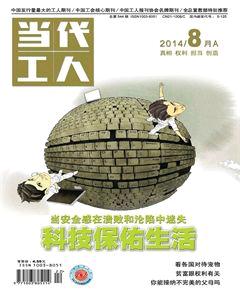貧富跟權利有關
李升初
在市場經濟體系內,一個人的財富來源除了遺贈,還來源于他對其他人提供的商品和服務。他一旦做到這點,作為交換的一方,就會獲得財富,或者說,誰越能夠讓更多陌生人滿意,誰就能獲得更多財富。這是市場經濟的通用法則。但是,這似乎難以解釋不同人之間的收入差距。
按產權學派鼻祖巴澤爾的分析,產權分為使用權、收益權和轉讓權。這是交換的先決條件之一,即先界定商品歸屬,誰有出租收益權和自由轉讓權,不然,交換就不能發生。當前大部分國家的國民都有這個權利。
但是,在不同國家間,這些個人權利的保護或界定有著巨大差異,尤其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間。究其原因,可能主要應歸于歷史,而不僅僅是國民性、或地理位置、或氣候條件、或人種等。中國是典型的城鄉二元體制,城市人不只是平均收入高于農村人,連生命價格都不一樣。拿羅斯福“人的四項基本權利”來說,城市人的自由權遠高于農村人,城市的社會保障和城市人的職業選擇自由權都遠超農村。改革開放后,中國人的一些權利都得到了極大提高,如言論自由權、遷徙權、自由選擇職業權、經商或交換權等。這些權利的提升和完善,是35年中國經濟奇跡的根源。
在人的基本權利無法保障的國家,個人財產權首先不能得到保障,連交換的可能都沒有,否則就要違法,甚至丟掉性命。同樣,在生命權得不到保障的地方,由于人人自危,自顧不暇,沒有人想著生產,這在很多種族仇殺地區能得到有力證明。當市場主體沒有辦法表達自己思想時,交易成本就會增加;在一個地方,當市場主體難以生存,或一個判斷失誤就可能餓死,就沒有人敢進入市場,只能拼命進入政府或類政府機構;當市場主體不能自由思考,創新對這個國家就是水中花、鏡中月;當市場主體時刻擔心自己的財產和生命安全時,生產就是居于太后面的事了。
基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國民的普遍富裕程度,取決于國家公民的權利豐富程度。兩者關系是既充分又必要。我們可以觀察世界上的富裕國家,他們的公民個人權利同樣“富裕”,反之亦然。
在這個基礎上,無論對未來中國長期走向,還是短期破解中國經濟社會政治困局,界定并保護公民權利都是唯一必然之路。只有越來越豐富的個人權利得到保護,才可能實現創新,才可能降低交易成本,才可能提高經濟效率,才可能不斷實現帕累托優化,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
可以說,現在的所有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似乎都面臨著兩面挨耳光的窘境,或者說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都已失效。從根子上逐漸匡正整個經濟系統、社會體系和政治系統,才是解開中國問題癥結的希望所在。如果繼續深入,那就涉及到一個宏大問題了,即:如何保護、歸還中國公民的個人權利!這些權利匯集為國家權力,牢牢掌控在一群人手里,這些權力在吳敬璉所說的權貴資本主義體系下,鑲嵌著、包裹著層層的特殊既得利益。如果說天賦人權,那中國歷史上似乎從未真正有過實踐;如果說人賦人權,那就意味著國民與特殊權力掌管者之間有必然的斗爭,當前來看,這種斗爭有望通過頂層權力機構的主動歸還或簡政放權來消弭,比如放開言論、打破戶籍制度、實現縣級自治等,都是當前可以繼續深入探索的路徑,否則,如果被動,這個國家可能面臨著又一次的大規模混亂。
總之,明晰了經濟發展與公民權利之間關系后,更重要的是能夠將其由認知轉為實踐。其實,這種實踐從來沒有停止過,中國改革開放即市場化這30多年,就是這一認知不斷實踐的過程,這一過程同時也論證了二者關系的科學性。所謂改革進入深水區,進入攻堅克難的階段,從權利角度來表述,就是人民與國家在權利、權力的不斷博弈和角力過程中,進入了均勢時期,往左,國家獲勝,意味著中國改革的倒退和集權的加劇,重演中國歷史的死循環悲劇;往右,公民獲勝,意味著中國改革的突破性進步和現代化水平的提高。從目前看,我們還是有望打破左的周期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