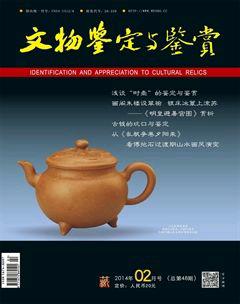風骨冷然 氣韻清逸
李艷紅



《曉江風便圖》繪于清順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是漸江晚年的一幅經典之作,也是其繪畫風格成熟穩定期的重要代表作之一。該畫現收藏于安徽博物院,為國家一級文物。該作品原由徽州大收藏家許承堯先生收藏,后來許先生的藏品大部分都捐給了安徽博物院,《曉江風便圖》才又得以重見天日。1987年,由啟功、謝稚柳、劉久庵、楊仁愷等專家組成的中國古代書畫鑒定組來安徽博物院鑒定時,認為它是漸江存世的最經典作品之一。
《曉江風便圖》為山水手卷,縱28厘米,橫243厘米,紙本,淡設色。圖寫自新安行船至揚州,由浦口練江入新安江一帶的實景,是作者漸江為友人吳伯炎赴揚州贈別而作。該手卷采用平遠法構圖,畫面橫向展開,前段寫練江沿岸霞山、將軍山諸山嵌巖峭峙,林木蕭疏,溪寒水涸,饒有冬意;中段寫兩岸高峰峻嶺,寒亭孤塔;后段寫江對岸曉霧迷蒙,煙巒重迭,順流而下的江面上,遠處兩船齊駛,近處一舟風帆正懸,依稀可見一人坐于船尾,這人可能就是出行赴揚州的伯炎居士。他坐于船尾,兀自看著新安江兩岸的寒寂之景,想起故友,心中感念萬分。
漸江作此畫意在別友,他想象著友人獨坐舟尾、乘舟側畔的情景,揮灑筆墨,一氣呵成,作此佳作。他于卷尾自題道:“辛丑十一月,伯炎居士將俶廣陵之裝,學人寫曉江風便圖以送,揆有數月之間,蹊桃初綻,瞻望旋旌。弘仁。”鈐朱文“弘仁”圓印,白文“漸江”方印。題字筆力雄健,瀟灑飄逸,漸江的行書師顏真卿,楷書學倪云林,皆得其神韻,享詩、書、畫“三絕”之譽。
漸江,俗姓江,名韜,字六奇、鷗盟,生于明萬歷三十八年(公元1610年),卒于清康熙三年(公元1664年)(漸江卒年說法不一,一說1663年),時年五十四歲。在中國繪畫史上,漸江是新安畫派的領軍人物,清康熙年間的藝術理論家張庚在《國朝畫征錄》中記載:“新安畫家多宗清閟法者,蓋漸師導先路也。”他和查士標、孫逸、汪之瑞并稱為“新安四家”或稱之為“海陽四家”,且居“四家”之首。
漸江生于安徽歙縣旺族,因早年喪父,家道中落,他勤奮攻讀,習舉子業,終成明末秀才。清軍入關后,漸江抱著一線希望,投奔當時稱帝于福建的唐王政權,繼續從事抗清復明的斗爭。唐王失敗后,漸江懷著亡國之痛入武夷山為僧,法名弘仁,字無智,號漸江,師從古航禪師,清心寡欲,潛心參禪學畫。皈依佛門數年后,他返回故鄉安徽歙縣,“歲必數游黃山”,以黃山白岳為家。黃山風景的奇偉絕俗、靈秀多姿陶冶了漸江的情操,使其深刻體味到自然之美,他善師造化并能得其情與神,終成一代巨擘。
在師法傳統方面,漸江從宋元各家入手,“凡晉、唐、宋、元真跡所歸,師必謀一見也”,對其影響最大的是元代畫家倪瓚。倪瓚性情清高孤傲,一生不仕,寄情于書畫之中,畫作多為一江兩岸式的構圖,作平遠之景,疏林坡岸,筆簡意遠,疏蕭淡泊。相似的人生境遇使得漸江對倪瓚惺惺相惜,對于倪云林的書畫,漸江朝夕揣摩,“喜仿云林,遂臻極境”“每到得意處,幾欲奪真”。漸江的作品中有很多以“仿云林筆意”“仿倪山水”等命名。在《畫偈》《偈外詩》中有多首云及倪云林,如:“老干有秋,平崗不斷。誦讀之余,我思元瓚。”“倪迂中歲具奇情,散產之余畫始成。我已無家宜困學,悠悠難免負平生。”“疏樹寒山澹遠姿,明知自不合時宜。迂翁筆墨予家寶,歲歲焚香供作師。”“漂泊終年未有廬,溪山瀟灑樹扶疏。此時若遇云林子,結個茅亭讀異書。”這些詩皆表明他對倪瓚的崇拜與敬仰。
《曉江風便圖》亦采用倪瓚的一江兩岸式構圖,一溪江水將畫面的前、中、后三段巧妙地連為一體,完整而和諧。漸江繪浦口景色,筆墨不多,淡淡幾筆勾出遠處群山,皴擦點染較少。樹木蕭疏,依稀可見。茅亭孤立,幾座房屋孤零零立于河畔,在古樹映襯下更顯孤寂。近處江邊,作者用濃墨作古木兩株,枝杈作鹿角狀,枯葉凋零,怪石橫臥樹下,造型怪異。中段勾畫兩岸山石林立,草木蕭疏,筆法疏簡、婉約,善用直線、折線勾畫山石,顯得穩固峻拔、堅挺有力。雖是層層累加的山體,但畫面干凈整潔,帶給觀者冷逸之感,又不失氣韻。石多而樹少,樹木造型各異,或立于山頭,或在巖石夾縫中,或是倒掛于巖壁中間,造型突出。黃山是由花崗石構成的,不像草木蔥蘢的江南土石山,石多樹疏的景觀是弘仁長居黃山師法造化的結果。后段繪曉江對岸煙霧迷蒙,峰巒重疊,作者用細淡而沉穩的線條勾寫,用墨清雅,不染塵埃,透露出一種空靈純凈、高潔峻雅的悠遠意境,頗有米家云山的氣韻。《畫偈》中有詩云:“云山蒼蒼,煙水茫茫。尚書克恭,先輩元章。”言下之意,漸江對高克恭、米元章非常敬仰,對其筆意也多有模仿。《曉江風便圖》后程守的跋中也有“憶漸公作米家云山”之語。
圖中江水用大片的留白來表達,不擦一筆,空明悠遠,蘊含著無限的美感,遠處的一片樹林以及依稀可見的山影更是將觀者的目光引向遠方,令人遐想無限。山腳之下有蕭疏的樹木、荒清的野屋、小亭,就著留白的江面,畫上一處樹木稍顯茂盛的沙渚、三只揚帆行駛的小舟,給這孤寂、清冷的畫面增添了一縷生氣。整幅畫面在這種簡潔枯淡的墨色氛圍中,凸顯了弘仁的荒疏冷逸之風,傳達出他清高冷峻的風骨。
從筆法上看,漸江用勁健、簡練的線條交織出山石的輪廓,然后用枯筆焦墨略加皴染,勾寫物象的輪廓線與內部枯墨皴擦的線條相互聯系、呼應、渾融,有一種由內向外擴張的視覺效果。作山石多用出自倪瓚的“折帶皴”,尖峭方折,山石勾勒的轉折角度較大,但轉折處不結不僵。筆力老辣而凝練,用筆靈活多變,有自家風格,突顯了山石的堅韌、瑩潔之質,偉岸雄峻之勢,給人以清逸、冷峭之感。在勾勒山石的外輪廓及礬頭、緩坡、平臺時,運筆注重平動與提按的結合,使得山石輪廓中那些較長的線條充滿朝氣,富有生命力。
《曉江風便圖》后有吳羲、程守、許楚、石濤題跋,對此畫給予極高的評價,這也是畫卷的重要組成部分。題跋諸人中吳羲、程守、許楚為漸江同邑好友。吳羲即漸江跋中的伯炎居士,是西溪南的吳氏大戶,家富收藏,府中多藏宋元名畫精品,尤以倪、黃最精,常邀漸江前去賞書評畫。對此,吳羲之侄吳之碌在《桂留堂文集》卷七《叔念武氏傳》記載:“余鄉多藏宋元名畫。是時高僧漸江觀畫于余叔粲如、伯炎家,每至欣賞處,常屈膝日:是不可褻玩。”
程守字非二,號蝕庵,杭郡諸生。他在跋《曉江風便圖》中道:“余方外交漸公卅年所,頗不獲其墨妙。往見吳子不炎卷幀,輒為不平。因思余城居,且窮年鹿鹿。漸公留不炎家特久,有山水之資,兼伊蒲之供,宜其每況益上也……”漸江好友程守多次欲求漸江的畫而不得,卻常見吳伯炎獲漸江畫,頗有妒意。但考慮到漸江留在吳伯炎家較久,吳氏又多藏古畫珍品,可供漸公摩觀,其畫技才得以“每況益上”,心下釋然。吳氏為漸江的生活及藝術創作提供便捷,漸江一生贈予吳氏畫作最多,《曉江風便圖》便是其中之一。
許楚字芳城,號旅亭,又號青巖居士,歙縣潭渡后許人,是漸江的鄉賢好友。漸公去世后,他曾作詩文留念。現在漸江墓的碑額依然保留當年許楚所題“漸江和尚墓”的篆書。他在題《曉江風便圖》卷跋云:“觀漸公畫如讀唐人薜業、孫逖詩,須識其體氣高邃,遙集古人;至仍以詩流結習求之,則終屬門外漢。是卷為不炎買帆江上而作,其吮墨閑曠,水窮云起,自卷自舒,有濯足萬里之致。吾鄉百余年來,畫苑一燈,恒不乏人。至若為此道放大光明,無識想相,則漸公卓有殊勛;往者諸君,不得嵩美于前矣。癸卯之秋,靜慧院曉起,坐松棚下,試邵青丘墨,援筆漫書。”他評價漸江“體氣高邃,遙集古人”“卓有殊勛”,說《曉江風便圖》“吮墨閑曠,水窮云起,自卷自舒,有濯足萬里之致”,這些都是出自學者內心的高度評價。
石濤沒有見過漸江,但對其為人及作品敬仰至極,在漸江去世三十多年后見到這么精妙的作品時題道:“筆墨高秀,自云林之后罕傳,漸公得之一變。后諸公實學云林,而實是漸公一脈。公游黃山最久,故得黃山之真性情也,即一木一石,皆黃山本色,豐骨冷然生活。吳不炎家藏古名畫甚夥,公與不炎交好,日夕焚香展玩,不獨捧跪而已。珍重如此。寫《曉江風便圖》贈不炎,而邈遠之意甚奇。今丙子春過邗上,晤葛人先生,出此卷命予書名。先生超古鑒賞之士,又不下不炎矣。予欣得是觀焉。”石濤在一位叫葛人的徽商處見到此畫并為之題跋,師傳統上,他認為漸江師法倪云林,并“得之一變”,在云林基礎上有所創新,達到“筆墨高秀,自云林之后罕傳”的境地。師造化上,漸江“得黃山之真性情也,即一木一石,皆黃山本色”,石濤對漸江藝術的高度評價顯然不同于一般人的淡淡概括。
誠如清代大書畫家楊翰在《歸石軒畫談》一書中所言:“欲辨漸江畫,須于極瘦削處見腴潤,極細弱處見蒼勁,雖淡無可淡,而饒有余韻,乃真本耳。”《曉江風便圖》便是體現漸江繪畫風格的真本,整幅畫面筆力勁健,技法多變,遒勁有力的線條勾畫出一塵不染的新安江荒寒實景,營造出一種冷寂幽遠而又靜謐和諧的氛圍。所謂“畫如其人,人如其畫”,畫作承載著作者的人格和氣節,從《曉江風便圖》亦可讀出漸江冷寂孤傲的心性,淡泊明志、不流俗媚世的崇高格調。
《曉江風便圖》是漸江畫風成熟穩定時期的經典之作,也是新安畫派的一幅代表性作品。它承載的歷史信息極為豐富,從中可知作者漸江的繪畫風格,該作品的創作緣由、流傳經歷,其中還有漸江師法云林的記載,徽商對新安畫家的資助等內容,是研究漸江生平及其藝術生涯的重要資料,對于研究新安畫派的流變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和價值。這件國寶幾經流轉,幸得黃賓虹、許承堯等大家的細心呵護才得以珍藏流傳,十分不易,正如石濤所言,我們后人當“珍重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