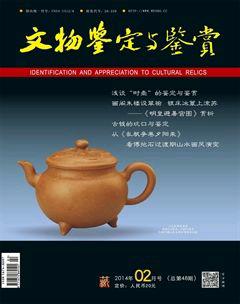從《亂帆爭卷夕陽來》看傅抱石過渡期山水畫風演變
萬新華



1935年6月,傅抱石留學東瀛歸來,任教于中央大學教育學院藝術科,講授中國美術史。受日本學術的啟發,傅抱石在教學之余開始了其持續數年的石濤研究之路,開啟了現代中國石濤研究之先聲。幾年來,傅抱石筆耕不斷,不斷考證和論敘,鍥而不舍地尋根探源,對石濤生平和藝術進行了深入的探究。隨著《石濤年譜稿》《石濤上人生卒考》《石濤叢考》《石濤再考》《石濤三考》《石濤畫論之研究》《大滌子題畫詩跋校補》的相繼脫稿或發表,傅抱石逐漸為人們提供了一個較為完整的、立體的石濤形象。1941年,傅抱石綜合研究成果,仔細耙梳石濤的生卒、言行、畫業、活動等,編訂完成自己石濤研究的大總結《石濤上人年譜》,比較清晰地勾勒出石濤一生的簡單輪廓,極具篳路藍縷之功。必須強調的是,傅抱石是中國美術史研究史上第一個考訂并逐年排列石濤的生活履歷和藝術創作道路的研究者,在石濤研究史上無疑是功不可沒的。
在石濤研究的過程中,傅抱石醞釀表現石濤一生的“史畫”,陸續畫出了諸多石濤題材的作品,如《訪石圖》(1941年4月)、《過石濤上人故居》(1941年9月)、《送苦瓜和尚南返》(1942年2月,見圖1)、《大滌草堂圖》(1942年3月)、《石濤上人像》(1942年6月)等,無一不是他多年研究石濤之心得。正如他在《壬午畫展自序》所云:“至關于明清之際的題材,在這次展品中,以屬于石濤上人的居多。這自是我多年來不離研究石濤的影響,石濤有許多詩往來我的腦際,有許多行事、遭遇使我不能忘記。當我擎毫伸紙的時候,往往不經意又觸著了他。三月間,本企圖把石濤的一生,自出湘源,登匡廬,流連長干、敬亭、天都,卜居揚州,北游燕京……以至于死后高西塘的掃墓,寫成一部史畫,來紀念這傷心磊落的藝人。為了種種,這企圖并未實現,但陸續地仍寫了不少。如《訪石圖》《石公種松圖》《過石濤上人故居》《張鶴野詩意圖》《四百峰中箬笠翁》《大滌草堂圖》《對牛彈琴圖》《石濤上人像》《望匡廬》《送苦瓜和尚南返》……十余幅。其中大部分是根據我研究的成果而畫面化的,并盡可能在題語中記出它的因緣和時代。”
就在撰述《石濤上人年譜》期間,傅抱石在金剛坡下的山齋中還常以石濤詩句入畫繪制畫作。約在1941年春,他經過精心的構思,探索性地創作了《亂帆爭卷夕陽來》(見圖2),題曰:“隔岸桃花迷野寺,亂帆爭卷夕陽來。抱石寫。”鈐印:“印癡”(朱文長方印)、“新諭傅氏”(白文方印)、“抱石齋”(朱文方印)、“亂頭粗服”(白文方印)。圖中畫江水呈三折,自遠處流來,又向畫外流去,江水滔滔,白帆點點。對岸山谷間桃花盛開,一古塔兀立,寺廟隱約于山坳云氣里;淡赭薄施,山水沐浴在落日夕照中,生動地完成了石濤題畫詩的圖解。
自1937年以來,傅抱石孜孜不倦地收集整理石濤散佚題畫詩跋,精心考訂,去偽存真,輯錄完成700余首規模的《大滌子題畫詩跋校補》,探求出石濤的藝術思想和藝術蹤跡。所以,傅抱石通曉石濤詩文,對石濤內心世界也有獨到的領悟,可謂心心相通。因此,此時的傅抱石順其自然地選擇石濤詩意進行創作,詮釋石濤詩的精神內涵。1941年1月26日,也就是庚辰除夕,傅抱石精心鐫刻壽山石朱文印“苦瓜詩意”,專門鈐蓋石濤詩意畫。
當然,傅抱石是在編撰《大滌子題畫詩跋校補》時通過程霖生輯錄的《石濤題畫錄》知曉石濤之“隔岸桃花迷野寺,亂帆爭卷夕陽來”的,后來詳細考訂于《石濤上人年譜》中:“(康熙十八年,己未,即1679年)夏,過永壽方丈為語山和尚作《枯墨赭色山水》,題云:‘隔岸桃花迷野寺,亂帆爭卷夕陽來。”多年之后,石濤的這件《枯墨赭色山水》現身于拍賣市場。就圖式而言,傅抱石的《亂帆爭卷夕陽來》與石濤山水小品頗為相似,然在圖像上作了刪減,更為簡潔概括。
所謂“詩意畫”,是以詩文為題材表達詩文內涵的繪畫,除了敘說文學作品的內容,并闡發其義涵與意趣,以達畫中物象與詩文情致交融之境。通常,“詩意畫”的表現方式依畫家選擇和詮解詩文的情況有所不同,或圖繪詩文全部的內容,具象其要旨;或摘取詩文短句,以詩眼統攝全文;或緣情而發,依于詩文而又別開新意,以整體之情境氛圍烘托詩文內涵,雖是以表達詩文內涵為目的,但是畫家的巧心營造,往往可能更添意趣,為詩文所不及,而具畫龍點睛之妙。所以,詩意畫是文學以筆墨鋪陳圖像的無聲演出,是畫家解讀詩意之后再現詩意的成果,其題詩則是對圖像文本的情思抒發。
1942年10月,傅抱石在畫展自序中表達了對詩畫關系的獨特見解:“我認為一幅畫應該像一首詩,一闕歌,或一篇美的散文。因此,寫一幅畫就應該像作一首詩、唱一闕歌,或做一篇散文。”故在題材選擇上,傅抱石有意識地選擇表現前人詩意,希企通過向山水畫中注入某種情節、某種情感的方式,給程式化的傳統山水畫注入新的活力。由于數年的石濤研究經歷,傅抱石浸淫于石濤的詩文世界,沉醉于石濤的精神情境,也深深折服于石濤其人其藝:“這自是我多年來不離研究石濤的影響,石濤有許多詩往來我的腦際,有許多行事、遭遇使我不能忘記。當我擎亳伸紙的時候,往往不經意又觸著了他。”在1940年前后的幾年間,傅抱石撰文著書之余,首當其沖地選擇石濤詩意畫的創作,如《露頂奇峰平到底》(1941年)、《深山有怪松》(1942年)、《滿身蒼翠驚高風》(1943年)、《蕭然放艇學漁人》(1943年)等。通過石濤史畫和石濤詩意畫的創作,傅抱石心摩手追,完成了與石濤心靈上的時空對話。
眾所周知,石濤古體詩功力甚高,往往不假詞藻,直抒胸臆,風格或委婉動人,或豪邁激昂,皆耐人尋味。即如“隔岸桃花迷野寺,亂帆爭卷夕陽來”,生動地再現出大河兩岸桃花迷離成片,姹紫嫣紅,如云霞彩虹,水上帆船競相飛駛的風景。石濤如此貼切地表達了一派靈光秀色之景,文辭十分逼真親切。
在《亂帆爭卷夕陽來》中,傅抱石以“桃花、松樹、寺廟、飛帆”為主要元素,充分發揮水墨逸趣,圖解石濤詩之意境。全圖由近景、中景和遠景三部分構成,呈s型,由近及遠地描摹崇山峻嶺和急流險灘,其右下角著力刻畫突兀山峰、道勁的松枝;中間是莽莽蒼蒼的逶迤群山、湍急的江流和片片征帆,兩岸叢林茂密,桃花點點,廟宇數椽,寺塔聳立,形象地再現出“隔岸桃花迷野寺”之景;最遠處,山巒與浩蕩的江水在朦朧的天際處交接又漸漸隱去,構圖穩重,意境深遠。在墨色交融的光影里,群山與江流巧妙地構成山水的虛與實、明與暗、動與靜的對比,雄渾多姿。而江流中的片片征帆,則是圖畫刻畫的重點,成群結隊,自遠而來,似有“萬舸爭流”之意,描繪相當精工細微,不僅突出了江流與群山的脈絡而倍增生機,也與山石形成一種對比的趣味,正如他在《壬午畫展自序》所說:“我對于畫面造形的美,是頗喜歡那在亂頭粗服之中,并不缺少謹嚴精細的。亂頭粗服,不能成自恬靜的氛圍,而謹嚴精細,則非放縱的筆墨所可達成,二者相和,適得其中。我畫山水,是充分利用兩種不同的筆墨的對比極力使畫面‘動起來的,云峰樹石,若想縱恣蒼莽,那么人物屋宇,就必定精細整飭。根據中國畫的傳統論,我是往往喜歡山水、云物用元以下的技法,而人物、宮觀、道具,則在南宋以上。”無疑,這是傅抱石的精心營構所致。總體而言,《隔岸桃花迷野寺》藉由山勢的錯落放置、山間的煙嵐效果,用墨的濃淡輕重,以突顯景象遠近的關系,以使全圖更為合乎自然界的實質空間。
當然,傅抱石的《隔岸桃花迷野寺》毫無例外地從石濤作品中獲得靈感,并汲取梅清縹緲法、龔賢積墨法的長處,偏重于“拖泥帶水皴”,并結合其他皴法交替互用,肆意揮灑,營造出水墨氤氳、墨彩交融的風格。同時,他還適當運用日本留學期間接觸到的橫山大觀、竹內棲鳳等人的日本畫法,以大塊體積分配畫面,配合色彩的濃淡變化,表示山體的層次,并造足空氣感。主山的描寫又因為筆觸與形態組織之單純粗疏,因而難以識別其彼此的空間遠近和層次關系,這種渾融感與壓縮的空間表現,便是傅抱石入蜀后繪畫變革的主要特征之一。
尤其是,江水波濤干皴輕染之法,為傅抱石獨創,富有表現力。江水不用層層排列的曲弧線條勾勒,而是以散鋒淡墨輕擦橫掃,再用藍色渲染,遠處及中間留出空白,于是白波翻滾,無邊無際的空闊水面頓時畢現。而千帆競發,鼓風而下,輕快迅疾,極有速度感。為了突出江面及帆船,近景的幾棵巨松畫法粗放,只求整體效果,拋棄了細部,剪影明確,表現逆光下的情狀;松下有許多墨點,其間夾雜著點點紅葉,表現出“隔岸桃花迷野寺”的意境。畫法也是線勾,而用濃墨淡染,使墨彩交融,自然地畫出明暗和立體感,明顯迥異于傳統的畫法,實乃創新。這種筆墨技法,與其幾乎同時的《觀海圖》(見圖3)十分相似。
作為目前所見傅抱石入蜀后的早期作品之一,《隔岸桃花迷野寺》使我們真實地認識到傅抱石畫風轉化之軌跡,即其具有一種放棄局部與個別事物之精描細寫而成全整體畫面渾融一體之傾向,可視為傅抱石過渡期畫風遞變過程中一個重要的實物資料。就技法而言,《隔岸桃花迷野寺》全是傅抱石20世紀40年代過渡期的繪畫特色,迥異于早期山水的傳統手法,又有別于成熟期山水的習慣形式。傅抱石早期以師古為主,山巖著重于中鋒出之,枯渴干筆勾勒、皴擦,再敷以淡墨輕染,筆墨嚴整細致,構圖營造則以層層山峰堆疊而成,勾染之間、點線面之間涇渭分明,缺乏后來風格中大塊畫面的磅礴氣勢和鮮明的空間層次感。而《隔岸桃花迷野寺》以淡墨、淡彩輕染遠山,以大筆涂抹近山和坡石,并作精心的點染和皴擦,那種以輕微渲染來沖淡山體輪廓線的試驗性表現方法得到了強化,山石輪廓的線與山石的面幾乎一氣呵成,以線破線,塊面經營,并消融山體的輪廓線,真實表現出巖石的質地肌理,已不再是傳統山水畫中所習見的筆墨樣式。當時,“抱石皴”法尚未完全形成,山石塊面含糊,樹法粗放,只覺得水墨與皴法融為一體,皴擦點染同時并用,墨瀋淋漓,亂頭粗服,混沌一片,整體效果很好,可視為“抱石皴”的前奏。所以,《隔岸桃花迷野寺》無需爭辯地成為傅抱石變革時期新舊技法結合的代表性作品,對于研究傅抱石山水畫風格演變具有不可或缺的參考意義。
稍后,傅抱石將同樣的筆墨風格持續于《擬梅瞿山筆意圖》(見圖4)、《松陰清話圖》(1941年9月)等的創作之中。這一系列作品不再完全保持傅抱石早年山水畫粗放野逸的筆致,“而以日后個人風格的筆法特征的半圓,或者描繪弧形似的輕細線條及濕潤的墨法為主”,筆墨雖嚴謹整飭,然又不失豪放率意,無不具有鮮明的過渡期特征。
后來,傅抱石一直展開著《亂帆爭卷夕陽來》章法、筆墨的經營,并不斷錘煉。在較短的時間里,他曾先后創作了多幅,其一,《亂帆爭卷夕陽來》(約1941年,見圖5),題識:隔岸桃花迷野寺,亂帆爭卷夕陽來。苦瓜句,抱石寫。鈐印:朱文長方印“印癡”、白文方印“抱石”、朱文方印“苦瓜詩意”。該圖與前述的《亂帆爭卷夕陽來》十分相似,但適當增加了兩岸坡石,更為沉厚。其二,《亂帆爭卷夕陽來》(1943年1月),題識:隔岸桃花迷野寺,亂帆爭卷夕陽來。壬午小寒前三日,傅抱石寫于重慶西郊金剛坡坡麓山齋。鈐印:白文方印“抱石長年”、朱文方印“抱石齋”、朱文方印“苦瓜詩意”。1944年又補題:曼雍夫人雅教。甲申二月傅抱石。其三,《亂帆爭卷夕陽來》(約1943年,見圖6),題識:隔岸桃花迷野寺,亂帆爭卷夕陽來。新喻傅抱石蜀中寫苦瓜詩境。鈐印:朱文長方印“印癡”、白文方印“抱石大利”、朱文橢圓印“新諭”、朱文方印“苦瓜詩意”、朱文方印“蹤跡大化”。與前述相比,1943年所作之圖增加了江面部分,突顯“亂帆爭卷夕陽來”之意境,大筆縱橫馳騁,描繪出干帆競發,江流天外的奇景,真所謂筆挾風雷,磅礴大氣,完全呈現出其成熟期山水的典型特征。
在后來的幾年間,傅抱石就地取材,駕輕就熟地演繹這種技法,慣用長鋒山馬筆,筆頭、筆鋒、筆根并用,結合山形、山脈的分坡走向,皴擦、勾斫、渲染并施,大膽落墨,細心收拾,使水、墨、彩在快速的用筆駕馭下有機地融為一體,酣暢淋漓,代表者如《夏山圖》(1943年)、《萬竿煙雨》(1944年)、《瀟瀟暮雨》(1945年)等,幾達爐火純青之境。簡言之,大片的墨彩,飛動的線條,氣象萬千,孕育著無限生機。
1944年夏天,傅抱石又作《亂帆爭卷夕陽來》(1944年8月,見圖7),完成了此一題材的另一種圖式,頗類似于稍早前完成的《呂潛(江望)詩意圖》。題識:隔岸桃花迷野寺,亂帆爭卷夕陽來。甲申六月下浣,新喻傅抱石寫。鈐印:朱文方印“傅”、朱文長方印“往往醉后”。此幅作品點畫之間洋溢著不可拘束的才情和大氣,峽江的磅礴氣勢兀立眼前。在這幅作品中,傅抱石融合“早隨煙月上瞿塘”之章法,刻畫了“亂帆爭卷夕陽來”的意境。畫面采取近實遠虛的表現手法,右側山勢環繞,而左側又加以中景,使層次錯落有致;近景用濃墨參以青綠表現山石的險峻,由近及遠則墨色漸變,山勢遁險,山腰云霧繚繞,用筆豪放,虛實相映,既率意又精細,既有激情又不失法度,洋溢著濃烈的詩情。
因此,筆者重點介紹的《亂帆爭卷夕陽來》與《觀海圖》《擬梅瞿山筆意圖》《松陰清話圖》等作品乃是其山水畫風格成熟的前奏。而這一系列的《亂帆爭卷夕陽來》則正好構成了傅抱石山水畫變革初期的完整序列,共同見證了傅抱石山水畫創新的發展軌跡。于此,我們可以尋繹出畫家一條清晰的演進脈絡。理所當然,我們能從《亂帆爭卷夕陽來》中得以窺見傅抱石風格變化的真實痕跡。
至今,人們還在驚嘆于金剛坡時期的傅抱石何以在極短的時間迅速完成了風格的定型,盡管研究者們做出了多種解釋,似乎仍無法得出令人滿意的答案。但是,人們普遍相信,對傳統的潛心研究和對巴山渝水的感悟,導致了傅抱石繪畫創作的成熟。蜀地大山往往遍布松林和竹林,一片空瀠潤融風光,間或露出一些深褐色的巖石,山風一吹,松濤的嘩嘩聲伴著近處竹林的颯颯聲,無論陰晴明滅,還是晨昏夕映,萬般動人。如遇下雨,那滿山溝壑則是泉瀑的世界,風聲、雨聲、水聲,如同交響樂一般;如遇云霧,山色朦朧,忽隱忽現,松林竹叢掩映于云霧之中,恍然仙境一般。一旦晴空皓月,山樹,小徑、房屋籠罩于夜色,黑影憧憧,一輪明月灑下淡淡銀輝,一派寧靜的山野景象,足以引來無限遐想。對此,傅抱石曾感慨萬千:“著眼于山水畫的發展史,四川是最可憶念的一個地方。我沒有入川以前,只有懸諸想象,現在我想說:‘畫山水的在四川若沒有感動,實在辜負了四川的山水。……以金剛坡為中心周圍數十里我常跑的地方,確是好景說不盡。一草一木、一丘一壑,隨處都是畫人的粉本。煙籠霧鎖,蒼茫雄奇,這境界是沉湎于東南的人胸中所沒有所不敢有的。”面對草木蔥蘢的蜀地風光,傅抱石將山水畫改革的方向從傳統的“線”轉至“面”的形式突破,所謂“散鋒筆法”便在“外師造化”與“中得心源”的心手相印中應運而生了。晚年,傅抱石自己承認其皴法是來自于四川風景地貌的啟發:
我作畫所用皴法是多年在四川山岳寫生過程中逐漸形成的。我著重表現山岳的變化多姿,林木繁茂又可見山骨嶙峋的地質特征。當然皴法還應與“點”、“染”結合起來,才能取得畫面完美的效果。皴法的用筆要自然,順筆成章,切忌堆砌做作,死板地勾斫。用墨要注意墨色的韻律、變化,要虛實相生而成天趣。皴法的處理必須注意山石的自然情趣和筆墨效果。
考察《亂帆爭卷夕陽來》,所謂“林木繁茂”“山骨嶙峋”“點染結合”“虛實相生”等諸要素,傅抱石在畫面中都一一充分體現。總而言之,作為同一題材最早的作品,《亂帆爭卷夕陽來》真實地印證了傅抱石過渡期的演變風格和創新歷程,成為傅抱石繪畫研究最為重要的早期作品之一,其價值自不待言。
《亂帆爭卷夕陽來》在完成后的一兩年間,遂為身在重慶的福建建寧名醫李世芳(1890-1968年)所得,徐悲鴻(1895-1953年)應邀題跋:“此幅沉雄奔放,余深好之,苦不得兼,遂為世芳先生所致,喜同嗜趣,敢志姓名,悲鴻。”顯然,徐悲鴻對此贊賞有加,惺惺相惜之心躍然紙上。審視《亂帆爭卷夕陽來》,其飽滿的畫面、沉郁的色彩里充溢著非凡的張力和奔放的激情,難怪徐悲鴻會發出“此幅沉雄奔放,余深好之,苦不得兼”的感嘆。
事實上,徐悲鴻自1942年6月南洋歸國后,看到了傅抱石的一系列新作,十分欣賞。當年秋天,他為《大滌草堂圖》欣然題寫詩塘:“元氣淋漓,真宰上訴。八大山人《大滌草堂圖》未見于世,吾知其必難有加乎此也。悲鴻歡喜贊嘆題,壬午之秋。”或許,徐悲鴻題跋《亂帆爭卷夕陽來》抑或也在此前后。傅抱石與徐悲鴻交情莫逆,自1930年7月結交以來,屢得到徐悲鴻提攜之助。1935年5月,傅抱石在日本東京舉辦“傅抱石氏書畫篆刻個展”,徐悲鴻郵寄題辭以表祝賀:“追尋真藝。抱石先生于繪事精進不已,諸名公展覽其作于東京,書此志懷。乙亥春盡,悲鴻。”(見圖8)1942年10月10日,傅抱石在重慶夫子池勵志社舉辦“傅抱石畫展”,徐悲鴻撰寫《傅抱石先生畫展》,發表于次日的《中央日報》,有云:“抱石先生,潛心于藝,尤通于金石之學,于繪事在輕重之際(古人氣韻之氣)有微解,故能豪放不羈。石濤既啟示畫家之獨創精神,抱石更能以近代畫上應用大塊體積,分配畫面。于是三百年來謹小慎微之山水,突現其侏儒之態,而不敢再僭位于廟堂。此誠金圣嘆所舉‘不亦快哉之一也。”這里,徐悲鴻充分肯定了傅抱石以大塊體積造型、風格豪放的山水畫新作,以此反觀《亂帆爭卷夕陽來》,亦真是貼切無比。由此,《亂帆爭卷夕陽來》見證了傅、徐兩人非同一般的情誼。更為難得的是,作為僅見的“傅畫徐題”作品之一,《亂帆爭卷夕陽來》成就了中國書畫鑒藏史上的一段佳話,彌足珍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