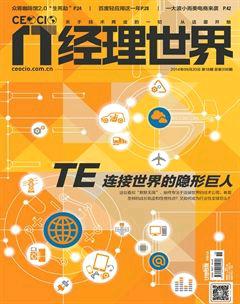工程師精神:“克服魔戒誘惑”
郝智偉



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獨特的誘惑。如今的時代,物質極大豐富,互聯網加速一切,太多傳統工程類企業也禁不住誘惑,戴上時代的“魔戒”,追求快投資、快收益、快變現,一心想站在時代的潮頭,卻摒棄了最根本的“工程師精神”,最后卻被時代所遺忘。
而TE卻是其中的少數派。它抵制住當下的誘惑,立足長遠,秉承工程師精神,持續專注地在連接器領域加速創新。如此,不僅令其產品覆蓋汽車、消費類電子、通信、航空航天、工控自動化,醫療等各行各業,更保持公司強勁的創造力,滿足客戶快速變化的需求。
“所以,從本質上來說,我們是一家工程公司。”TE全球執行副總裁兼首席技術官 Rob Shaddock這樣解讀道。這種“本質”構建了企業的基因,它決定了企業的基本形態和發展的種種特征,并在業務、部門、人員的擴張中不斷復制,使得企業整體不失自己的調性。
尤其對于TE的15個事業部,由于系統的復雜性,只有讓眾多變數圍繞“工程師精神”的核心運作,讓它們形成合力,才能保證企業順利跳過各種橫、逆、困、頓的商業陷阱。
的確,如今的時代,噪音已經多于灼見,概念被肆意包裝,無數的主義,讓企業沒了主意,此時,TE這傳統企業“守拙”的成功,恰是老牌巨頭有力的反擊——其實,企業代代傳承的核心精神,才是其創新、管理、協作真正的原動力。
創新之法
按照管理大師彼得·德魯克的說法,創新是企業的基本功能。一旦企業失去創新的能力,不能適應市場的變化,很快就會站到失敗的邊緣。
“因此,TE鼓勵、期望和重視創新精神,對變革持開放態度,鼓勵更新的工作方式。”TE人力資源副總裁張超如此說道,畢竟,連接器產業的技術革新極快,這就要求工程師們不斷吸收新知識,而TE則要刺激他們,給予他們挑戰的喜悅和研發的成就感,以工程師精神驅動創新。
家電事業部的宋博士便是因此加入TE。2010年TE籌劃在上海建立前沿工程開發團隊,她受其吸引,加入TE,負責籌建團隊,利用領先技術實現“創新領先和智能的連接”。
按照宋博士的解釋,當時,TE已經預測到家電智能化的方向,因為物聯網的興起,很可能顛覆家電領域。畢竟相關連接器已有數十年沒有發生大變化,家電有望成為智能家居的重要組成部分——比如,通過手機提前打開熱水器、空調,讓人們一回到家就可享用一切——這就需要為家電連接外部互聯網賦能。
而這一切對于已經拿到20多項專利的宋博士而言,充滿了新鮮的挑戰。于是,她開始招兵買馬,搭建團隊,尋求前沿創新的方向。4年下來,她已將團隊擴張至11人,在多個全球和本地項目上取得了矚目的成就。
除此之外,TE還設立了諸多刺激創新的機制。例如,模仿國際學術大會形式,每年都會舉辦一次TEchcon大會,該年度大會由全球經選拔的TE工程師參加,旨在推進“互聯的創新”。主辦者會前確定數個主題,工程師們按照相應主題自由投稿,由TE的高工們默評審稿,最終以極高的淘汰率確定參會者,與會的工程師不僅可以與世界級大拿頭腦風暴,更可以路演自己的項目,尋求創新資源的整合與支持——宋博士團隊就因此得到啟發,在一項設計中與韓國汽車部門相互借鑒研發思路。
同時,負責TE技術路線圖的各事業部CTO們還會不定期發起“創新大戰”。好比最近舉辦的“樹莓PI大戰”,就是針對智能穿戴設備領域的創新——有人設計遙感家中游泳池的溫度,有人開發智能音響播放、視頻監控……如此,推行開源文化,讓軟硬件工程師們共同頭腦風暴,相互借鑒,以資金支持他們,讓他們從專業能力出發,既見木也見林,向最前沿的趨勢看齊。
更吸引TE工程師的是,若創新項目有商業化前景,發起人還可以將項目遞交給TE網絡社區里的“發明游戲”孵化器。在這里,其他TE工程師扮演投資人,不斷“挑戰”和“協助優化”商業計劃,利用虛擬幣進行A、B、C輪投資。最終孵化成功的項目,將拿到TE真金白銀的內部投資——去年,一個“用谷歌眼鏡輔助連接器布線”的項目就順利拿到了這筆投資,進入實質的開發優化階段。
如此種種,使TE在創新的道路上亦步亦趨,日拱一卒,聚能成勢。即便面對“技術越進步,產品生命周期越短”(From《創新者的窘境》)的大勢,TE依然有充分的創新儲備,在市場中游刃有余。
管理之道
當然,要保證如此強度的創新動力,更少不了在管理上的道行。
在張超看來,最首要的,就是讓掌握企業“核心競爭力”的工程師們找到自己職業發展的歸屬感。
眾所周知,在國內,許多工程師缺乏上升的職業通道,在獲取一定資歷以后,沒有更好的晉升途徑,很多人不得不轉向管理崗位,以致精深于產品和技術的高級工程師極其匱乏,為此,很多技術型企業甚至不得不將研發中心設在境外。
而在TE,工程師們享受“職業發展階梯”計劃,只要自己喜歡,就可以一直在專業的道路上不斷升遷,從入門工程師到總工程師,都有明確的評定標準,以及不亞于管理體系的級別、待遇。就像宋博士,最近被任命為TE新產品開發副總工程師,成為TE工程師團隊的頂尖成員。
“要知道,在TE,工程師的人力資源管理可不僅是HR部門在做。”沈偉明這樣告訴記者,各級管理層都要親自研究每位工程師的能力,在工作上為其提供充分的條件,讓他們看見發展,讓他們有歸屬感。
當年,中國的汽車事業部建立不久,只有20名工程師,后來不斷有人加入,TE不僅投入大量資源,為他們提供培訓機會,還通過“百團大戰”,將工程師們編成一個個小團隊,解決公司快速擴張中的實際問題。由此,令其產出和個人能力得以迅速提高,突出者自然獲得快速提拔。同時,TE的“Go China”項目,也會把國外優秀的專家請到中國,手把手地帶動這群“好苗子”,一起做項目,幫助他們成長。
按照沈偉明的說法,他在TE的20年,幾乎了解屬下所有關鍵員工,大家只有多溝通,才能沒有隔閡。一方面,管理者要融入工程師人群,與他們打成一片,哪怕是打籃球被教練罵,他也頂在前面;另一方面,將績效考核做到細致入微,每個項目考核要達到什么目標,怎樣的百分比,都要在公告板上公示,讓制度絕對透明。這樣,管理者與工程師才能無礙溝通,更有利于調配資源,充分發揮每個人的聰明才智。
如今,汽車事業部已有300多位工程師,與5年前相比增長了一倍,但人員流失率遠低于同地域的平均水平。
“同樣重要的是,找到氣味相投且又有不同特長的人。”宋博士這樣說道。就像她的團隊,有時候面試數十個應聘者,才能招入一人。
因為她認為,團隊要用新發現改變人們生活,所以她要帶一群人,這群人從“看別人玩,到幫別人玩,再到與別人一起玩”,必須一直有開放的心態,不能拘泥于自己的一畝三分地,更要有全局觀,更懂得從別人的角度看待問題。
在此前提下,“對事不對人”地頭腦風暴,獲得思想的火花,才不會將技術上的“爭論”變成“爭吵”,影響到團隊的和諧。進而,工程師團隊可以高效地開發、實驗,快速驗證,在全面鋪開到產品投放階段前,結合技術、市場成熟度,證明創新項目的可行性,保障“200小時為限”的“開放式發明”有最高的效率、最少的浪費。
可見,通過對工程師生態的洞察,TE形成了相應的包容式管理,為其構筑出又深又寬的“護城河”,使得競爭對手難以逾越。
協作之術
其實,根本而言,作為TE的核心資源,工程師團隊更像一個企業型社群,有共同的目標、綱領,高度協同,一致行動。要知道,這種高效率的自組織協作,才是管理延伸的最佳形態。
例如,TE工程師常常活躍于他們專有的網絡社區,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標簽——做過哪些項目,擅長哪些領域,獲得哪些獎項等等——如此,遇到困難的工程師都能及時在社區內廣發“英雄帖”求救,尋求全球同僚的幫助。無論國內外,同僚們也都會不吝賜教,因為TE有獨特的激勵機制。
要知道,TE信奉:“出色的工程師,都是自己冒出來的,是在各種解決方案中成長出來的。”所以TE規定,資深工程師的晉升不僅需要本事業部的CTO同意,更需要其他事業部的CTO共同投票。在這樣的體制下,倘若一個工程師只在自己部門里做得出色,卻從未幫助過其他同僚,不被其他CTO們了解,自然難以獲得廣泛認可而晉升。這樣的機制鼓勵TE的工程師們積極地相互幫助,既成人之美,又累己之功。
不僅如此,按照張超的說法,TE更鼓勵人才在不同部門之間的流動,工程師們轉崗、輪崗的自由度極高。中國事業部聯席委員會就為之提供了方便,使得不同部門在人力上的協作變得十分順暢。
而在技術層面,工程師們的合作更是“頻繁地相互借鑒”。因為市場變化極快,產品開發周期從按年計算變為按月計算,不同業務部門需要更多的技術互通。
Jason告訴記者,其事業部在高速率數據傳輸方面的技術十分先進,已經開始被汽車、工業自動化領域的同事采用,加入產品設計中。與此同時,電子數據通信部也向消費品事業部“取經”,學習手機連接器快速迭代的訣竅;還從寬帶網絡事業部覓得應對極熱、極寒、潮濕環境的設計關鍵……從而,節約了研發成本,更節約了寶貴的開發時間,為TE產品贏得市場先機打下了基礎。碰巧的是,在采訪結束后的一周,Jason調任至傳感器部門出任副總裁,TE的跨部門交流由此更可見一斑。
團隊間的協作之外,TE也十分重視團隊內協作的效率。宋博士就將每月最后一個周五下午的一個時段變為團隊的“務虛”會,大家討論工作之外的所見所聞,甚至共同探討、推導《地心引力》電影中的場景,確定兩個太空人剪斷相連繩帶能給予對方多大力量的助推,會產生怎樣的后果……以此磨合團隊協作,提高共事的默契程度。
正因有這些手段,TE才能維持高效的自組織協作,即便面對市場劇烈變化,將項目開發周期從2年縮短到現在的幾個月,也未顯現出創新疲態,技術儲備仍在不斷增加,產品投放有條不紊。
由此可見,對于TE而言,工程師精神指引著整個公司的管理風范,推動更有力的創新、更高效的協作——這是TE對內在傳承的覺醒,也是獲得基業長青的關鍵。我們更期冀更多的公司能從中受到些許啟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