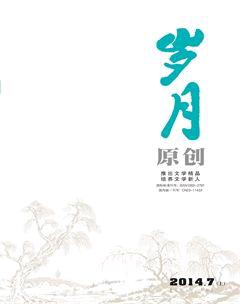小說的確定性與非確定性
紅孩
多年前,當有人問我小說和散文、詩歌的關系時,我曾經說:小說是我說的世界,散文和詩歌是說我的世界。我這樣講,似乎把這三種文體的外延給框定住了。對我的這個觀點,絕大多數寫作者最初聽到都持肯定的態度,有相當多的人在各種場合也多次引用過。我為此也在較長的時間里為自己的創造得意過。應該說,我的這種觀點在一定程度上是成立的,尤其在傳統的敘述性小說創作上,是無可厚非的。
也就是說,文學在某種程度上是可以被確定的。具體說,小說是可以被確定的,散文和詩歌也是可以被確定的。按這個邏輯,何謂小說、散文、詩歌,是應該可以給個明確的定義的。在現代漢語詞典中,“小說”一詞的解釋為:一種敘事性的文學體裁,通過人物的塑造和情節、環境的描述來概括地表現社會生活。“散文”一詞的解釋為:1指不講韻律的文章;2指除詩歌、戲劇、小說外的文學作品,包括雜文、隨筆、特寫等。“詩歌”一詞的解釋為:泛指各種體裁的詩。“詩”的解釋則為:文學體裁的一種,通過有節奏、韻律的語言集中地反映生活、抒發感情。很顯然,以上對三種文學體裁的解釋都十分勉強,其確定性并不明顯,而且三種解釋之間互相融合,這就給創作者提供了多種可能的嘗試。對于研究者,文學的愛好者,在確定某個文體的確定性時,出現了模糊不清的感覺。
長期以來,對于文學,我們往往像對待政治一樣,總愛給它以一個確定性的說法。而在藝術創作中,也總愛以一種形式、一種權威的標準來引導整體的創作,特別是在各種評獎中,也會出現以一種形式或幾種形式來總領整個的創作形式。于是,我們會看到,在已經發表和出版的大量的作品中,不論在題材還是在創作手法上幾乎都是雷同的。正因為如此,有人公開站出來說,中國當代文學出現了審美疲勞,即使面對莫言、王蒙、賈平凹、張煒等眾多的名家。
那么,我們的文學創作有沒有出現過百花齊放的時期呢?當然有。一是上世紀“五四”時期,另一是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改革開放初期,這兩次的文化變革,其意義不僅改變了我們長期固有的文風,也推動了整個社會的政治進程。究其個中原因有很多,很重要的一條是當時的作家、藝術家大都受到西方文藝思潮的影響。如果沒有外來思想的跟進,光憑國內一些文化精英的呼喚是很難成功的。
進入新世紀已經十四年了,改革開放也已經三十余年了。今天的文學顯然已經不是三十年前的景象了,有人認為現在才是文學的正常樣子。而過去一篇小說、一首詩動不動就轟動全國,無論如何是一場全民的精神病態。對此,我不完全茍同。我以為,一個時期自有一個時期的精神訴求,轟動是正常的,不轟動也是正常的。八十年代初,形成兩大陣營,一種是寫實主義的,強調小說的故事、情節與塑造人物;另一種則提出淡化故事情節,消解人物,兩條路數都有成功的作品。顯然,就大多數讀者而言,前者更容易被接受。而對于后者,更容易接受的幾乎是大多數校園學生和有探索精神的作家、學者。這種爭論持續了很長時間。進入九十年代以后,有作家提出“向內轉”——即遠離現實,關注自我,寫人的內心世界,很快得到一大批學院式寫作者的支持。也就是從那時起,伴隨著市場經濟的如火如荼,文學逐漸被邊緣化,圖書、報刊出版市場出現了極大的滑坡,以至有相當多的文學期刊被迫停刊。
如何看待九十年代以來的中國文學,具體說,如何看待就九十年代以來的小說,在理論界一直是個復雜的問題。幾年前,我曾提出好小說的三個標準:一,對推動民族的思想文化進程是否構成影響;二,是否塑造出了典型人物,如阿Q、駱駝祥子那樣經典;三,是否形成了獨特的作家地域語言。在這里,我沒涉及小說的技巧、形式創新問題。即使這樣,有很多的作家也覺得我提得太高了。說如果按照我的這三條標準,自九十年代以來,中國沒有一個小說家能做到。我說好啊,既然沒有一個作家能做到,那就說明小說界出了問題。事實也確實如此,這些年來,文學界除了熱鬧了一些作家的名字,作品本身并沒有走入讀者的內心。茅盾文學獎、魯迅文學獎的獲獎作品的命運大致如此。
一個小說家寫了一輩子,如果沒有一個筆下的人物被讀者記住,這個作家肯定是不幸的。這就如同一個歌唱家,唱了一輩子沒有自己的成名曲,其歌唱家的稱呼就值得懷疑。面對這樣的困窘,我相信有很多作家一直在內心焦急。于是,在傳統與現代之間,人們在不斷地尋找出路,尋找癥結的所在。
我們高興地看到,在散文創作中,有一大批畫家,如吳冠中、黃永玉、范曾、韓美林、于志學、伲萍、陳丹青、崔自默、陳奕純等人先后寫出了大量的作品,這些散文以其對人生的獨特感悟和對事物的獨到描寫已經越來越被讀者所青睞。以我的個人感受,作家應該拿出一定的時間,多向美術、音樂、戲劇、舞蹈、雕塑、宗教、建筑等其他藝術門類學習,同時也要向國外的藝術家學習,學習他們的思維方法、文字的表達形式和創作的技巧。倘不如此,只是一味地關起門來,盲目地寫,做重復的勞動,即使再過二十年,也很難改變中國文學的現狀。我們決不能因為有人得了諾貝爾文學獎,就以為中國文學怎樣了。那只是幾個評委的標準,而不是文學的標準。
我所以寫了以上的話,緣于我最近看了一組張瑜娟的小說。包括本期雜志重點推出的《所有的相逢都是重逢》。張瑜娟是陜西的一位青年女作家,她畢業于西安美院,長期從事文化創意產業。近幾年,在繪畫的同時,開始從事散文和小說的創作。由于長期做報紙副刊編輯,我接觸過一些非職業化寫作的作家,他們在日常的生活中大多從事其他藝術門類,也有的經商或從事政府機關工作。幾廂比較起來,我更喜愛畫家寫的作品。因為,他們的作品從創作開始到結束,給人的感覺是常常帶有很大的不確定性。
以張瑜娟的《所有的相逢都是重逢》為例。這篇小說有別于當下文學報刊的小說路數,她不是在敘述故事,或者說根本沒有故事,也沒有完整的情節,它完全是作者思想的流動,我姑且把它看作是一部意識流小說,也可以叫心理小說。在這里,夢是非具體的,夢中的女人也是非具體的,甚至夢中的城市建筑、畫水的畫都是非具體的,但在所有的非具體的疊加在一起后,小說給你傳遞的又似乎是非常具體的,確定的,它讓你更加地接近真實、接近現實、接近自己。特別是讀完結尾,讓你不由拍案叫絕。說實話,這種現代超現實的寫作我已經多年沒有見到過了,過去偶爾見到,但總覺得夾生。但張瑜娟不同,她已經很熟練地掌握,讓你看不到模仿的痕跡。endprint
心理小說的寫作是需要才氣的。這其中既包括對通篇作品的布局,更包括思想的豐富與精辟,而且這種思想是跳躍的,是靈性的,是你在絲毫未經準備的情況下隨著自身意識的流動而閃現的。其創作的原則是我思故我在,我在故我思,正反都成立。在這篇一萬兩千多的文字里面,你在閱讀時會隨時被作者靈性的思想所吸引,如果要是在文字下劃重點線,至少要劃三四十處,盡管它會使你的閱讀節奏慢下來。如:“虛幻其實是個大的整體,讓人不會糾纏在細節里,像瞇起眼睛看一件剛開始上調子的素描,意義在于朦朧、不確定,又其實早已暗含了架構,逃也逃不掉地在不必追究里,模糊了知覺。”又如:“我每日都活得差不多,甚至于極其相似。我每日穿行于一段繁華的街道,也許那繁華是曾經的繁華,因它曾是繁華的,于是在城市不繁華的各處得到建設以后,這段曾經的繁華便呈現出頹然,甚至于敗落,破敗不堪地承受地下排水系統的整修以及人行道的改建,修了幾次,改了幾回,仍在修,在改,每一次都無法徹底,仿佛在為一個衰老的病人做內臟手術,沒法徹底去摘除或修補,于是總在反復,治不好也死不掉。”再如:“最初我是計劃著怎么過的,從不認為自己會像機器運轉,我若是機器,誰還能是真的自己?我一直認為自己是個至誠至真的人,與太多人相比,我相信是這樣,可是這是經不住審視的,起碼經不住自己的審視。歲月,不長的歲月也有力量改變最初自己以為既定的那些。”面對如此多對生活深刻思考的語言,我相信讀者絕不會嫌它是累贅而放棄,相反,讀者一定會引起強烈的思想和感情的共鳴。
我注意到,在這篇小說中,作者還恰當地運用了象征手法,將半條灰色的絲巾、畫水的畫、女人的模糊印象等,反復地出現,從而增加了小說的意象,使讀者讀來更有藝術的質地,也極大地增加了小說的藝術魅力。這種手法,過去有人運用過,但在當代的青年作家中,幾乎很少有人運用。不是他們不知道,是他們缺少這種藝術的自信與自覺。
任何作家的創作都是自我的。是從我出發的。但從我出發,并不是以我結束,而應該是以我們結束。如果人生是一條直線,作家攫取的生活無非是直線中的一個線段。作家寫作時,對這個線段的描寫是確定的,但它所呈現給讀者的一定是對線段兩端無限的延長,否則,這個作家的寫作就沒有多大意義。從我到我們是藝術美學的接受過程,也是一個哲學過程。
所有的相遇都是重逢。這不僅是這篇小說的一次思想傳遞,也是在創作技巧上的讓我們有一次很好的回望。如是,我十分看好張瑜娟的這種畫家式寫作。
責任編輯:王政陽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