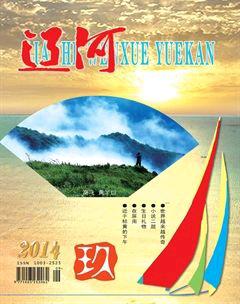寬恕
周月霞
孫旺財快死了。娘停住腳步,輕輕說。
他早就該死!
別這么說,那年頭……
可他用棒子面窩頭喂狗!我一想到此,就恨得牙根癢。
我十二歲那年,正趕上三年自然災害,全國處處吃“低標準”的饑餓年代。挨肩的三個弟妹最小的才六歲,都是長身體能吃的時候,加上年邁的爺爺奶奶,只有母親一天掙六個工分,分到家的糧食根本就不夠一家半年吃的。母親總是野菜樹葉一大盆摻上一小碗棒子面在鍋里蒸,我們用碗盛著吃。那年秋后分糧食,因為我爹是烈士,瞅瞅我們個個面黃肌瘦的,村支部特別照顧,多分給我們家一口袋玉米。我和娘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剛把玉米推回家,沒等氣喘勻停,孫旺財就帶著兩個壯漢進了門。他說,上邊有指示,要照顧更困難的!不由分說推走了救命的糧食,娘絕望地抓起了農藥瓶子,以死相挾。可任憑娘怎么央求,孫旺財頭都不回。
孫旺財,你不得好死!我們兄妹幾個抱著娘嚎啕大哭,詛咒他。那狗救過一個軍長和他爹的命。也是天意,狗吃了窩頭也沒擋住死。上邊就怪罪下來,他的隊長給擼了,老婆也餓死了。咱家要不是遇到貴人,我每回上工干活挖野菜的筐子里總給悄悄放幾個棒子軸,才挨過年,不然,你們幾個也不知誰會餓死……娘深深的嘆息聲把我從記憶里喚回。
鄉(xiāng)間小路,坑洼不平,我走得有點喘。志良,孫旺財說,見不到你閉不上眼……
我終于明白了娘急急喊我起床匆匆趕路的原因。娘的白發(fā)在曙光里泛著金色。八十二歲的娘,身板纖瘦卻挺得很直,娘甩開我的攙扶,腳步幾乎能用輕盈形容。
孫旺財比娘小不下十歲,癱瘓了三四年了。娘說,他有時候餓得吃自己身上的虱子。快死了身邊也沒個親人守著。他家那棟許多年前在村里最宏偉的建筑物近在眼前,三間坯房歪歪斜斜像一陣風就能吹倒。屋子周圍一片荒涼,只有屋后那棵大槐樹枝繁葉茂。
東里間屋,離北墻一步遠的房梁用根木柱子頂著,木柱子人頭高的地處很光滑,粘著幾根白頭發(fā),肯定是孫旺財平時蹭癢蹭的。叔,志良來看你了……
娘好似聞不到孫旺財?shù)纳眢w散發(fā)出的臭氣,附在孫旺財?shù)亩呎f話。聽到娘的呼喚,孫旺財慢慢睜開了眼睛。
他嘴角抽動,渾濁的眼珠亮了亮,又暗下去,就像快沒電的燈。娘把耳朵湊到他的嘴邊,聽他斷斷續(xù)續(xù)地吐著字。孫旺財已經(jīng)回光返照了,額頭光滑得像綢緞。他的喉嚨里咕咕響,就像冬天的白頭翁躲在雪地里掙扎。
聽著聽著,娘忽然轉回頭看我,我看到娘的眼淚像斷了線的珠子似得往下流。叔,原來,那些棒子軸是你給俺的啊……志良,你快叫,叔,志良他不恨你了……娘一邊哭著一邊踉蹌著把我拽到孫旺財?shù)拿媲啊?/p>
旺財爺,我來看你了……聽到我的話,孫旺財渾濁的眼睛突然睜得又大又亮,怔怔地盯著我看了好久,眼角緩緩滾下一顆淚。那淚讓我的心猛地一顫,多年之前,有一雙眼睛里也這樣滾落下一顆淚。
我逃出了一片哭聲的小屋,逃到那棵大槐樹前。大槐樹下埋著軍犬賽虎。
賽虎吃的窩頭里有我從母親手里搶過來的農藥。那天,我躲在槐樹后邊,看著賽虎抽動著四肢,肋骨怒張,慢慢沒了呼吸。它深凹的眼珠里滾下一顆大大的淚。
三十年了,那顆淚時時滾進我的夢里。
我撲倒在賽虎的“墳”前,請求寬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