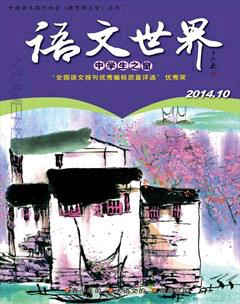貴州,山上有“文化”美景在地下
單之薔
說起貴州,我腦海中立即浮現起一幅畫面:在黔東南的清水江邊,在蒙蒙的細雨中,經過幾個小時的徒步跋涉(不通公路),我看到了遠處山坡上的苗寨,遠遠望去,寨子高低錯落地掩映在繚繞的云霧中,房子全是二層的木樓;走近寨子,就聽到一陣輕悠悅耳的“叮當”聲,原來這個寨子是一個銀匠村,這“叮當”聲是打制銀器的聲音。
我欣賞這里苗族民居的陽臺,從房間延伸出的陽臺,圍繞著一圈座位,很有獨創性的是:傾斜出去的靠背。坐下把身子斜依在上面,欣賞著外面的青山綠水,是一件很愜意的事。在村長家中,我坐在這樣的陽臺上,和村長一家人聊天。非常有趣的是,他室內的三道房梁上分別筑有三個燕巢,有一個燕巢竟筑在了房間的最深處,我們說話時,燕子飛進飛出,穿梭不已。這和城里人的寵物完全不同,人和燕子仿佛是一種協同共生的關系。
這是貴州人文方面幾年前給我留下的生動印象。
在自然方面,貴州給我的印象是全是山、多溶洞。用地理的語言講,貴州是中國最典型的山地省,換一個說法,貴州是中國唯一一個沒有平原的省。貴州在自然上還有一個特點,就是貴州是中國的“喀斯特(巖溶地貌)省”:近74%的大地是巖溶地貌。
然而,這自然和人文上的特點卻對貴州追趕現代化,成為經濟大省貢獻不大。
雖是山地省,但貴州的山卻缺少像黃山、廬山、峨眉山那樣令游客趨之若鶩的名山。
同是喀斯特地貌,廣西有桂林山水那樣世界級的喀斯特峰林風景,云南也有像石林那樣的劍狀喀斯特景觀。但在貴州喀斯特卻演變為大面積的“石漠”。
山地交通不便,勞動生產率也不如平原,因此山地的經濟和社會發展緩慢是一個普遍的世界現象。如果用所謂現代化的各種標準,如國民生產總值、人均收入等看貴州,那么貴州的確落后,可以說,貴州雖地處內地,卻是“中心的邊緣”和“現代化的飛地”。
那么貴州的優勢是什么呢?其實貴州的優勢就在這“落后”中,因為落后,所以貴州許多地方躲過了一次又一次的追趕現代化的運動;因為落后,貴州保持了較為原始的生態環境,貴陽附近保留有七十多公里的森林帶,這在那些先進的經濟大省是不可能的;因為落后,貴州的鄉鎮還較多地保留了古樸的風貌。
山地比平原經濟落后,但山地比平原“多樣性”豐富。因為大山的封閉,因為山地垂直分布著不同的氣候、土壤、植被、動物等,這也造成了不同的谷地之間、不同的海拔高度上分布著不同的民族。貴州少數民族的豐富性令人嘆為觀止。按照現在劃分的少數民族,貴州的少數民族種類少于云南。但少數民族的劃分和確認是一個很復雜的有爭論的學術問題,就具有不同文化的族群而言,貴州未必少于云南。僅就苗族來說,較早進入貴州的日本人類學家鳥居龍藏就把苗族分為黑苗、紅苗、白苗……這僅是根據服裝顏色劃分的,根據其他標準,我們知道的還有長角苗、短裙苗等。
少數民族文化的多樣性是貴州最珍貴的資源。我不記得用過貴州何種的工業產品,但我卻收藏有來自貴州的侗族的背兒帶、苗族的百鳥裙和水族的銀項圈。在北京潘家園民間藝術品市場,活躍著一批貴州賣刺繡和銀飾的苗族、侗族人,他們是靠貴州獨特的少數民族的文化生存在北京的。貴州還有珍貴的東西在地下,那就是溶洞。溶洞可以看作是一種負地形,仿佛是地上地形的倒置。貴州的“桂林山水”和“云南石林”在地下的溶洞里。中國的傳統文化中沒有欣賞地下洞穴和洞穴探險的傳統,因此中國人不了解自己的地下世界之美麗。我們給名山排名次,有三山五岳、十大名山,但我們不了解地下的洞穴,因此也就沒有“十大名洞”。如果評選名洞的話,前幾名一定是在貴州,就目前全國已探知的洞穴而言,最長的洞是貴州綏陽雙河洞,此洞竟分為上、中、下三層,結構奇特復雜,已測長度達70.502公里,想象一下吧,一個七十多公里的錯綜復雜的洞;貴州還有堪稱最美的洞——畢節的織金洞;最大的洞中庭是紫云的“苗庭”……貴州的地下世界可能是中國或者世界最美的。
從經濟的角度看貴州,或者戴著現代化的有色眼鏡看貴州,貴州是“落后”的,是小省,是中國經濟的“盆地”,但換一種目光看貴州,從文化的、從生態的、從多樣性的角度看,貴州就是一個大省,一個高地,是中國的一塊珍寶。
貴州完全不必在“現代化”和“先進”面前自卑。其實人類的許多活動無論是搞現代化還是發展經濟都是一個“試錯”的過程,現在西方對現代化和工業化運動有大量的反思和批判,西方的后現代社會就是對“現代化”的一個反動,它啟示我們:“現代化”并不是一個必不可少的過程。
因為落后,貴州有一種后發優勢,這種優勢就是可以省去“試錯”的過程,借鑒先行者的經驗。譬如,沿海地區鄉鎮企業的大發展是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的,發達地區的城市改造和鄉村現代化浪潮把老街區和老房子拆除干凈,把城市和鄉村搞成“千人一面”,貴州可以躲過此劫。
貴州應該告別“現代化”和“GDP”崇拜,認識到“落后”也是一種優勢,從“落后”越過“現代”進入“后現代”,這或許是貴州的希望所在。
(選摘自《中國國家地理》2004年第10期)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