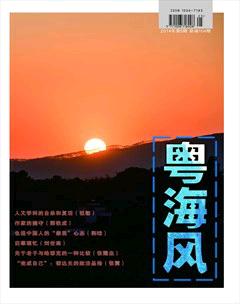關于老子與哈耶克的一種比較
張耀杰
上海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韋森教授新近出版的《重讀哈耶克》的代導論《良序社會運行的基本原理》,是他此前為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新中文版所寫的導言;其中引用的篇首題記“天有顯道,厥類惟彰”,出自《尚書·周書》的“泰誓下”。
2014年5月9日,韋森教授在“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寫作和出版的時代背景”的演講中,首先引用的篇首題記依然是“天有顯道,厥類惟彰”;接下來才是哈耶克的幾段經典語錄。像這樣的引用方式,讓我聯想到曹禺創作于1936年的四幕劇《日出》,其在正文之前先是引用老子《道德經》七十七章“天之道,其猶張弓歟?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余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余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余”;接著又引用了源自基督教《舊約》和《新約》的七段經典語錄。
最近一段時間里,盡管從韋森的演講和文章中得到許多教益,本文關于哈耶克的諸多引文也直接來自他的《良序社會運行的基本原理》;但是,我還是要明確指出:像這樣中西合璧的語錄引用,其實是一種格格不入甚至于背道而馳的牽強附會。為了便于實證研究,本文打算結合曹禺《日出》的相關劇情來展開討論。
“天之道”與“人之道”的極端演繹
曹禺《日出》的戲劇情節并不復雜。劇中的女主人公陳白露是一位聰明美麗的女學生,父親去世后失去經濟保障,只好依附于大豐銀行經理潘月亭,被包養在某大都市的大旅館里,過著見不到陽光的“放蕩,墮落”的“發瘋的生活”。
陳白露從前的“朋友”或者說是初戀情人方達生,從鄉下老家前來英雄救美,卻在與她相處的幾天里,逐漸認識到整個社會“損不足以奉有余”的黑暗與不公,最后昂首走向高亢洪亮地合唱“日出東來,滿天大紅!要想得吃飯,可得做工”的《軸歌》的砸夯工人,以及由他們所象征的號稱是“天之道損有余而補不足”的陽光天堂東方紅的彼岸世界。
但是,留在方達生身后的,是由既是替天行道的“閻王”又是天下為公的“財神”的金八,所主宰操縱的一場中國特色的“存天理,滅人欲”的天譴天罰:
劇中的出場人物,無論是資產階級的有余者還是無產階級的不足者,都面臨著比所謂“損不足以奉有余”的“人之道”更加恐怖黑暗的既要“損有余”又要“損不足”的人生絕境。已經走投無路卻不愿意追隨方達生追求陽光天堂“天之道”的陳白露,更是吟誦著詩人前夫留下的天堂神曲——“太陽升起來了,黑暗留在后面;但是太陽不是我們的,我們要睡了”——而喝藥自殺。與陳白露同樣失去父親的砸夯工人的女兒小東西,在此之前已經為捍衛自己的處女清白而在下等妓院里上吊自殺,從而充當了“存天理,滅人欲”的天道天理的神圣祭品或者說是純潔善良的犧牲羔羊。
在《日出》第一幕中,由于“代表一種可怕的黑暗勢力”的金八,一直躲藏在幕后為非作歹,曹禺只好通過人物對話來加以介紹。按照旅館的服務生王福升的說法:“金八爺!這個地方的大財神。又是錢,又是勢,這一幫地痞都是他手下的,您難道沒聽見說過?”
陳白露聽了,開始擔心小東西的命運:“(低聲)金八,金八。(向小東西)你的命真苦,你怎么碰上這么個閻王。——小東西,你是打了他一巴掌?”
長期把陳白露包養在大旅館里的潘月亭,對于金八的評價是:“這個家伙不大講面子,這個東西有點太霸道。”
潘月亭的銀行襄理李石清對于金八的神秘身份另有介紹:“本來公債等于金八自己家里的東西,操縱完全在他手里……”
在1936年前后的中國社會,像金八這樣集替天行道的“閻王”與天下為公的“財神”于一身的一手抓權一手抓錢的神秘人物,所對應的只能是蔣介石、杜月笙之類青洪幫出身的皇帝以及準皇帝式的權貴人士。
劇作家曹禺創作《日出》時的職業身份,是天津河北女子師范學院的英文教師。基督教《圣經》恰好是他給女學生講課的英文教材。《日出》劇本之前的八段引文,除了第一段出自中國本土的老子《道德經》之外,其余七段全部出自基督教《圣經》。但是,貫穿于這七段《圣經》語錄的核心思想,并不是耶穌基督承擔罪責、遵守契約、政教分離、平等博愛的高貴精神,而是老子《道德經》所傳達的中國特色的替天行道、天下為公、吊民伐罪、天誅地滅的“存天理,滅人欲”的天譴天罰。
比起實際壟斷替天行道、天下為公的政治權力和經濟命脈的金八來說,劇作者曹禺連同空喊“天之道損有余而補不足”的革命口號的自傳性人物方達生,表現得比金八更加虛偽也更加險惡。曹禺在《日出》中不僅精心安排了沒有出場的小東西的砸夯工人父親、黃省三的三個兒女以及李石清的小兒子的無辜死亡;而且通過出場人物陳白露和小東西自裁自贖的獻祭犧牲,為自傳性人物方達生一個人走向“天之道損有余而補不足”的陽光天堂,提供了兩個美好善良的犧牲品和墊腳石。
金八的一手抓權一手抓錢的劫財劫色,并沒有殘酷惡毒到直接葬送個體生命的地步。沒有損害到金八一根毫毛的方達生,卻偏偏仗著救苦救難的神圣名義,把劇中兩位美好善良的弱女子陳白露和小東西送上了死路。從這個意義上說,空喊“天之道損有余而補不足”的革命書生方達生,所扮演的其實是與“代表一種可怕的黑暗勢力”的金八主動合謀、殊途同歸的偽善幫兇的角色。
用階級論觀點來加以評判,《日出》中的相對有余者潘月亭,屬于大資產階級的資本家。黃省三、李石清、陳白露、方達生這些人,屬于無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單就黃省三來說,這樣一個犯下人命大案并且已經進入法律程序的刑事犯,與他此前曾經就業的大豐銀行之間,已經完全不存在人身依附式的經濟債務關系,應該對他承擔依法管制及依法救濟的社會責任的,是掌握并且行使公共權力的政府司法機關及民政部門的官員們。被法庭釋放的黃省三,完全沒有理由撇開政府公共權力部門去欺軟怕硬地向潘月亭發泄階級仇恨。
在官本位的中國傳統社會里,真正剝奪壓迫無產階級不足者的,并不是通過擴大再生產創造社會財富的資產階級有余者潘月亭,而是像金八那樣既不創造財富也不服務民眾的一手抓權一手抓錢的絕對有余者。劇作家曹禺把黃省三的個人及家庭悲劇直接歸罪于資產階級的潘月亭,顯然是對于像金八那樣壟斷掌控公共權力和公共財富的官商一體的政府官員欺軟怕硬的偏袒開脫。
工商社會的損有余而補不足
概括了說,曹禺在《日出》中展現了三個層級的社會形態:第一個層級是由潘月亭主導的“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余”的現實社會。第二個層級是由一手抓權一手抓錢的“閻王”加“財神”的官商大佬金八,主宰操縱的既要“損有余”又要“損不足”的人間地獄。第三個層級是由方達生連同砸夯工人所代表、所追求的號稱是“天之道損有余而補不足”的烏托邦式的彼岸天堂。
而在事實上,隨著潘月亭的大豐銀行破產倒閉,被曹禺和自傳性人物方達生歌頌為擁有陽光天堂的砸夯工人,必然要淪落為像黃省三那樣下崗失業、走投無路的不足者。套用哈耶克的話說,第三層級的“損有余而補不足”的“天之道”一旦強制性地付諸實現,必然是比金八所主宰的既要“損有余”又要“損不足”的人間地獄更加恐怖黑暗的“奴役之路”。1958年前后用人類社會根本不可能實現的烏托邦式的極端高調,強制幾乎所有中國人天下為公、大公無私吃大鍋飯、過集體生活的人道災難,就是最有說服力的事實證據。
放眼已經充分世界化的現代地球村,為包括曹禺在內的絕大多數中國人所不愿意虛心接受的社會現實是:在《日出》所呈現的三個層級的社會形態之外,部分發達國家已經建設完善了另一種社會形態,也就是哈耶克等西方思想家所堅決維護的既要“奉有余”也要“補不足”的現代工商契約及民主憲政的現代文明社會。
在《通往奴役之路》第一章,哈耶克著重介紹了作為西方現代文明社會成長根基的個人主義:“由基督教與古典哲學提供基本原則的個人主義,在文藝復興時代第一次得到充分發展,此后逐漸成長和發展為我們所了解的西方文明。這種個人主義的基本特征,就是把個人當作人來尊重;就是在他自己的范圍內承認他的看法和趣味是至高無上的——縱然這個范圍可能被限制得很狹隘——也就是相信人應該發展自己的天賦和愛好。……個人活力解放的最大結果,可能就是科學的驚人發展,它隨著個人自由從意大利向英國和更遠的地方進軍。”
對于個人自由來說,最為切實可靠的物質保障是個人本位的私有財產,用哈耶克的話說:“我們這一代已經忘記,私有財產制度是自由的最重要的保障,這不僅對有產者來說是這樣,而且對無產者來說一點也不少。只是由于生產資料掌握在許許多多的獨立行動的人的手里,才沒有人有控制我們的全權,我們方能以個人的身份來決定做我們要做的事情。如果所有的生產資料都掌控在一個人手中,不管這是在名義上是屬于整個‘社會的,還是屬于一個獨裁者的,誰行使這個管理權,誰就有全權控制我們。”
現代工商契約及民主憲政社會個人本位的自由自治、契約平等、民主法治、憲政共和的良性秩序,正是以財產私有、意思自治的個人自由為前提條件的。哈耶克認為,當年許多以進步自居的社會主義者,希望通過消滅私有財產來縮小收入差距、實現社會財富的平等均衡,是一種莫大的誤識:“雖然在競爭社會中,窮人致富的可能性比擁有遺產的人的可能性要小得多,然而,只有在競爭制度下,前者才有可能致富,且才能單憑自己的努力而不是靠掌權者的恩惠致富,才沒有任何人阻撓個人致富的努力。”
這段話著眼的主要是個人與個人以及自然人與企業法人之間意思自治、雙向選擇、互惠互利、平等合作、權利義務充分量化細分的契約平等、公平競爭。就三人以上或當事多方的公共領域來說,“如果‘資本主義這里是指一個以自由處置私有財產為基礎的一個競爭體制的話,那么,更要認識到,只有在這種體制中,民主才有可能。”
哈耶克所說的民主,顯然是嚴格限定在法治框架和法律程序之中的程序正義優先于實體正義的有限民主。公民社會是不可以撇開正常的經濟文化生活而無休無止地從事民主集會、投票選舉之類群體運動和集體狂歡的。尤其重要的是,民主投票、全民公決的對象只能是公共權力和公共利益,而不是私人領域天然正當的人身自由、思想自由、財產自由以及人與人之間契約平等的男女情愛及工商合作;任何針對私人權利加以越權干預甚至于強制剝奪的所謂“民主”,都是公然踐踏人權的偽民主和反民主。即使在公共政治領域中,民主選舉的勝利一方所爭取的也只是微弱多數,而不是完全壓倒敗壞競爭對手及反對黨派的全票通過和全體同意。民主選舉的失敗一方所要尋求的,是下一輪民主選舉的微弱多數,而不是采取暴力革命的極端手段顛覆推翻正在執政掌權的敵對黨派,進而通過趕盡殺絕的武裝征服來實現敵我斗爭的你非我是、你死我活。
著眼于政府公權力層級上的權為民所賦、權為法所定的憲政制度建設,哈耶克進一步論證道:“國家一旦負起為整個經濟生活制定計劃的任務,不同個人和集團的應處地位(the due station)就必不可免地成了政治的中心問題。由于在計劃經濟中只有國家的強制權力決定誰擁有什么,唯一值得掌握的權力就是參與行使這種命令權。”
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還引用老牌共產主義者伊斯特曼(Max Eastman)的說法,指出了馬克思身上最為深刻的自相矛盾:
馬克思希望通過廢除切實保障個人有限自由的私有財產制度,來實現一種烏托邦式的無限自由:“私有財產制度(the institution of private property)是給人以有限自由和平等的主要因素之一,而馬克思則希望通過廢除這種制度而給人以無限的自由。奇怪得很,馬克思是第一個看到這一點的人。是他告訴我們,回顧以往,私人資本主義連同自由市場的演化,是我們所有民主自由(democratic freedom)演化的先決條件。他從未想到,向前瞻望,如果如他所說的那樣,那些其他的自由,會隨著廢除自由市場而消逝。”
在《通向奴役之路》第六章“計劃與法治”中,哈耶克指出:“撇開所有的技術細節不論,法治的意思就是指政府在一切行動中均受到事前規定并宣布的規則約束——這種規則使得一切個人有可能確定地預見到當權者(the authority)在給定情況中會如何使用其強制權力,并據此知識來規劃自己的個人事務。”
應該說,在哈耶克倡導維護的政府公權力必須與公民個人一樣遵守法律規則及憲法條款的“the Rule of Law”的法治社會里,是不可能出現像金八那樣幕后操縱公債交易的一手抓權一手抓錢的官商大佬的,依法經營的金融企業家潘月亭以及他的所有銀行客戶,盡管會遭遇各種各樣的商業風險,在公債交易中血本無歸、徹底破產的商業悲劇,也是不太可能發生的。只有在像潘月亭那樣的工商企業家得到充分尊重和保護的情況下,整個社會的財富創造和經濟發展才有可能走上健康軌道;沒有工作的不足者,才有可能通過有余者提供的工作崗位而實現充分就業;沒有工作能力的不足者,也才有可能通過有余者的依法納稅而享受到足夠的社會救濟和福利保障。
現代工商社會的價值譜系
參照哈耶克所描述的多層級、多元化、多維度的自由路徑和價值思考,以及胡適所提出的“健全的個人主義”的價值觀念,我在新近出版的《曹禺:戲里戲外》《民國紅粉》《北大教授與〈新青年〉》等多部學術性傳記作品的相關章節中,歸納概括出了現代工商契約及民主憲政社會的共同價值四要素:第一要素是個人層級的自由自治;第二要素是二人世界及當事雙方之間的契約平等;第三要素是公民社會的民主法治;第四要素是政治制度及政權建設層級上的憲政共和。
哈耶克在《通向奴役之路》第二章中,正是基于這種多層級、多元化、多維度的自由路徑和價值譜系,頗為雄辯地區分了既“奉有余”又“補不足”的現代工商契約及民主憲政社會,與打著“天之道損有余而不補足”之類烏托邦式神圣旗號,強制剝奪私有財產并且強制推行計劃經濟的各種社會主義之間的路徑歧異:
“毫無疑問,對更大自由的允諾已經成為社會主義宣傳最有效的武器之一,而且,對社會主義將會帶來自由的信念是真心實意的。但是,倘若允諾給我們通往自由的道路一旦事實上被證明是一條通往奴役的大路的話,悲劇豈不更慘。”
與此相印證,哈耶克在《通向奴役之路》第二章篇首還引用了詩人荷爾德林(F. Hoelderlin)的經典語錄:“總是使得一個國家變成人間地獄的人事,恰恰是人們試圖將其變成天堂。”這樣一句經典語錄在反復創作陽光天堂東方紅式的宗教化戲劇的曹禺身上,得到的是最具說服力的事實驗證。
一直以神道設教、替天行道的儒教先知加抒情詩人的特權身份創作陽光天堂東方紅式的宗教化戲劇的曹禺,1949年之后馬上變成各種各樣的社會主義主旋律的精神奴隸,以至于在精神高壓下陷入精神崩潰。他在社會主義新時代里所創作的包括《明朗的天》《膽劍篇》在內的戲劇作品,再也沒有貫穿于《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艷陽天》之中的被他形容為“原始的情緒”和“蠻性的遺留”的生命張力和藝術魅力。
據曹禺的女兒萬黛、萬昭回憶:“現實生活并不完全像爸爸所期望的那樣,政治運動、文藝界的批判和斗爭年復一年,一個接著一個,永遠沒個頭兒,涉及的面越來越廣,人越來越多。……他服用大量的安眠藥,50—60年代出現了強迫性神經官能癥的危險精神癥狀,因而不得不多次住進協和醫院治療。”
歸結了說,1840年之前的中國社會的文化傳統和制度框架,完全不存在所謂天人合一的中庸美好,無所不在的其實是“存天理,滅人欲”的二元對立、一元絕對的以天為本、天人對立。能夠享受天人合一的特殊權力的,只有以天子自居并且像金八那樣一手抓權一手抓錢的皇帝、準皇帝,以及自以為掌握著神道設教、替天行道的天道天理的儒教先知帝王師。絕對大多數連讀書識字的機會都享受不到的中國人,所面臨的是隨時隨地像代罪羔羊一樣被抄家征地、罰沒財產、充軍當差、砍頭示眾、滅門抄斬的“存天理,滅人欲”的悲慘命運。老子所標榜的似是而非的“天之道損有余而補不足”的烏托邦理想,比起他譴責詛咒的“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余”的現實社會來說,在“存天理,滅人欲”的反人性、反人類方面,表現得更加恐怖黑暗;與哈耶克所倡導維護的既要“奉有余”也要“補不足”的現代工商契約及民主憲政社會,其實是格格不入甚至于背道而馳的。
(作者單位:中國藝術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