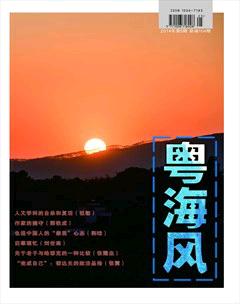杜拉斯文學的美學品格
張向榮
法國女作家瑪格麗特·杜拉斯(以下稱杜拉斯),原名瑪格麗特·陶拉迪歐,她集作家、劇作家、電影編導于一身。杜拉斯的一生專注小說創作,尤其擅長寫自傳體,她的成名作就是她描寫在印度支那生活的自傳體小說《抵擋太平洋的堤壩》,此后又創作出《廣島之戀》《情人》等蜚聲文壇的代表作。杜拉斯曾因獨特的文字及內容曾獲龔古爾文學獎、法蘭西學院戲劇大獎等獎項。
杜拉斯畢生都在與愛情糾纏在一起,她將愛情視為生命之必須,因此她的文學生涯也是她的愛情生涯。她的代表作《情人》就是寫與中國情人之間的愛情。杜拉斯期望通過性的宣泄,剝開愛的真諦,并將愛情中的所獲得的肉體歡愉交付給靈魂的滿足。她曾說自己如果不是一個作家,會是個妓女。的確,在她的世界里,從十六歲開始就與愛欲纏纏繞繞,《情人》中的女孩就是少年杜拉斯的影子。為了追求至高無上的愛情體驗,她可以拒絕外部的喧囂而忘我實踐,甚至以濫情來對抗規則。在《抵擋太平洋的堤壩》中,女主人公蘇珊與哥哥、諾先生的三角曖昧關系與傳統倫理道德格格不入;《情人》中白人少女與黃種男人超越種族的情欲撞擊;《直布羅陀水手》中一個竭力逃避現實的法國男人與在意大利漁村遇見的法國女人踏上未知的旅行——尋找女人的舊愛直布羅陀水手,而直布羅陀水手顯然成為他們浪漫愛情旅程的象征,尋找本身則散發著避世逍遙的意味。
杜拉斯鐘情于自己對愛情的理解,留戀著情欲帶給她的體貼和光華,她更喜歡自說自話。《無恥之徒》《烏發碧眼》是這樣,就連她七十歲時出版的《情人》都布滿了幽怨卻又生機盎然的泛情旋律。杜拉斯不僅創作小說,還有戲劇,如:《來自中國北方的情人》《薩瓦納海灣》《諾曼底海岸的妓女》《英國情人》等。她還擔任電影編劇乃至導演,如:著名的《廣島之戀》《印度之歌》《恒河女子》《樹上的歲月》《大西洋人》等。她筆下眾多的人物個性皆源于她強烈的欲望情結和自我中心主義,這使得她心靈深處充滿無可逃避的孤獨感,由于孤獨,他們往往表現出近乎變態的異樣行為:癲狂、執拗、健忘、嗜睡、故意與他人作對等等。愛情、孤獨,這就是杜拉斯本人,這就是她不顧一切所進行的生命實踐。這一切,都為我們呈現了一個立體的杜拉斯文學話語。
杜拉斯不是簡單的欲望高昂,她的寫作起步于愛欲,駐足于書寫,卻貫穿在孤獨之間的知性清晰和不惑精神。在杜拉斯眼里,孤獨是愛欲的舞臺背景,唯有在孤獨的舞臺上愛欲才顯得“激情蕩漾,回聲悠揚”,才會“安舒自在”[1]。
杜拉斯的孤獨愛情通過“性愛”的快樂而發現人性美的純真本質。在她那么多晦暗文字之下是對回歸自然的渴望。杜拉斯借《烏發碧眼》中“她”和“他”的偶遇,撥開蒙在欲望之上的灰塵,“繼這黃昏之后的黑夜,美麗的白晝便如大難臨頭,頓然消殞。這時候他倆相遇了”[2]。一男一女在黑夜的偶遇,仿佛是一盞明燈,即使白晝消逝,夜也不會再逞淫威,夜幕下的人們也不再恐懼,而是洋溢著與黑夜握手言歡的欣然,好像生命的真面目就此漸漸清晰,這是對情愛充滿期待的杜拉斯。《無恥之徒》中喬治與慕的眼神交流似乎是更讓人感到來自兩性相吸的無與倫比,這是純凈無暇的杜拉斯。期待與純凈分明就是一朵朵熱烈綻放的孤獨之花,生長在杜拉斯神圣的文學園地,它們與杜拉斯的那些心靈植物一同安安靜靜地生長,為她的思維世界帶來不斷更新的活躍色彩。
的確,杜拉斯文學象征著人類最本質和最真實的欲望。這是人類保持生命活力的根本,但又因為它太真實、太袒露、太我行我素,所以,杜拉斯是在一片驚呼聲中橫空出世的。她大膽突破傳統文學的“性”禁區的寫作旨歸,實際上是在做一種放棄的姿態,就是要放棄那些經過粉飾的,與自然本性相悖的道德力量。我們有理由相信,她的“放棄”充滿了自信的底氣,她完全有能力駕馭“性”快樂帶給她寫作上的清高孤傲。生命的載體是肉身的存在,而肉身之所以能生機勃發完全是“性”裂變所產生的能量。“性”是人類得以延伸的唯一途徑,它需要呵護,需要力量和勇氣的支持,然后才能顯示出它超越凡俗的美和光彩,如果單純控制“性”的釋放,只會讓生命枯萎,杜拉斯恰恰注意到了這一點。杜拉斯力求發現承載人類原始欲望的世界意義,讓人感受生存在世界上的各種感受,并且在文本實踐中建立一個既可以支撐生命本體存在而又可以化解人類痛苦的時空交融體,既是在場獨白又是幻覺中的喧囂。
表面看,杜拉斯的孤獨愛情來自于她對內心世界的獨特創造,但當我們深挖杜拉斯的身世后會發現,杜拉斯還是因為潛意識中對自我身份的認同障礙。的確,純粹的人離不開文化的支撐,人生之初的文化對其一生都具有深遠的影響。杜拉斯生于印度支那(現今的越南),十八歲才回到法國,對東方文化的偏愛已經深入到她的每一根神經。回到法國后,她深刻感受到了沒有文化根底的空落感,這也成為她后來創作中所表現出的東西方文化沖突的根本原因。在《情人》中杜拉斯敘述了在與中國情人交往的過程中,因種族隔閡使他們的交往被迫摻雜進了來自世俗的偏見,“人們說,又是一個中國人,大富翁的兒子,在湄公河上有別墅,還是鑲了藍琉璃瓦的。就是這位大富翁,也不會認為這是體面事,決不許他的兒子同這樣的女子有什么瓜葛。一個白人壞蛋家庭的女兒。”[3]再加上現實的困窘,常使她處于不知所措的自虐心理狀態中。但是白種人骨子里的高傲讓杜拉斯不愿撕下那一點點上等人的意識,“她雖然在哭,但是沒有流淚,因為他是中國人,也不應為這一類情人流淚哭泣。”[4]所有這些,都是杜拉斯為十八年的西方文化生活空白經歷讓她在身處西方世界時感受著文化失落后的孤獨。到此,我們不禁唏噓,不管是迷戀也好,孤獨也罷,這都是杜拉斯內心深處剪不斷理還亂的對文化歷程的生死守望。
是的,在重重疊疊的生命歷程中,杜拉斯因為文化帶給她生命的錯位,讓她始終拒絕與外界溝通,只是自顧自構建自己的“文學花園”,在其中享受著簡單、自得而又自閉的文學意境。杜拉斯與傳統文學漸行漸遠,南轅北轍。但杜拉斯并不排斥傳統文學,她甚至會收起矜持,刻意討好大眾。例如,她在《抵擋太平洋的堤壩》、 “印度之歌”系列中的描寫,就是迎合了西方文化對東方苦難經歷的看客心理;還有那些精心構建的日常生活情境:《街心花園》《廣場》等;趕潮流模仿當時流行的后現代文學關于內心獨白的刻畫:《琴聲如訴》《昂斯瑪代的午后》《塔基尼亞的小馬群》等。的確,杜拉斯做到了,在她逝世后其作品始終暢銷不衰,她將現今各路所謂的“暢銷書作家”遠遠甩在身后。
著名法國文學專家徐真華先生這樣評價杜拉斯:“的確,杜拉斯的世界表現了失敗、絕境、猶疑、焦慮、期望、謊言和各種毀滅,簡言之,那是一種顛三倒四、亂七八糟的生活。由此產生了令人不安的奇怪行為:呼喊,也就是瘋狂。因為人們認為:瘋狂這個詞是杜拉斯式的抗爭中最符合邏輯的表達形式。時光悄然流淌,空虛進駐,生命消逝,現實與我們的夢想不再相符。杜拉斯通過其敏銳的眼光和女性特有的音調來塑造形象,描寫情感,重現在記憶或現實中尋回的時刻。人類的一切變化幾乎總是通過婦女——無論她們是妻子、情人還是母親——而實現的。這些變化體現了對某些制度束縛的拒絕。而婦女的社會生存狀況,或廣而言之,人類的社會生存狀況正是在這些不合理制度的禁錮之下。”[5]
杜拉斯文學不與凡俗陳陳相因,敢于袒露自我,勇于歌頌性愛的光彩。她在長期的寫作過程中,將傳統文學所代表的寫作范式用水滴石穿的精神進行著杜拉斯式改造,不虛美,不隱惡。這既是杜拉斯對文學的殷切守望,也是她對孤獨愛情的人文關懷。杜拉斯已離我們遠去,但是她的文學光華依然照耀后人,讓人難忘。
(作者單位:廣東外語外貿大學)
引用作品:
①法 瑪格麗特·杜拉斯.情人[M]. 王道乾譯.上海譯文出版社, 1997.
②法 瑪格麗特·杜拉斯. 烏發碧眼[M].南山譯.上海譯文出版社, 1997.
③徐真華 黃建華 20世紀法國文學回顧——文學與哲學的雙重品格[M].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8.97
[1]法 瑪格麗特·杜拉斯.情人[M]. 王道乾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97.39
[2]法 瑪格麗特·杜拉斯. 烏發碧眼[M]. 南山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97.104
[3]法 瑪格麗特·杜拉斯.情人[M]. 王道乾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97.74
[4]法 瑪格麗特·杜拉斯.情人 [M]. 王道乾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97.91
[5]徐真華 黃建華 20世紀法國文學回顧——文學與哲學的雙重品格[M].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