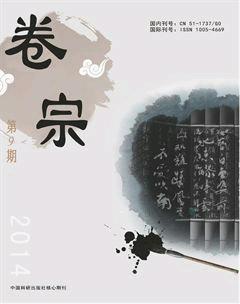職務侵占罪中的共同犯罪問題
李璐
摘 要:共同犯罪與身份的關系,是共同犯罪理論中一個很重要的問題。而我國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條職務侵占罪中也同樣存在共同犯罪的可能性。職務犯罪作為一種身份犯,對犯罪主體有特定要求,那么共同犯罪中不滿足這種特定身份的其他行為人應當如何定罪以及共犯中有其他特殊身份的行為人應當如何定罪。本文認為按照侵犯的特定法益和共犯從屬的原則,應當對共同犯罪的無身份人確定為職務侵占罪;對其中有其他特殊身份的行為人應區別對待。
關鍵詞:職務侵占罪;共同犯罪;身份
我國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條規定:“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單位的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將本單位財物非法占為己有,數額較大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數額巨大的,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處沒收財產。國有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國有單位中從事公務的人員和國有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國有單位委派到非國有公司、企業以及其他單位從事公務的人員有前款行為的,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二條、第三百八十三條的規定定罪處罰。”這一條法律規定提出了兩種不同的犯罪主體,在有同樣法律行為時,所應當適用的不同的法律。這是犯罪主體單一化時的情況,如果實施該行為的有兩個以上不同主體,是否就構成了共同犯罪?如果構成,這種共犯的身份如何界定?對這種共犯又應當以何種罪名定罪量刑呢?本文將根據職務侵占罪中共同犯罪的其他行為人的不同身份進行討論。
1 無身份者與有身份者共同犯罪
1.1 實踐問題
(1)非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單位的人員構成職務侵占罪共犯的情形
企業、單位或者其他單位的人員的近親屬與其共同勾結,共謀財產利益,將本單位財物非法占為己有;但現實中很多情況下是近親屬教唆工作人員進行職務侵占。近親屬作為教唆犯,主要表現為誘導、勸說、催促甚至是威脅工作人員侵占單位財務,致使工作人員產生了職務侵占的故意,并實施了職務侵占的行為。這一行為近親屬是否還是應定職務侵占罪的共犯呢?
(2)工作人員的近親屬并非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單位的人員但直接利用工作人員的便利實施單位財產侵占的行為。
在現實中還有一種情況,就是工作人員實際不知情,行為人利用與工作人員的親密關系,盜取相關財物的情況。對這一類犯罪主體的犯罪又該如何界定?
1.2 理論分析
對于身份犯的共同犯罪來說,如果各行為人均滿足特定的身份要求,自然是可以構成純正身份犯的共犯;如果各行為人均不滿足特定的身份要求,就談不上構成純正身份犯的共犯了。復雜的問題就在于身份犯的共同犯罪中既有滿足身份要求的行為人,又有不滿足特定身份要求的行為人。這就在理論上引發了對身份犯的共犯如何界定的問題。
否定說,認為不具有單位職員身份的人不能構成職務侵占罪的共犯。從理論上講,職務侵占罪的主體是特殊主體,必須由單位的工作人員構成,其他人員不能構成該罪的犯罪主體。這種主體的特殊性,不僅僅體現在單獨犯罪中,對于共同犯罪也不例外,并不能因為是共同犯罪,就可以放寬要求,只要其中有一人是國家工作人員就行了。非單位工作人員并不能因為勾結單位職員就改變了身份變為單位職員。而且對于刑法總則中關于共犯規定的使用前提必須是共同犯罪人的行為均符合犯罪構成四要件,缺一不可。共犯在共同犯罪中要有共同的犯罪故意,實施了共同的行為,侵犯了同一客體,而且首先要符合共同構成罪名的主體要件。推而廣之,這實際上是共同犯罪中的身份問題,即無身份者能不能加入到只要特殊身份者才能實施的犯罪中,無身份者與有身份者實施共同行為,應當以自己的身份確定罪名。
肯定說。肯定說認為,不具有單位職員身份的人可以構成職務侵占罪的共犯。根據我國的刑法理論,行為人的行為符合犯罪構成是承擔刑事責任的依據。而這里的犯罪構成既包括基本犯罪構成,同樣也包括修正的犯罪構成,共犯的構成屬于修正的犯罪構成。根據修正犯罪構成理論,共同犯罪的組織犯、教唆犯、幫助犯,并不具備犯罪構成,而是不具備刑法分則所規定的具體犯罪的基本犯罪構成,但具備修正犯罪構成,這就是他們承擔刑事責任的根據。因此,身份客體對身份者只有相對的專屬性:在單獨犯的場合具有專屬性;而在共同犯罪的場合下則具有開放性,只要共犯中有一人具有該特定的身份,則所有共犯都有侵犯身份客體的可能性。肯定說是目前我國刑法理論的通說,司法實踐中也普遍采取這一觀點。
1.3 筆者的觀點
筆者贊成肯定說。肯定說實際上也就是共同犯罪中的共犯從屬說,共犯的犯罪性質根據主犯的犯罪性質而定。在職務侵占中,不具有工作人員身份的人伙同公司、企業或其他單位的工作人員進行侵占的,仍應認定為是職務侵占罪。這是從所侵犯的法益角度來分析的。對特定身份犯來說是因為他們侵犯了特定的法益,只有他們的特定身份才能夠侵犯這種法益,別人不能侵犯這種法益。在職務侵占罪中所侵害的是行為人所在公司、企業或其他單位的集體利益,行為人之所以能侵害這一法益,正是因為行為人的職務之便。而在共同犯罪中,即使有行為人不具備這種身份,但只要主犯有這種身份,確實利用這種身份實施了這一侵害行為,這種法益就有了被侵害的事實。那么職務侵占罪所要保護的法益就被所有行為人同時侵害了,對其中的行為人自然就應該訂立該罪名。
我國現行的法律也是贊成了肯定說。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貪污、職務侵占案件如何認定共同犯罪幾個問題的解釋的第二條:行為人與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單位的人員勾結,利用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單位人員的職務便利,共同將該單位財物非法占為己有,數額較大的,以職務侵占罪共犯論處。根據這一觀點,上述現實中的問題也可以得到解決。在第一種情況下,非工作人員與工作人員勾結將單位財物非法占為己有,不管其身份是單純的共同謀定,還是誘導、勸說等,只有侵占單位財物這一行為確實發生了,所有行為人均應以職務侵占罪定罪量刑。而第二種情況首先就不構成共同犯罪,只有單一行為人,單位的工作人員毫不知情,并不存在共同故意,共同行為。對這一行為難以界定的原因在于,雖然單位的工作人員不知情,未參加,但財物損失的原因卻與其相關,沒有該工作人員的存在,行為人則不可能實施該行為,如從該單位人員那里偷取其保管相關資料或財物等。在這種情況下,筆者認為對行為人只能定盜竊罪,而若考慮該單位人員在案件中的“作用”,則可以認定由于其過失造成單位損失,可以采用行政處罰等手段進行處罰,故不在此贅述。
2 不同身份者的共同犯罪
2.1 實踐問題
在現實生活中,職務犯罪還存在另外一種情況,職務犯罪的行為人有不同的身份,如其中一個行為人只是普通單位的工作人員,而另一行為人是從事公務的人員。在定罪的時候,應該區分對待還是同樣算作職務犯罪也是一個值得討論的有關身份犯共同犯罪的問題。
2.2 理論分析
關于職務侵占罪中存在不同身份的犯罪主體應該如何定罪在學術界也存在不同的觀點。
第一種觀點為分別定罪說。該說認為應根據主體的不同身份分別定罪。即對公司、企業或其他單位中的國家工作人員定貪污罪,對公司、企業或其他單位中的非國家工作人員定職務侵占罪。
第二種觀點為主犯決定說。該說認為應以主犯的身份來確定共同犯罪的犯罪罪名,主犯是國家工作人員的,應認定為貪污罪,對其他共同犯罪人也按貪污罪定罪判刑;主犯是公司、企業或其他單位中的非國家工作人員的,應認定為職務侵占罪,對其他共同犯罪人也按職務侵占罪定罪判刑。
第三種觀點為主犯決定說與分別定罪說的折衷說。該說認為,如果主犯的身份是公司、企業或其他單位中的非國家工作人員的,全案都定職務侵占罪;如果主犯的身份是公司、企業或其他單位中的國家工作人員的,對具有國家工作人員身份的定貪污罪,對公司、企業或其他單位的非國家工作人員定職務侵占罪。
第四種觀點為實行犯決定說。該說認為應根據實行犯的犯罪性質來確定共犯的犯罪性質。
第五種觀點為特殊主體決定說。該說認為在共同犯罪中有一般主體和特殊主體,應按特殊主體觸犯的罪名來定性。
第六種觀點為特殊主體從重說。該說認為特殊主體與非特殊主體共同實施犯罪行為的,以特殊主體所定之罪定罪,特殊主體中有不同層次的,以其中法定刑重的罪名定罪。
第七種觀點為區別對待說。該說認為如果共同犯罪行為的實施是利用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之便的,應定貪污罪;如果共同犯罪行為僅僅是利用公司、企業或其他單位中的非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之便的,應定職務侵占罪。
2.3 筆者觀點
在這一種情況下,由于犯罪主體本身具有不同的身份性,所以在定罪時不能只考慮其中一人的身份,而應該綜合考慮不同行為人的不同身份以及這些身份之間的關系,這里涉及到的是兩個身份。一個是普通的工作人員身份,另一個是公務員身份。上述的各種觀點均是針對這兩種身份做出的不同評判。筆者認為第一種觀點是不可取的。既然是共同犯罪就應當綜合考慮案件的整體性質,包括共同的犯罪故意,犯罪行為的互相配合、互相協作,這些都使得共同犯罪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而第一種觀點的定罪方式,人為地割裂了共同犯罪的這種內在聯系。其他幾種觀點均承認了共同犯罪的整體性。
筆者認為最后一種觀點是可取的。由于這種情況下存在的兩種行為人都是具有特定身份的,在定罪時必須考慮行為人是利用哪一具體身份進行。根據第一種情況下對侵犯的特定法益的分析,這里同樣要區分侵犯的法益。如果利用的是只有國家公務員才享有的職務之便進行的職務侵占,不管另一行為人具有什么身份,都應按貪污罪定罪。如果利用的只是普通工作人員即可擁有的職務之便進行的職務侵占,這時公務員的身份并未在其中發揮任何“作用”,公務員也只是用普通工作人員的身份侵占了財物,當然只能以職務侵占罪定罪。這與我國立法目的是息息相關的。如果立法將公務員按照貪污罪定罪是為了嚴格要求國家公職人員,對其有比對一般公民有更高的要求,剛才的只定侵占財產罪就與該立法目的不相吻合。如果立法目的不存在加重處罰的要求,那么對公務員也只定侵占財產罪就是合理的。如果在侵占單位財物時行為人的兩種身份都用到了,則應當按照主犯決定說。如果主犯是國家工作人員則以貪污罪定罪。同時對非國家工作人員在與國家工作人員同為主犯的情況下,處以較國家工作人員較輕的刑罰,在國家工作人員為主犯而非國家工作人員為從犯的情況下,處以更輕一些的刑罰。如果主犯是一般工作人員非國家工作人員,則以職務侵占罪定罪。這也是與第一種情況下的共犯從屬說相一致的觀點。
3 結論
由于職務侵占這一罪名本身存在特定的身份的要求,導致對這一罪名共同犯罪的其他行為人的定罪較為復雜。在綜合分析了理論界的各種觀點之后,筆者根據共犯從屬原則得出相應的結論。若其他行為人無特定身份,則應根據其中具有該特定身份的行為人的行為定罪,確定為職務侵占罪;若其他人有國家工作人員的特定身份,則根據行為的具體情況判定。該行為只利用了國家工作人員身份的便利,則應定為貪污罪;若只利用了一般工作人員的身份便利,則應定為職務侵占罪;若兩者均涉及到了,則應按照主犯的性質決定。
參考文獻
[1]李成,《共同犯罪與身份關系研究》,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北京,2007年
[2]劉志偉,《職務侵占罪中的共同犯罪問題》,人民法院報,北京,原刊期號2005.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