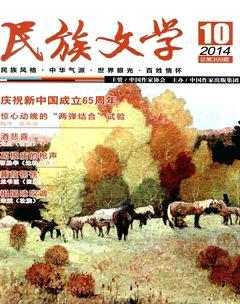沙漠之羊
徐藝嘉
一
第一次遇見美女記者的時候,是西北大漠慣有的晴天,焦灼的陽光投射在一望無際的沙漠上,每一粒金黃的沙粒上都翻滾著熱燙的氣息。
我和周小亨他們幾個一字排開,站在沙漠中一根孤零零的電線桿投射下來的陰影下,這是我們僅有的蔽陰處。我雖一介草羊,但也算是一個名副其實的老兵,已經在這個117點號風吹日曬摸爬滾打,堅守了600多個日落月出,完全具備識別軍銜的能力。她的軍服雙肩上扛著一杠兩星,而我的三個伙伴除劉相資格老一些外,周小亨、陳衛都才是二級士官。算起來,也得喊她一聲首長了。當然,這能力是我內心的一個驚天秘密,人類還真識不破我的廬山真面目。除了周小亨,那個最了解我的兵。
此時此刻,我雖然站在隊尾,卻依然可以耳聞目睹我的三個戰士伙伴激動的心跳聲和潮紅發汗的面孔,眼睛里跳動著壓抑著的獵艷與驚喜。日復一日的極簡生活磨剝了他們的感知,這屁大點的地方常年就翻來覆去固定的幾個人,更不要說有女人出現了。過年時基地曾派文藝隊來演出慰問,那些漂亮女兵穿著露胳膊露腿的演出服唱歌跳舞,羞得他們幾個連抬眼看的勇氣都沒有,整個演出就那樣糟蹋了。說良心話,因為這事兒我有點兒瞧不起他們仨,遇事缺乏骨氣,把我們大漠戰士的尊嚴都丟盡了。我昂首挺胸站在隊尾,盡量保持著一個軍人的標準站姿和威嚴。
首長走近我們了。他把旁邊的美女中尉逐一介紹給我的三個伙伴,并分別握手寒暄。我知道他們需要的是什么,當走到我面前時,我模仿伙伴們的行為,下意識禮節性地抬了抬前蹄表示敬意。我看見他們不約而同地愣住了,十分驚訝地睜大了眼睛……
首長盯著我,禁不住伸出大拇指脫口贊嘆:“嘿,這只羊,神了!”
美女中尉也把持不住,隨即掩嘴笑:“哎呀,這羊太逗了!”
我的兩只犄角上纏著紅頭繩,是一大早周小亨的杰作,說是為迎接上級來視察的首長而作,也是這個綿延幾百里的孤寂荒漠上唯一的一道喜慶色彩。
我為自己的出色表現贏得如此尊重而感到驕傲,這是一個羊戰士所表現出的超常軍姿和軍人的榮耀!我的身材雖稱不上豐潤,但絕對正宗非山寨,骨頭緊貼著一張純正的羊皮,跟我那三個整天被沙漠烈焰烘烤暴曬如風干臘腸的伙伴比較起來,決不輸士氣。
我太了解他們三個了,我和他們是心連心肺連肺的。我像最為洞察世事的族長一樣,此刻他們想些什么,我心里有數。他們的拙舌表達不出的,我一個動作,全有了。
果然,首長發問了。誰養的羊?
周小亨跟被點了贊似的一下子從隊列里跳出來,一只手撫摸著我的頭皮開肉笑地炫耀起來:“報告首長,我養的。這只羊我給它取名叫‘小白,別名‘沙漠之羊,可以跟‘沙漠之狐隆梅爾相提并論,是我們團隊中的一員戰將,是我們的驕傲,特別有人情味,通人性。我們早晨出操它跟著出操,列隊它跟著列隊,我們相處得已經有感情了,每當有寒流和風沙來襲的時候,我們就一起抱團取暖。”我高昂起美麗的頭顱,聽著周小亨的介紹,目視前方,期待得到上級領導和美女記者的認同和贊美。
首長一邊搖著頭一邊贊嘆:“奇跡!奇跡!你們在大漠深處創造了一個奇跡!這次王記者專程下到你們這里來,就是要采訪一下你們在這么惡劣的自然條件下是如何生活、工作和戰斗的,回頭你們跟王記者詳細地介紹一下你們這里的情況,讓王記者回去好好地寫一篇文章報道一下。”他用手一指我說:“尤其是這只‘沙漠之羊,也要好好地宣傳宣傳。”
美女記者一聲招呼,我的光榮形象就同時被攝像機和照相機納入收藏了。
“噢!”我能聽到那三個伙伴心底的歡呼,我的心情同樣也很興奮,兩只前腿騰空而起作狂歡狀。步調一致才能得勝利,已經成為我們共同的生存默契。
這是一條全國唯一的軍用鐵路大動脈,全長271公里,蜿蜒盤旋在西北大漠深處,沿途共設38個點號。點號都是以公里數作代號,我們這個117點號,表示從鐵路源頭到這里的距離剛好是117公里。每個點號哨所之間相隔幾十乃至上百里,即便是在每一個點號只停留短短的幾分鐘,乘坐軍用越野車也要腰酸背痛渾身像散了架似的顛簸一整天,待返回出發營地時早已是夜幕降丘下,大漠孤煙直。
你可千萬不要小看了這條荒漠大畫作中簡單得就像兩筆平行素描一樣的鐵路,其實它的能量大得很,據說從能上九天攬月的火箭、飛船、衛星,到可下五洋捉鱉的導彈、洲際彈道導彈都是從這條鐵路運進大漠深處。如果說鐵路是衛星的天梯,那么散落串聯起來的點號就是構成天梯的每一個臺階。
這些都是聽周小亨跟我說的。可他和我一樣,從沒見過這些高科技玩意兒。我們的生活內容僅限于彼此。每隔一段時間,便有一列列悶罐子火車呼嘯而過,既看不清車上裝的都是些啥家伙,也看不到車上究竟有多少人,更不知道是男是女,都長成啥模樣。鐵路連接著城市和鄉村,連接著平原、高山和大河,也連接著點號和牽掛著他們的親人。
我的親人就是現在的三個伙伴,我的家就是點號。
眼前這個被首長稱為王記者的美女中尉看樣子頂多只能算作一個還沒畢業的大學生,乳臭未干,連走路都跟扭秧歌似的,居然混上一個中尉軍銜,還是什么大報的記者,著實大跌了我的眼鏡。真是人不可貌相,沙漠不能用瓢舀。她正跟我的三個伙伴圍坐在一起了解我的生活情況,那活躍的架勢恨不能把我上輩子的信息都挖出來了解透徹。
他們仨像打了雞血似的,從剛剛的緊張氣氛里恢復過來,一個個爭著搶著跟她匯報工作,講故事,打開話匣子跟竹筒子倒豆子似的沒完沒了,尤其是陳衛,還時不時地腆著臉不知羞恥地露出大板牙傻笑。
我開始不安,憤懣,羨慕嫉妒恨。我迅速接近人群,貼近美女中尉用犄角頂她柔弱的腰,惹得她大聲驚叫,躲閃,手忙腳亂中碰倒了水杯,灑了她一身水。
我以一個勝利者的姿態,昂首開心地“咩咩”大叫。
誰知陳衛一巴掌毫不留情地拍在我的身上,還沖我大吼:“小白,閃開!添什么亂呀你!”endprint
沒等我反應過來,我的死黨周小亨竟然也惡狠狠地打了我臀部一巴掌,“去,一邊兒玩去!”
我眼淚汪汪地看著周小亨,一種被疏遠和不被理解的委屈瞬間彌漫全身每一個細胞,心痛遠大于肌膚之痛。
斜陽夕照時,美女中尉和她的新聞團隊終于啟程離開了點號。臨走前她竟然呈依依不舍狀,讓我很長氣。如果真不愿走,為什么不留下待上一周半月的瞧瞧,難保不會成為逃兵。
當然,我們真實的生活她是永遠不會了解的。她機器里記錄的,只能是感人的動人的煽情的幾個精彩瞬間而已。
我跟隨三個伙伴一路相送。
火車開動,三個人一起向軍車敬禮。而美女記者也舉起手臂,向我們行了一個標準的軍禮。
我專注地盯著即將開走的車,習慣性地抬起前蹄作敬禮狀。
我看見美女中尉急忙拿出手機拍照,可車已經漸行漸遠。
不知她拍出的照片里,我的一副尊容將會怎樣。也不知道,我行將結束的生命還能延續多久……
二
人走茶涼,戲演完了。
晚上,陳衛一腳踏進門就恢復到劍拔弩張的狀態。他滿嘴酒氣,面色紫紅,比起之前黑黝黝的樣子更加殘忍,嘴里嚷嚷著:“殺!殺!”
周小亨瞥了他一眼,幸災樂禍道:“晚了。”
陳衛露胳膊挽袖子:“晚什么晚?老子現在就一刀把它給宰了。”
周小亨一下子站了起來:“做夢去吧你!難道你看不出來嗎,小白馬上就要成典型了!多少媒體記者會來報道它。要是來了看不見羊,知道是你干的,上頭不擰斷你脖子才怪!”
陳衛“嘿嘿”怪笑:“老子還就不怕了。就憑今天那妞兒能把它寫出花兒來?也就是一時新鮮,估計人還沒回去呢,就把這茬兒給忘了。”
劉相走過來拉陳衛胳膊,被陳衛一把推開。
劉相怒指陳衛:“我告訴你,陳衛,別喝點貓尿就借機發瘋,在這里胡攪蠻纏,老子也受夠你了。”
陳衛凄厲地一陣笑,連我都起了雞皮疙瘩:“老劉啊老劉,我還不知道你那點兒心思?你一撅腚我都知道你要拉出幾個屎球來。你不就想當典型上位嗎?算個毽!”
劉相“哈哈”一樂:“我想當典型,難道你就不想?我是為了我自己嗎?!誰他媽的嚼沙子都嚼吐了,吃罐頭吃膩歪了,可這就得殺小白?怪得著它嗎?現在它就是我們的希望!”
陳衛不以為然:“反正老子就是一個走,管他什么先進不先進,典型不典型,老子是絕了后的人,還怕個毬!你以為這羊留下了,它就能話?這些日子,你見它吃過幾根草?人都死絕了,更何況羊!”
陳衛的話讓現場出現了沉默。
我知道,他們定是想到了陳衛老婆出,走那天的情景。
我默默看了眼周小亨,他嘴唇被牙齒咬出來一排印子,手指也緊握得發白失去血色。
這是殺機,明顯的殺機。對手便是陳衛。
這是我生平第二次親歷來自周小亨的殺機。
平靜的日子里醞釀著風暴。
劉相掰著指頭計算那個美女記者離開多少天了,也不知她寫的報道什么時候可以見報。他甚至懷疑那個美女記者寫的東西會不會被上級因為某種原因給槍斃掉,或者由于版面的原因只是象征性地刊發一條小消息,起不到什么宣傳效果。
周小亨絕對相信王記者可以寫出一篇有影響力的好東西出來,他說從美女記者那雙清澈透明的眼睛里就可以看到真誠和希望。
陳衛譏諷周小亨:“你小子是不是喜歡上那個美女記者了?既當典型又抱美女,一箭雙雕呀!只可惜你這是癩蛤蟆想吃天鵝肉,門兒都沒有!”
周小亨大為不悅,兩個人吵起來。
劉相把兩只好斗的公雞按下了。
全變了。
原來的日子不是這樣的。如果說我一生中有什么最值得珍惜的日子,那就是我與三個伙伴和和睦睦度過的那段時光了。雖然從來沒有充足的食物,也沒睡過一天安穩覺,可心底是踏實快樂的,不像現在這樣,每天憂慮著生與死。
其實,從我剛一來到這里,就注定了成為一只待宰羔羊的命運。
點號全部的生活內容簡單乏味得屈指都比它豐富多彩,幾間小屋,一排稀疏的柵欄,一根與外界聯通的天線,構成了全部的生活設施,恰似幾筆素描勾勒的簡筆畫。
沒事的時候,周小亨常蹺著腳站在鐵軌上,伸長了脖子使勁兒或向東或向西地眺望,結果望斷天涯也望不到鐵路的盡頭,有時候還會產生幻覺,感覺遙遠的模糊地平線上出現一個小人兒,緩緩地飄過來。周小亨心里盼著那人走快些,等啊催的,到了近前才發現,原來是南柯一夢。
整個點號世界數周小亨最有文化,大學上到一半應征入伍,平時總愛用些形容詞之類的寫幾首小詩,否則我也不會奪得“沙漠之羊”的美名。劉相和陳衛無聊到拿一副發黑的紙牌玩接龍或者大眼瞪小眼的時候,周小亨愛用看書打發時間,幾本書翻來覆去讀得打了毛邊。他曾跟我說過,每次沿著鐵路巡邏一圈回來,感覺鐵路連接的并非天地,而是古今。他像是荒漠中的一個孤點,時間的線流透過粗糲的沙子將他打透了,鑿穿了,隨時都能消失似的,只有皮膚和沙粒摩擦的疼痛和唇齒間的嘎嘣聲提醒他還活著。
劉相一直擔心周小亨讀的那些東西會害了他的腦袋,每天迷迷糊糊神神叨叨的,便勒令他跟他倆一起打打牌喝喝酒。
周小亨打趣說:“我就不喝啦,我再喝醉了,你倆要是吃點小酒,喝點小肉,沖動起來摩擦出火花,那可是連個勸架的人也沒有啊。”
劉相笑笑,也就隨他去了。
吃點小酒,喝點小肉是周小亨故意這樣說的,顯得自己有幽默感。
當然,吃點小酒可以偶爾實現,但喝點小肉卻太難了。
直到我的出現。
俗話說,一方水土養一方羊。然而,這里的水土并不適合我的生長,但我恰恰降臨到這里。而我的到來,仿佛讓幾個戰士從日復一日比做菜沒放鹽還乏味的長久單調生活中集體覺醒過來。日夜與沉寂荒漠為伴的點號突然來了個動物,周小亨等人的喜悅不遜于年輕的父親喜得貴子。當然還有另一層含義,他們已經許久沒有聞到新鮮的肉腥味兒了。endprint
我剛來時身上并沒有多少肉,骨頭包層皮,還打蔫,毫無胃口可言。
三個戰士之前費勁巴力地在小院子里侍弄的幾點新綠,眼巴巴地連一口口福都沒撈到便迅即夭折。陳衛沖著一片貧瘠得寸毛不生的膠土地罵罵咧咧地踹了兩腳,不得不斷了自給自足的夢想。
食品供應完全靠定期運輸的火車統一配送,一般是15個日出月落運送一次,有時是30個日出月落一次,綠色蔬菜運送過來都蔫頭耷拉腦的早沒了精神,新鮮肉食根本就是烏托邦幻想主義。這里經常還會遇上風沙或者暴雨的惡劣天氣,部分路段被掩埋,火車無法通行,流動食物鏈斷裂,就只能依靠儲存的罐頭食品。罐頭的種類還算豐富,有魚香肉絲,紅燜豬蹄,清炒扁豆,土豆燉牛肉……可是腌制的食物跟新鮮烹調美味之間的差別謬之千里,連續吃幾天腸胃系統便膩歪得死去活來,且經常會發生死機現象,不想吃東西。
綜合以上種種,我初來乍到就沒指望活著回去。
為此,劉相特意主持召開了一次內部會議。
陳衛主張直接把我宰了吃掉。
周小亨強烈反對,理由是我太瘦,養養看再說,放長線釣大魚,要吃就吃豐腴肥壯的。后來他告訴我,其實他藏著心思,好不容易來了個伴兒,舍不得吃。他把這種情懷叫做悲天憫人。
陳衛“嗤”地一聲嘲笑:“你倒說說看,咋養肥?院子里除了那一叢長不成氣候的綠菜芽,羊還能吃啥?”
周小亨想了想,憋紅了臉也沒找到答案,最后只能說:“反正我有辦法。”
三個戰士中資格最老的劉相像族長一樣端著臉,作了一番嚴肅思考后,最終得出結論:“先養著,后續命運再議!”并將飼養員的桂冠一下子扣到周小亨的頭上。
我跟周小亨之所以成為死黨,其實原因很簡單,他愿意無條件負責飼養我,我愿意元條件跟隨他,這叫知恩圖報。
周小亨為了飼養我真是挖空心思,花了大功夫。原來小院子里有幾點不成氣候的野草,早就被我風卷殘云干掉了。周小亨就徒步跨越幾座沙丘,去幾公里以外的地方尋找綠色植物,那是我的生命,也是他的希望,他說過的,為了綠色生命而生活和工作。他撫著我的羊頭跟我說,說老實話,我在家對我老娘都沒有像對你這么好,這么上心,這么付出。說這話時,周小亨的眼里蓄滿了淚水,我干澀的眼睛也潮濕了。那一刻,我們手拉著手,心手相連,血脈相連,我在內心發誓,我們的友誼是用鮮血和生命凝成的,是牢不可破的,經得起時間和歷史的考驗。我在內心對他已經以身相許。
為了養活我,周小亨陪著笑臉跟定期送貨的師傅拉關系,說一大堆拜年話,拜托他給我帶食物。
師傅一般都是有一搭沒一搭地應付,有的兌現承諾,有的一拍腦門子說忘了。最可恨的是一個長一只三角眼,臉上帶一道傷疤的閻師傅,竟然公然叫囂:“干脆把這只羊宰了吃肉,省得麻煩!”
我當時聽了怒火萬丈,要不是周小亨使勁拽住我的一只犄角,我非沖過去跟他玩命不可。我至今記得他那張丑惡的嘴臉,頗似京劇里的白臉小人模樣,下次見到他,絕輕饒不了他。
三
沙漠還是那個沙漠,點號還是那個點號,日子還是那個日子。
最初我的生存范圍和他們幾個還隔著生物品種劃分,人與羊互不侵擾。
周小亨是一個勤勞的兵,他動手把院子里唯一的一截柵欄圈了起來。在我們尚彼此陌生互不了解底牌時,我隨時都有可能跑丟。在這大漠深處,我其實無處可逃,等待我的最終不是餓死就是渴死的命運,然后來一陣沙塵暴連肉帶骨地把我埋掉,百年之后,再來一陣風沙將我打回木乃伊原形。
如若那樣的話,對他們幾個來說,可真是到手的肥羊飛走了。
我漸漸融入了他們的生活,成為他們中的一員。我對周小亨的報答方式就是跟隨他。由于經常鮮草斷頓,我不得不從罐頭里挑菜吃。這無異于杯水車薪,更何況菜早已不是那個新鮮菜,還伴有一種怪怪的變態味道。沒辦法,每天只能餓著大半拉肚子鏖戰風沙,與苦難的死神環境較量。即便這樣,我還是努力地生長著,讓自己變得強壯。
我成了周小亨的影子,他早晨起床,我也起床;他做早操,我跟著做早操;他跑步,我跟著跑步;他立正,我跟著立正;他稍息,我跟著稍息;他吃飯,我跟著吃飯;他沒事坐在那里看著大漠發呆,我依偎在他身邊也跟著看大漠發呆;他熄燈睡覺,我跟著閉眼睛睡覺……我當然注意得到劉相和陳衛對我態度的轉變,當我跟在他們后頭像個戰士一樣刻苦訓練,努力模仿他們的時候,我從他們眼神之中讀到了一種情感,柔柔得像一張網一樣籠住了我,搞得我渾身酥酥麻麻的。我已從“盤中餐”成功逆襲為戰友了,完全融入到他們的生活和工作里,成為他們中的一員,是人是羊有時連我自己都真偽難辨,只有在方便排泄時才恍然大悟:噢,人類需要脫褲子干這活!麻煩!
可說一千道一萬,我畢竟是一只羊,具有動物所特有的隨意而自由的屬性,貪吃,可是沒的吃,貪玩,大漠好大,好遼闊,可以到處逛逛,驅散一下食不果腹的郁悶,散散心,順便也找找有沒有鮮美可口的綠色食物。
這天,我在丘陵起伏的沙漠毫無目標地閑逛了半天,沙漠好柔軟,溫度好熱,四蹄跋涉在里面如同足浴加按摩,很是舒爽,還不用花錢,完全免費,這是城里人無論如何也無法享受到的地區專利。沒辦法,羊嘛,總會有羊的規則,這是上帝造物的自然規律,萬事萬物都與人類完全一致,豈不是天下大亂了嘛!
就這樣信羊由蹄,胡思亂想地溜達了一上午,視線所及都是遮天蔽日的黃沙,連一點兒綠毛都沒看見,感覺很失落,也有點兒渴了,餓了,累了,頭有點兒暈,也開始想念死黨周小亨和另外兩個伙伴了,我便折返身,沿著原路深一腿淺一腿地溜達回了點號。
我記憶力蠻好的,一般認路還基本沒有問題。
隔大老遠,我就看見死黨周小亨向我狂奔過來,一副激動萬分的神情。我心里一熱,一股見到親人的情感奔涌上來,也想發力迎上去做一個擁抱的感人場景,可惜我只抬了抬前腿,后腿綿軟無論如何發不上力,關鍵時刻掉鏈子。endprint
周小亨一下子將我撲倒在地,雙臂死死摟著我,聲音哽咽地喃喃道:“小白,你跑哪兒去了?害我找得好苦!我還以為你跑丟了,被沙漠埋了呢!”
我的死黨如此情深意切,令我感動得五體投地,熱淚盈眶,我“咩”地回應了一聲,用嘴唇親吻著他的嘴唇和臉頰……
周小亨捧起我的頭,眼睛紅紅的,閃動著淚光看定我說:“記住,以后不許到處亂跑,會有生命危險的,聽懂了沒有?”
我發自肺腑地“咩”了一聲作為回答。
沒想到,陳衛黑著臉走過來,指著我面露兇相惡狠狠地說:“再敢亂跑就殺了你吃肉!老子已經很久沒嘗過新鮮羊肉的味道了!”
我大吃一驚,掙扎著從地上爬起來,這家伙怎么說翻臉就翻臉。
關鍵時刻,周小亨挺身而出護佑我。
兩個人又吵了起來。
自從那場沖突過后,我跟死黨周小亨幾乎是形影不離。工作中,在懸空的毒日頭暴曬下,我盡量選擇站成一道細細的陰影,為死黨遮陰納涼,使其免受一些皮肉之苦。
可同時,我感覺陳衛看我的眼神有點兒怪怪的,內容兇險。平時往往一陣風沙吹來,都會令我不寒而栗,心中隱隱地不安。我感覺到死亡的陰影開始籠罩著我……
周小亨只有一件事不帶著我,就是巡道。巡護鐵路是這個點號存在的意義,也是最為費力的工作。每次巡道,都要全副武裝地穿上巡道服,背上維修包,頂著風沙沿鐵路線挨個檢查螺釘、枕木,一走就是十公里,一趟下來滿嘴滿眼滿身滿心的沙子,在生死場上滾過一回似的,劫后余生的驚喜中還包含著巨大的傷感與痛楚。說不清的感覺。周小亨是這樣形容的。
每次巡道回來,他都要摟著我的脖子哭上一場。有時是嚎啕大哭,有時是默默流淚。陳衛嘲笑周小亨這是不成熟的表現,娘娘腔,沒出息。
可我能體諒他,我知道他心里最柔軟的地方。他怕死。人人都怕死,但周小亨的怕又有些不一樣。他對生命極其敏感,極其敬畏,又那樣憧憬著外面的世界,渴望著將來有一番作為。說到底,他不會做一輩子的巡道兵,把生命埋沒在茫茫沙漠里。每當他傷心哭泣時,我能做的唯有依偎在他懷里,溫柔回望著他,用眼睛告訴他,我懂他。
一個不陰不陽的天氣,輪到死黨周小亨去巡道。他十分熟練麻利地穿上橘紅色的巡道服,從頭到腳包了個密不透風。其實無論春夏秋冬,每次巡道回來,脫下厚重的巡道服,都跟被淋了一場大雨似的,渾身上下濕個透。
周小亨還沒出門就發現我開始躁動不安。根據經驗,這種天氣極容易演變成風雨交加。他本來不想讓我跟去,可是我不干,任憑他使勁推我的犄角,怎么拽,怎么趕,可我就是倔犟地擰著性子跟上他,死纏爛打。死黨毫無招數敗下陣來,退讓妥協,把一件巡道服折疊了幾下套在我身上,前后腳一起出門上路。
周小亨貓著腰,沿著蜿蜒曲折的平行鐵路線一步一個腳印地向前平穩推進。他一只手拎著小鋼錘不時地敲打幾下,查看一顆顆螺絲釘和一塊塊枕木是否堅固牢靠,嚴肅而認真,一絲不茍,絕對像戰場上的排雷戰士。
我熟悉并喜歡他這種工作的樣子和風格,特別具有一個戰士的魅力。每當這時,我就會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如果有人解釋說是踢踏舞也不過分。
前幾公里天公配合,工作還算順利。可是進行到一半路程時,起風了,風勢且行且大,裹沙帶粒劈頭蓋臉地襲過來,打得我們睜不開眼睛。
周小亨蹲下來努力護住我的身體,我緊緊靠在他身上拼命護佑他。這就是生命的本能和生存法則,何況我們是戰友,是生死兄弟。
狂風裹夾著熱辣辣的黃沙猛烈地燒灼著裸露在外的皮膚,睫毛上,眼睛里全是沙子,生疼難耐,眼睛沒一會兒就紅腫起來。
周小亨努力睜大眼睛,辨識著鐵路的方向,掩護著我原路返回。
可是,我們的速度無法超越風沙的速度,回程的鐵路很快就被風沙掩埋掉。
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終于發生了。如果看不見鐵路,我們將迷失方向,我們的生命將接受大自然最嚴峻的挑戰。
周小亨懷抱著修理包,雙膝跪地開始拼命用手挖沙子,一捧接一捧地往一邊兒揚。
我看見了他的懊惱,后悔不該貿然帶我出來。我也意識到了生命面臨危機,開始用前蹄扒沙,后蹄蹬沙,酷似一部自動化掘沙機。
黃沙在我們周圍上下狂飛亂舞,鬼哭狼嚎,大有摧枯拉朽埋葬世界之氣勢。我們拼盡全身力氣瘋狂地挖沙,挖沙……
天色暗沉下來。
天地渾濁不堪。周小亨終于放棄了努力。他搖搖晃晃地站起來,仿若置身在天地尚未分開的盤古時代。他搖擺著身子努力尋找方位,給自己打氣。可是他的身體像是不聽使喚了,艱難得一小步一小步地蹣跚著,突然腳下一絆,便失去了平衡,再也沒有起來。而我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黑暗之中……
當我再次醒來的時候,周小亨在我身邊。
是他把我喚醒的。他渾身是沙,不知剛剛經歷過什么。我混沌不清,分不清晝夜,可我卻分明從周小亨眼中感到了殺機。
是的,殺機。夜是孤冷的,可他眼中卻閃耀著兩團火,那是一種對生存的原始渴望。
我知道,在這沙漠中一旦迷了路,若救援不及時,生存下去的希望是渺茫的;我也知道,他隨身的包里面是備有刀和火的。也許他那一刻的想法并不真實,但卻在本質上改變了我們。我閉上眼睛,絕望卻是心甘情愿地等著為周小亨犧牲,獻身于他……
可那一刻并沒有到來,巨大的黑暗再一次將我倆吞沒了。
四
如果不是陳衛老婆來,我還真不知平時對我時冷時熱,性情暴躁的陳衛,關鍵時刻竟然還會那般袒護我。
在他老婆尚未駕到之前,小小的點號已經開始騷動不安起來。陳衛像換了個人似的,不再為喝酒打牌的事兒整天罵罵咧咧的,而是變成了嘿嘿傻樂。他對著戈壁灘,對著月亮,甚至對著早已斑駁的破墻壁,都能樂出聲來。好幾次在跑操的時候竟然都忍不住樂,干活兒也比以往勤快。有時候出門看到我,竟愛撫我的脖子打招呼:“小白,干嗎呢?”“小白,今天好嗎?”整個一太陽從西邊出來,搞得我莫名其妙,受寵若驚。endprint
陳衛對他妻子的感情,點號皆知。117點號資歷最老的是劉相,最有文化的是周小亨,可寫信最勤的卻是陳衛。他寫信對象只精準對位于一個人:他老婆。每次看他一個大老粗對著低瓦度的小燈泡認真寫字的模樣,真是既滑稽可笑,又有點讓人感動。
在點號,收信寄信都要等添乘的時候,來往路過的火車師傅負責收取,亦根據天氣狀況和時間來定,有時候30個日出月落,有時幾十上百個日出月落。如果不幸趕上天線中斷信號,那可就是趙本山上春晚——說不準了。有一次陳衛在門口值崗,遠遠看到添乘過來,折身瘋狂往屋里跑取信,跑到門口遇到正往外跑寄信的周小亨,兩個能量場強大的男人狠狠撞在一起,作用力的結果自然是增大倍數,雙方竟當場暈倒。
陳衛老婆來探親的日子終于敲定。我們以接待首長的規格接待了她。其實也只不過是按照出操次序站成一排,周小亨費勁找來幾張紅紙剪了幾個窗花,赫然貼在窗上,喜慶色彩大增,比過年都熱鬧。
陳衛的老婆叫小方,個子不高,還有些胖,但是看上去依然年輕,打扮得土洋結合,匹配陳衛倒也綽綽有余。
晚上喝酒時我聽說,陳衛能娶到她絕對是祖墳冒青煙。陳衛老婆是縣城的,當初嫁陳衛完全是被電視劇和小說里的軍人形象給洗了腦,加上聽說陳衛是在飛船發射的地方當兵,感覺光榮崇高得搭上火箭一般,二話沒說就嫁了。
可是來了才知道,這里距離飛船發射的基地遠著呢,就好比現實和理想的距離。我還沒來的時候,據說陳衛老婆來過一次,因為受不了這里的氣候和環境,便早早回娘家去了,惹得陳衛好一陣懊惱。這次好說歹說地給勸來了,劉相擠眉弄眼地說,是帶著重大任務來的,為的是要“懷上”。
點號只有兩間房,陳衛和她老婆住一間,劉相和周小亨擠一間。小方嫌棄外面太曬,也礙于劉相和周小亨的性別,極少出屋。我偶爾透過門縫往里瞧,她往自己身上扎針,據說得了某種病,要定期服激素,不然也不會這么胖。她每隔7個日出月落就要搭車去幾十里外的醫院檢查身體,陳衛有時因為工作不能相陪,她就很生氣。
一次她從醫院回來,路過我時溫柔地看了我一眼,還拍拍我的頭說了好幾句話。晚上吃飯的時候,她難得移駕跟我們一起吃,在飯桌上跟劉相說:“老劉,陳衛不好意思跟你說,我來說……醫生說了,我的體質本來就弱,再加上生病,很難懷上孩子,必須要滋補才行。醫生說,羊肉對女人最好了,如果每天能喝上一碗鮮美的羊肉湯,我準能懷上孩子。你們看……”
飯桌上靜悄悄的,連碰撞碗筷的聲音都顯得非常刺耳。
晚上睡覺時,從陳衛的屋里傳出爭吵聲,摔東西聲和女人的哭叫聲,然后是陳衛小聲勸慰的聲音,到后半夜才逐漸平息下來。
這種情況持續了八、九個日出月落。
后來一天早上,陳衛大驚失色地從房間沖出來,屋前屋后地到處找。老婆不見了。
小方不告而別。
陳衛無精打采耷拉著臉子好一陣子,突然又樂了。小方來信說懷孕了。可即將當爹的喜悅持續沒多久,陳衛又不開心起來,脾氣更暴躁易怒了,看我的眼神里也有了恨。小方來信說,孩子沒保住,她把錯全推到陳衛頭上,說是她來探親的時候沒讓她喝上羊湯,調理好身子。她發誓永不原諒陳衛,揚言要和他離婚。
陳衛像泄了氣的皮球一樣,整個人都癱軟了。他比以前更頻繁地喝酒,每次喝完酒就來找我,踢踢踹踹,罵罵咧咧的,放狠話要殺了我。
周小亨為了保護我,夜里都不敢睡踏實了,有一點風吹草動就翻身出來查看一番。
有一天周小亨撫著我的頭說:“小白,你的命真大。你知道嗎?老劉都同意要殺你給小方燉湯了,是陳衛攔著不讓的。哎,他既然那時候不殺你,現在又是為了什么呢?”
我一驚,流下了兩行熱淚……
我不得不跟我的伙伴們告別了。
美女記者的報道遲遲沒有見報,不知是計劃流產了,還是壓根她就沒有寫。就像陳衛說的,可能她一扭身,興奮勁兒一過,就把我忘在茫茫大漠里了。
周小亨已經偷偷對我說過,他準備找個時間把我送走。對,是送走。我是一只羊,沙漠之羊,命運無非就是兩種:要么被宰殺吃掉,要么賣了換酒喝。這兩種選擇周小亨自然都不會接受。我當然知道,如果不是那次暴風飛沙的極端情況,他永遠也不可能真心要我的命。而自那次沙漠事件之后,我分明能感受到他一舉一動里都透著對我的愧疚和自責,他是從骨子里愛我的呀!
而陳衛,他會真的殺了我嗎?我不知道。可我私下里是愿意為他而死的,畢竟,他是我最親愛的戰友矗如果我的死能換來小方對他的原諒,那我絕對是死得其所,值了。
劉相,我感覺對不起他。我沒有如他所愿,換來光輝形象的登報,成為這個點號的驕傲與榮耀。我知道他為的什么。為了少受些苦,為了吃得更好,為了引起重視,為了前途,為了117點號。
我并不打算被周小亨送走。也許會有更多的草,更溫暖舒適的窩,可是離開這里,這一切毫無意義!
我和他們一樣,是一名戰士,可卻從沒有為這個小小點號奮斗過,反而因為我打亂了他們平靜生活的步調。我必須做些什么。
我已經做好準備,按照預想的那樣,等周小亨睡前看完我,走回房間關上門,我立即從假寐狀態清醒過來,提耳聞聽一會兒動靜,證實安全之后,立即開始行動。所有的人。尤其是我的死黨周小亨絕對想象不到,我會以這樣的形式跟他告別。
整個行動和想象的一樣順利,沒有出現任何意外情況,反倒讓今夜的行動有些索然無味了。
我輕著蹄子跑了出去,沿著鐵路以勻速跑了一段路程,然后開始加速,全力前進。我從未見過外面的花花世界,在我短暫的一生中,我的心永遠屬于一望無際的大漠,屬于我深深眷戀著的戰友。
我知道我會在某一時刻停止奔跑并死去,也許恰好停在另一個點號,被戰士們拖去煮掉;也許在荒無人煙的某個地點,就那樣一點點風干,成為沙漠昆蟲的美食;還有可能被突然刮起的沙塵暴掩埋……不管是怎樣的結局,至少在生命終止那一刻到來之前,我都在奮力向著大漠的盡頭奔跑,以一只沙漠之羊的姿態奔跑,以一名戰士的姿態奔跑……
責任編輯 孫卓endprint